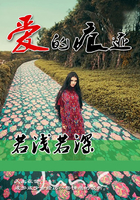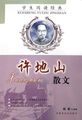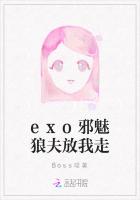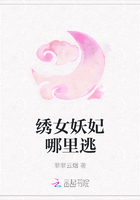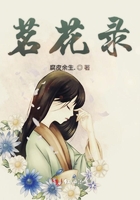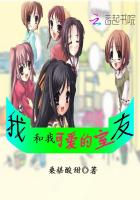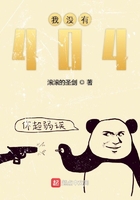《红楼梦》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以“冷”著称的人物,一个是“冷面郎君”柳湘莲,另一个则是冷情美人薛宝钗。“冷”虽一字,含义有别。柳湘莲的“冷”,是自视甚高,踞傲不群,对“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冷面冷心”,只“最和宝玉和的来”,对他倒不太冷,而是冷中有热。薛宝钗的“冷”,则是理胜于情,过于克制,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偏于冷静、冷淡、冷漠,有时近于冷酷。
“任是无情也动人”(薛宝钗所掣花签酒令诗句)。“无情”是冷,美则“动人”,这一诗句是对冷情美人薛宝钗的一种诗意概括。当然,“无情”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她并非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情”;不过,对有的人,她即使动情的时候,一般也有所节制,表现得比较含蓄委婉,往往给人以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感——她对贾宝玉就是如此。
宝钗对宝玉的感情,比起黛玉对宝玉的感情,不仅性质、深度有区别,其表达方式、表露程度也很不相同。再则,作品对宝黛爱情描写中插入了一定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使读者理解二人内在感情更增加了透明度和确定性。而作品对宝钗的描写则侧重在外部行为、外部情态,较少触及她的内心世界,尤其在涉及她对宝玉感情心态的过筋过脉处,往往讳莫如深,不置一词。鉴于上述原因,宝钗对宝玉的感情描写本身就带点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既给读者的理解增加了难度,也给读者的创造性解读留下了一定空间。这种创造性解读,当然必须是以文本为据的合理分析,而不是毫无依据的随意猜测。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形于外。即使像薛宝钗这样相当理智、善于克制的冷情美人,也会有七情六欲,因而就难免有“情动于中”、情不自禁之时,其感情也将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直或曲地流露于外在形态和外部言行。
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的情节,通过描写宝钗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宝玉时的言谈举止,就相当曲折、微妙地透露了她对宝玉的感情心态和婚姻意向。尽管这不是二宝初见,但毕竟是表姐弟俩第一次单独亲密接触,性情中人、情痴情种的宝玉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对宝姐姐的某种倾慕之情,这原在情理之中。即使平时“罕言寡语”、“人谓藏愚”、“自云守拙”的宝钗,直接面对前来探病的宝玉,她的喜悦和激动,也情不自禁溢于言表。在互相问候回答之后,她就让宝玉“在炕沿上坐了,即命莺儿斟茶来。一面又问老太太姨娘安,别的姐妹们都好”(真是礼多人不怪,什么人都问候到了);同时一面上下打量宝玉的穿戴,很快把眼光定在了宝玉“项上挂着”的那块“通灵”宝玉上。于是,宝钗便直奔“主题”地对宝玉笑着说:“成日家说的你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此话出自平时端庄娴淑、“罕言寡语”的宝钗之口,可能是她出于好奇,但似乎又不只是好奇。宝玉那块“玉”与宝钗身上所挂的“金锁”有何瓜葛与传闻,且不说薛姨妈,连不相干的薛蟠和薛家丫鬟都了解,她本人绝不可能不知道。此时,她毫不避嫌地急于“瞧瞧”“通灵”宝玉,恐怕不单是为了“赏鉴”,还有更深层的感情动因。
宝钗对被宝玉本人视为“劳什子”的那块“通灵”玉,真有点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托于掌上”,细细“看毕”之后,“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看还不够,又“口内念”(玉上镌文:“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一遍不足,“念了两遍”。更有趣的是,宝玉刚进“里间”时,宝钗就“命莺儿斟茶”,究竟斟没斟,她忙于看玉,已无暇过问,唯独细细“赏鉴”完了玉,念完两遍玉上镌文,她才“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听话听音,莺儿听了宝钗问话似乎心领神会,又没遵命去“倒茶”,却答非所问,针对“通灵”玉上的镌文,“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莺儿无论是因为善解人意,还是由于别具会心,她说的“一对儿”三个字,可能恰好说到宝钗的心坎上,也激起宝玉要看宝钗“金锁”的强烈兴趣。宝钗假意推脱了两句,便承认莺儿说的是事实,并“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将出来。”“宝玉忙托了锁看时,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两面八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于是,“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字倒真的与我的是一对。’”机灵的莺儿接过话头,马上说明宝钗金锁上的八个字的来历:“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不待说完”,宝钗“便嗔他不去倒茶”。这是宝钗第三次说到了“茶”,但说者本意似乎并不在“茶”。实际上,“金玉姻缘”之说来历已明,再让莺儿说下去(无非点出“金”要“玉”配的话)就会令人尴尬,故宝钗再一次以“倒茶”为辞转移话题,突然前言不搭后语,“又问宝玉从那里来”。
以上这段情节,回目尽管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但从“比通灵”到识“金锁”,却都是宝钗主动提出或巧妙导演的,莺儿只不过“心有灵犀”说了一些宝钗心里想说而嘴里说不出的话;她“微露”的有关“金玉姻缘”意向,又何尝不是宝钗自己内心深处的婚姻意向呢。宝钗“命莺儿斟茶”之后,又两次提及“倒茶”(主奴都忙于看“玉”说“金”,“茶”始终未去倒),这更是借“茶”为题、言此意彼的传神之笔。
过去,有的红学家把“金玉姻缘”看做一场骗局,认为此说是薛姨妈为将女儿嫁进贾府而处心积虑编造的谎言。这种看法既无文本根据,也过分贬低以至丑化了薛氏母女。只要我们不否定《红楼梦》虚幻描写存在的特殊意义,也就没有理由怀疑、否定“癞头和尚”是“金玉姻缘”之说的始作俑者,并代表了世俗之见的天意,薛氏母女只不过是顺天意,遂人愿,愿意或乐意接受此说。
据此,我们注意到:宝钗对宝玉的感情,尽管带点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给人以道似无情却有情之感,却又往往与相对比较明确的婚姻意向联在一起。第二十八回,当宝黛正为“金玉”之疑纠缠不清、赌咒发誓时,“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鉴于薛姨妈“往日”对王夫人说的“金”要“玉”配的话已近于正式提亲,而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则像是默认二宝亲事的一种暗示,宝钗内心的“金玉姻缘”意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有底,因而她更加自重,更不好意思,“所以总远着宝玉”,远离宝黛感情纠缠。不过,宝钗只是有他人(尤其是黛玉)在场时“远着宝玉”,单独面对宝玉时,非但没疏远他,反而与他似乎更亲近。就在宝黛二人“走开”后,宝钗与宝玉相遇,宝玉笑着要瞧瞧宝钗臂上的“红麝串子”(元春所赠之物),宝钗毫不迟疑,“少不得褪了下来”,尽管由于她“生的肌肤丰泽”,好不容易才褪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般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并引来他希望宝钗“酥臂”“长在林妹妹身上”的奇思异想。
如果说少男少女间的相互愉悦倾慕也属异性之爱,那么,二宝间确有相爱一面,只是爱的性质、层面不能与宝黛爱情相提并论。由于思想性格等方面的差距,二宝在相互愉悦倾慕的同时又彼此各有不满之处,而宝钗对宝玉恰恰是在最动情、也最“动人”的时刻,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感情。宝玉因“不肖种种”挨了贾政毒打后,宝钗前去探视,在彼此问候应答时,“见他睁开眼睛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面对卧床养伤仍不失礼让的宝玉,宝钗此刻的确动了真情,感情也相当复杂:心疼中带埋怨,娇嗔中夹爱意,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红脸低头,耍弄衣带。这种种“娇羞怯怯”之状,也只能是一个动情少女在自己所愉悦的少男面前才可能有的情态。“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薛宝钗,恰恰是在这动了真情、去了矫饰的刹那间,显露了纯真少女本色一面,表现出真正“动人”的魅力。可是,宝钗的真情流露,如春光乍泄,转瞬即逝,一旦恢复了常态,她思想性格上世俗性和道学气的一面就突现了出来。当袭人误信谣传,怀疑宝玉挨打可能与薛蟠有牵连,宝玉“唯恐宝钗沉心”,“忙又止住了袭人”,并为薛蟠辩护。宝钗因此“心中暗暗想到:‘打的这个形象,疼还顾不过来,还是这样细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喜欢了,也不能吃这样亏……’”随即又笑对宝玉说:“……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宝钗心头想、嘴上说的话,虽出自对宝玉“规引入正”的良好愿望,但对宝玉来说,这无非是要他热衷“仕途经济”、多在“外头”结交官宦之类的“混帐话”,只能使他生厌,也“生分”了彼此关系。
说到宝钗对宝玉的感情心态,我们不能不提到袭人。红学历来有“袭为钗副”(甲戌本第八回批语)或“袭为钗影”之说,这不无一点道理。仅从同宝玉未来择妻择妾问题的关系来说,这主奴二人仿佛一“正”一“副”,一搭一挡,声息相通,命运相连,因而时有借袭影(影映)钗之笔。清人陈其泰在《红楼梦回评》第七十四回评语中说:“袭人留房,而知薛婚之已定……如镜照影,若离若合。善悟者,自得知。”《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7页。虽然说得过于简单、绝对,但对读者的解读确有启发。一次,宝钗来到怡红院,恰逢王夫人“打发人”特地“指名”给袭人“送了两碗菜来”,袭人受宠若惊,却又佯装不解其意,对宝钗笑道:“从来没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宝钗听了,“抿嘴一笑”说:“这就不好意思了?明儿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还有呢。”(第三十五回)这句话“话内有因”,暗示“明儿”王夫人即将把袭人内定为宝玉未来侍妾。此事王夫人尚未在一定范围宣布,而宝钗心中却已明白,除了表现她悟性很高或信息灵通外,更意味着平时她对此事的重视和关切,似乎此事与她本人命运攸关。这不是单纯的推测。试想此前,宝钗“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没意思”即“不好意思”,也是受宠若惊,同袭人得到王夫人赏菜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而今,她从“袭人留房”,预感自己婚姻大局已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而她是为袭人高兴,也在为自己高兴。她说此话时露出的那份高兴劲儿、得意劲儿和神秘劲儿,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借写袭人与宝玉的特殊关系来影映宝钗对宝玉的感情心态或婚姻意向,在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一段情节中,用了所谓“金针暗度法”(己卯本回前评语),更表现得蕴藉含蓄而又妙趣横生。袭人被内定为宝玉“屋里人”后,宝钗“独自”来到怡红院,“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鸦雀无闻,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丫头们都“在床上横三竖四”睡午觉;更见宝玉也“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针线,旁边放着一柄白犀麈。”显而易见,这绝不是可能与“宝玉谈讲”闲聊的时刻,再则,袭人作为准侍妾侍候宝玉午睡犹可,宝钗身为待字闺中的大家闺秀,理应回避悄然退出。但令人奇怪之处,一是宝钗不合时宜地不避反进:“走近前来”,无话找话地和袭人“悄悄”拉起家常来;二是宝钗有失身份的越俎代庖:袭人借故“出去走走就来”,“说着便走了”,“宝钗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得拿起针来,替他代刺”(重点为引者所加)。什么“不留心”“一蹲身”,完全是情不自禁地忘了礼数,忘了避嫌,身不由己地取代袭人,临时充当了陪侍宝玉午睡的角色。请看,作品通过黛玉视角“摄”下的镜头:
……隔着纱窗往里一看,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
好一个“夫”睡“妇”陪,琴瑟和谐的动人场景!难怪黛玉见了吃醋“冷笑”,就连与宝钗素日交谊甚厚的湘云见状也几乎笑了出来。正统派兼拥薛派旧红学家王希廉,对这段描写也评点道:“宝钗刺绣尚可,蝇刷实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云亦不免疑”。一位被人称为“女夫子”的冷情美人,竟然也有动情而忘形的时刻。其实这算不上失态,更不是过失,只不过证明任何人也会有真情真性一面,这种真情真性在有的场合、有的时候也是掩盖、压抑不住的(或者毋需掩盖、压抑)。
正当宝钗忘形地沉浸在宁静温馨的个人感情世界时,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本来,“木石姻缘”与“金玉姻缘”之争由来已久,宝黛间怄气、口角多与此事有关,钗黛间也曾因此争风吃醋、反唇相讥。但是,宝玉在梦话中,对两种婚姻之争,作出如此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选择,毕竟使宝钗大感意外,所以“不觉怔了”。一个“怔”字,点出了宝钗当时的外部神态,其内在心态却耐人寻思:是震惊?是尴尬?是羞愧?是不满?很难明确回答,或许可说兼而有之。
通读《红楼梦》原著前八十回,可以看出:宝钗对宝玉看似无情,实则有情,只是这种“情”虽与“金玉姻缘”的婚姻意向密不可分,却始终未能深化、升华,基本停留在异性间相互愉悦倾慕的感性层面或浅表层面——这不仅由于二人思想观念上有差距,更在于性格类型上的不同:像宝钗这种理智型的冷情美人,即使宝玉能如她所愿,改邪归正,成为她更理想的婚姻对象,她也绝不可能像黛玉那样,对宝玉爱得如痴如迷,死去活来。据此可知,“木石姻缘”与“金玉姻缘”之争,不是常见的爱情婚姻与无爱婚姻之争,而是理想爱情婚姻与世俗性爱婚姻之争。
在《红楼梦》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爱情对于婚姻来说乃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享受到,而宝黛所追求的那种生死以之的理想爱情婚姻,更是凤毛麟角,极为罕见。“金玉姻缘”虽带世俗婚姻色彩,但与有些完全无爱的世俗婚姻却又不能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按《红楼梦》原著所写,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黛死钗嫁,“木石姻缘”“终虚化”,“金玉姻缘”成现实,宝玉对宝钗并非深恶痛绝、拒之门外,而只是有“美中不足”之叹,即所谓“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能“齐眉举案”、相敬如宾的夫妇,按当时世俗婚姻标准还算美满姻缘。只因宝黛二人爱得太深,爱得超过了生命、超越了生死,所以宝玉失去黛玉的心灵创伤才永难平复,“到底意难平”。比较中外古今文学作品所写的爱情婚姻悲剧,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独到而特别深刻之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