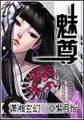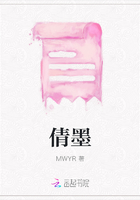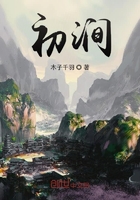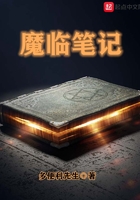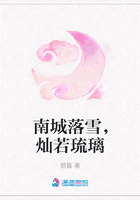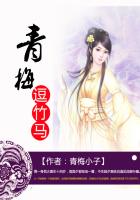但上述喜剧性叙事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一个主流的传统,另一个真正具有主导性的传统,是以其“奇书”叙事为代表的具有“完整时间长度”的悲剧性叙事。这个问题同样复杂,需从源头上探析。对照当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性、片段性和断裂性时间修辞,正在被人本主义的、生命本体论的、完整时间长度和永恒循环逻辑的时间理念所代替。因而也不难理解,中国传统叙事中的悲剧美学也正得以修复,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其“现代”意义得以持续展现的同时,也焕发出真正的民族气质、传统神韵的一个深层原因。
中国传统的时间意识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叙事,并创造出民族特有的悲剧美学。从汉魏时代开始,个体生命意识的彰显导致了中国人关于时间的焦虑,也形成了诗歌中感伤主义的主题,这一点可以从《古诗十九首》和建安文学中得到证明。“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自这个时代开始,诗歌的最高主题开始显形为关于生命与存在的哲学追问。而先秦时代人们的生命意识曾经至为朴素,“有限”(人生)是顺从而不是对抗“无限”(宇宙)的,一如老子所言:“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庄子也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而“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众人匹之,不亦悲呼?”这些都告诫人们:不要以个体生命的尺度丈量“无限”以自寻烦恼,而应以认同自然的态度取得宽解才是明智之举。然而汉末以下,上述观念却陡然转为一种生命本体论的感伤主义,不论是登临怀古,吟咏山水,还是感叹季候变幻,时序轮回,无不是表达有限生命对无限宇宙的追慕和感叹。
也许用“生命本体论”的时间观、哲学观和价值观,来概括中古以后中国文学的认识论方法是准确的。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导致产生“奇书”一类有“完整长度”的悲剧叙事的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有一定长度的”,这不是随便说说,悲剧当然地会呈现出一个包括“死亡”在内的完整过程,特别是死亡的结尾。直接呈现这样一个结尾,在修辞的意义上会导致“时间终结”的叙事效果,从美学上则会导致悲剧的体验。“奥古斯汀就用可怕的世界末日比喻个人的死亡”,反之亦然,个人的死亡也同样可以拟喻一个世界的毁灭或“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才是悲剧唤起人的怜悯和恐惧的真谛。生命本体论的世界观和个体生命本位的时间观,催生了中古以后中国文学叙事中的“完整的悲剧”结构理念,它刻意彰显死亡的结局和“时间终结”的完整长度。这理所当然地使叙事的悲剧性得到了凸显。个体生命的短暂,个体时间的“寄蜉蝣于天地”一般的迅疾的“生——死”对立模型,在叙述过程中便演绎为一个“盛极而衰”的修辞与结构模式。当然,它可以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悲壮,也可以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伤,还可以是“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呼的绝望,但很明显,个体生命的经验角度,是他们解释历史和完成叙事的基本视角。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从被给予(从“无”到“有”),到经过少年的蓬勃和盛年的极顶,最终又归于衰老死亡(又回到“无”)一样,时间不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线,而是无数独立又连环在一起的圆。一如老子所说,“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有——无”便成了宇宙大道的基本规律。这样的理念构成了“奇书”内部的时间框架与结构模式:《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其在整体上分别构成了“色——空”、“分——合(——分)”、“聚——散(——聚)”的模式,这根本上也都是《红楼梦》式的“无——有——无”的结构,一个“梦”的经验过程,一支“曲终人散”、“天上人间”的悲歌旋律。可以说,“梦”是中国传统小说最形象和最具美学意义的一个命名,《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注定会成为中国小说的最高典范,它是人生经验的一个形象比喻,“人生如梦”典型地表现着中国文人的生命感知方式,而历史作为“人化的生命经验的对应物”,当然也折射和隐含了人生。
这就是“完整的时间长度”与中国人特有的“生命本体论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悲剧历史美学”。它使中国人的历史观显形为一种悲剧性的生命体验:历史的悲剧——它的完成、终结、闭合和循环往复,同世代的交替、人必然面临的死亡是同一个逻辑,因此离开了人的生命经验的投射,将不会真正读出历史的奥妙。这才是《三国演义》开篇词中所传达的思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通过人生的悲剧体验,而生出了磅礴悲凉的诗意,从而也生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悲剧叙事诗学。言其“特有”,是因为它是在“循环论”的“时间总体性”逻辑下诞生的,与现代性时间观完全不同,历史在我们这里从未呈现为“进步”形态,而总是一种重复。时间本身就像历史中的个体存在一样,只是按照一定的节奏,生死代谢,往复循环而已。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小说“历史美学”的特点:它不指向“未来”一极,也不以所谓“新”为价值指归,在时间的纵向坐标上,不存在一个伦理化的二元尺度,没有过去与未来、“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立,所有的是非成败,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世的代谢化为乌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样,这个悲剧的历史美学又在一定程度上被“中性化”了,并且缘此深化了其哲学意蕴。这是在其他民族的文学叙事中所不曾见到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叙事所发生的变化,就会从根部找到依据和答案。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在80年代初期的“伤痕”、“反思”等表现创伤记忆的叙事中,虽然写作者也试图在其中注入历史的思考,但由于其早已习惯并根深蒂固的“片段式时间修辞法”的作祟,而常适得其反。不管是《伤痕》、《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蝴蝶》等中短篇,还是《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长篇作品,虽然也表现了对一小段历史的悲剧思考和体验,但人为地将历史予以断裂式的处理,却把这些悲剧和苦难喜剧化了。因为这一切已经“永远地结束了”,个人的“蹉跎岁月”和出现的弯曲的历史,并未改变时间“向着未来”开放的总方向。人物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命运重现光明,就像古希腊的那种传奇叙事一样,人物命运的转机是完全外力的“春雷一声震天响”的不期然的结果,“主动权不属于他们,就连爱情也是万能的爱神突然赋予他们的。”这个“爱神”就是政治,时间的政治在历史的尽头等待,“乌云遮不住太阳”,“正义的审判”终将出现,虽然小说的某个主人公可能会死去,但“叙事人”却会幸运地留下来,并且看到作恶者的下场。这样,最终的叙事效果就变成了“青山在,人未老”的喜剧,历史和所谓的“创伤记忆”在被唤起的同时,也被予以集体地删改和忘却。
很明显,当我们把被人为割断的时间连续起来看的时候,伤痕和反思文学叙事的虚伪性就昭然若揭了,它是对以往断裂式时间修辞的简单重复。如果《青春之歌》有续集,林道静能够在漫长的战争与政治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话,那么她一定又会成为伤痕反思文学的主人公。一旦我们将这段历史整体来看,喜剧的美学就会转化为荒诞、荒谬和反讽的美学。
真正有“完整时间长度的叙事”的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寻根文学”作家们试图为当代文学寻找这种长度,但却因为更注重“文化”和“民俗”等平面性的东西,而使作品的历史感受到了限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通过展示种族生命力的“降幂排列”式的历史衰败,而呈现了一种“壮美的悲剧”,但它仍留有寻根文学的观念——年轻叙事人“我”一直试图寻求与“爷爷”、“奶奶”和“父亲”所代表的历史的“对话”,所以“时间的终点”——最终的“死亡”在事实上仍未得到凸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在时间修辞方面则有了新变:它刻意消除了寻根小说中生硬的“现代意识”,同时去除了进化论和伦理化的历史主义,它突出的是“时间的延续”而不是“时代的断裂”。而这正是先锋文学的叙事经验受到广泛接受和赞赏的一个原因。当代小说的修辞与美学立场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回溯到历史的永恒维度。以苏童的《米》为例,它所写的进城农民五龙的传奇一生,可以说是延续了一个底层生存者永恒的命运与性格逻辑。没有“成长”,他是从一个被欺压者争取到与欺压者同样的地位、然后又对他人施以欺压、最后陷于败落并众叛亲离地死去的悲剧,他保留了一个农民骨子里的信念——对男权、财富、性和暴力的嗜好,而这一切又归根结蒂到对“米”的崇拜和迷信,他死时随身所带的宝箱中装满了米而不是别的东西。格非的《敌人》也是写了一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悲剧,财富的轮回与风水的轮转,“关于敌人的恐惧和想象才是真正的敌人”这样一个秘谶。巨富的赵家被一场无名大火烧去了大半家财,其后人一直生活在“谁是纵火者”这样的恐怖和疑问里,三代之后,其实“谁是敌人”的追问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家长赵少忠却被这阴影压垮。他在无意识中产生了强烈的毁灭倾向,先后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使家族血缘的链条被彻底中断,这样关于“敌人”的历史记忆也就最终中断了。它揭示了一个古老而又有现代意味的道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有着一个支配着其自我毁灭的东西,其死敌不是别的,就是它自我“轮回”的意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悲剧性的叙事终点替代了过去的片段性、阶段性修辞。这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
真要形象地展现时间修辞的变化,还要借助一部最典型的小说,即王安忆的《长恨歌》。因为它与前面的革命时代例证《青春之歌》之间,构成了极有意味的对比。这两部作品,无论在作者的观念、在小说主人公的处境、身份、人生选择与命运之间,在两部作品的题材、叙事结构、修辞与美学风格之间,均构成了奇妙的比照关系。首先,两部小说的最大不同表现在主人公的价值趋向上,林道静和王琦瑶这两个生活在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女性,却选择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竭尽全力要踏入“时代”的主流式的人生轨道,另一个则是要重复前人已重复了无数次的古老人生之路;一个用全力试图改变女人被规定的古老命运,另一个则顽固地逆来顺受地接受这样一种命运。然而这仅仅是个外在的解释——是谁决定了她们如此不同的命运?是作者吗?表面看是杨沫和王安忆这两个置身于不同时代的作家,分别“支配”了她们的命运,然而直接在小说叙事层面发生作用、并使两部作品产生巨大精神鸿沟的原因,却是两种不同的时间修辞。《青春之歌》的“小说时间”是结束于主人公革命生涯的成熟与革命高潮的到来之际,这个终结点让人相信,在此之前的一切挫折和失败,都是为了最后的“胜利”;而《长恨歌》则是对这一“时间将来”的持续面对,它用“延伸的叙事”推翻了前者的叙事结构。在这里,时间一意孤行地向前流动,越过了青春的欢乐而直抵暮色的悲凉。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蒋丽莉的命运,恰好反证了林道静被省略的“未来”,她在革命胜利后的岁月,并没有始终占据精神的高点,相反却体会了人生的另一种失败。胜利的节日和欢庆并没有改变她回身面对日常生活、进入上海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市民生活氛围时的命运,她仍然是一个命定的“灰姑娘”和“局外人”——就像王琦瑶面对她的主流与红色生活时是个“局外人”一样,最后她在抑郁中不幸患肝癌而死。时间的延伸改写了“青春”的一切——天下还有不散的筵席吗?也许这样一种改变应归于历史本身无情的延伸或循环,杨沫在写《青春之歌》时还不能看到这样一个结尾,而王安忆则必须面对它。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如此不可同日而语的叙事,其实原本不过源于这样一点不同:前者是按照革命的“集体时间”来完成她的“青春美学”的;而后者是按照单个人的“个体生命时间”来完成她的“暮年(死亡)叙事”的。
构成生动的戏剧性对照的还有王琦瑶与林道静这两个人物。她们之间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与不同,王琦瑶重复了无数中国古代女性的命运:美丽的容颜,曾经的花期,不可理喻的阴差阳错,始料不及的蹉跎磨难,让人扼腕的悲剧,令人长叹的结局。世有白居易长歌当哭的《长恨歌》,曹雪芹哀情浩荡的《红楼梦》,俱是缘于四个字:“红颜薄命”。王安忆之作《长恨歌》,显然也是仿照了白居易的诗意。我想这是一个标志,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叙事逻辑的归复,这一方面是由它在题材内容上与中国传统叙事之间酷似的关系决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种文化情境及其逻辑的循环——精神的沦落和世纪的终了,尤其是作家精神认同的彻底改变,使它产生了强烈的历史闭合感,一维的进化论时间理念在这样的情境中当然会变得幼稚短浅。
显然,主人公的死亡和“完整的历史长度”的归复,成为了当代小说悲剧性特征得以呈现的基础。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还有莫言的《丰乳肥臀》。它通过一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伟大母亲的一生,书写了一个世纪的血色历史。她的一生所具有的历史影射力,正好对应着20世纪中国的一个完整长度:风雨如晦,沧桑变迁,各种政治力量走马灯般地争相表演,但最终又迅速湮没在历史之夜和时间的黑洞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不请自来,侵犯着原生和苦难的民间,而最后只有民间和底层人民对苦难的默默承受;同时这承受也使她们获得了永恒与自在的力量,使她们在一切外来的短命的“文明”与政治的侵犯面前,显出了本然的高贵和不朽。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它呈现了历史的“完整的逻辑”,而不是阶段性的胜利或者失败,“时间走到了尽头”,悲剧的本质和命运感、历史的闭合与永恒轮回的意志顽固地呈现,这无疑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一部有着强烈现代感和非常“西化”的悲剧——它的主人公最后甚至皈依了基督教。但在此至关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时间修辞所产生的中国式的悲剧结构。
相应地,与传统时间观念的恢复同时出现的,是对政治化和社会化时间概念的淡化。这种刻意的消除,使得叙事的“编年史”的性质被代之以永恒的存在性质,由此所谓“生活”也被“生存”和“存在”所取代。在先锋小说中,时间被处理成抽象的东西,它或者从叙事的具体功能中消失,或者被故意颠倒,成为“固体”的事物而不是“流动”的维度。在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中,一封内容为“速回”的电报,让主人公回到的不是某个地方,而是过去的某个时间;但接下来某个时间又变成了刑罚之一种。这样,历史具体性和纵向维度的消失,换来了历史的哲学内涵的彰显。这也是使先锋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能够越出通常的社会主题与具体的历史内容,而接近于哲学、人性与存在的深度的一个原因。
余华曾明确阐述过他的时间观:“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排列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再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它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出新的含义。时间的顺序在一片宁静里随意变化。”这就是说,作为经验和某种生活的启示录,在关于记忆的某种叙事中,时间恰好不应用突出自己的刻度来夸大其作用,当它刻意显示自己的具体性时,恰恰缩小了自己的作用,当它回到时间的本来意义(即永续)时,也就变成了存在与启示。在这方面,《许三观卖血记》是个例子,在一些论者看来,它也许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时间常态的社会性标志的淡化,却使它“溢出”现实主义的设限。因为余华并没有把当代社会历史坐标中的时间要素推向前台,而是出奇制胜地用“卖血”的频率代替了时间的现实刻度,使之成为生存的刻度。这样叙事节奏也就成了生命与生存的节奏。它由慢到快,由疏到密,再戛然而止,这种节奏本身即揭示了作品的主题,也揭示了个体人生的速率,即人生犹如卖血,是“用透支生命来维持生存”的,同时,时间在人生中是“加速度”的,死亡也是如此。《许三观卖血记》由此成为一部哲学求问录,而不只是一部小说。
与此同时,余华又说:“在我越来越接近30岁的时候……在我规范的日常生活里,每日都有多次的事与物触发我回首过去,而我过去的经验为这样的回想提供了足够事例,我开始意识到那些即将到来的事物,其实是为了打开我的过去之门。因此现实时间里的从过去走向将来便丧失了其内在说服力。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如果我此刻反过来认为时间过去只是时间将来的表象时,确立的可能也同样存在。”时间在这里显然又具有了其内在逻辑,它的过去和未来在冥冥中是统一的,并未有任何本质的改变,这使余华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哲学之间产生了联系。《活着》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证:时间在这部作品中呈现了复杂的情形,主人公福贵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在“时间过去”里的人,从他开始赌输那一天起,实际上他的一切的“将来”都已注定要汇入这一“过去”之中。当他所有亲人连同他的财产一起化为乌有时,他的“活着”便成了两种时间——生者(还在延续的时间)和死者(已终止的时间)之间的一种比照和对话。天上与人间,生死两茫茫。这类似于《红楼梦》和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那种时间模式,因此它非常感人,具有某种“煽惑性”。这种格局既能显示出人生的短暂与无常,又可以在叙事上显出“未亡人”余生的漫长与凄凉——“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它所昭示的是,人生就是被剥夺的过程,一点点开始,其实死亡从年轻时代就早已开始了。人生如同赌徒,赌得干净彻底时,他的生命才会终结。时间在余华这里具有了哲学的意义,由于成为“哲学”,而使他关于苦难、命运、人性、历史的叙述得以超越了历史本身。《活着》的意义当然不排除它真实而严峻的历史批判内涵,但它更是对于生存的哲学追思。正是得益于其时间意念,它的“简单”使得它成为了一部复杂的作品。余华在看似不经意间,巧妙地运用了他的时间修辞,构造出一个近似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情境的命题——历史并未呈现为“进步”与“光明”,相反在哲学的意义上,除了个体和普遍的共同悲剧与终结(死亡)体验之外,一无所有,小说感人的诗意正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