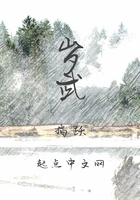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天志》上。参考《天志》中、下及《法仪》篇)
这个“天下之明法度”便是天志。但是天的志是什么呢?墨子答道:
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篇。《天志》下说:“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与此同意)。
何以知天志便是兼爱呢?墨子答道:
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仪》篇。《天志》下意与此同而语繁,故不引)。
第二,兼爱天的志要人兼爱,这是宗教家的墨子的话。其实兼爱是件实际上的要务。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通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
《兼爱》中、下两篇都说因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要兼爱。
第三,非攻不兼爱是天下一切罪恶的根本,而天下罪恶最大的,莫如“攻国”。天下人无论怎样高谈仁义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读《非攻》上)。墨子说:
今天下之所〔以〕誉义(旧作善,今据下文改)者,……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欤?……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不〕免攻伐并兼,则是(有)(此字衍文)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非攻》下)
墨子说“义便是利”(《墨经》上也说“义,利也。”此乃墨家遗说)。义是名,利是实。义是利的美名,利是义的实用。兼爱是“义的”,攻国是“不义的”,因为兼爱是有利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攻国是有害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所以《非攻》上只说得攻国的“不义”,《非攻》中、下只说得攻国的“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你看他说:
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
又说:
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之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非攻》
中、下)
可见墨子说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是“兼爱”的真义,也便是“非攻”的本意。
第四,明鬼儒家讲丧礼祭礼,并非深信鬼神,不过是要用“慎终追远”的手段来做到“民德归厚”的目的。所以儒家说:“有义不义,无祥不祥。”(《公孟》篇)这竟和“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话相反对了(《易·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乃是指人事的常理,未必指着一个主宰祸福的鬼神天帝)。墨子是一个教主,深恐怕人类若没有一种行为上的裁制力,便要为非作恶。所以他极力要说明鬼神不但是有的,并且还能作威作福,“能赏贤而罚暴”。他的目的要人知道:
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男女之为无别者,有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孙诒让云:退是迓之讹,迓通御),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明鬼》)
墨子明鬼的宗旨,也是为实际上的应用,也是要“民德归厚”。但是他却不肯学儒家“无鱼而下网”的手段,他是真信有鬼神的。
第五,非命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来墨子不信命定之说,正因为他深信天志,正因为他深信鬼神能赏善而罚暴。老子和孔子都把“天”看作自然而然的“天行”,所以以为凡事都由命定,不可挽回。所以老子说:“天地不仁”,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墨子以为天志欲人兼爱,不欲人相害,又以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若祸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可得福;不作恶事,也可得祸了。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说,便没有人努力去做好事了(“非命”说之论证,已见上章)。
第六,节葬短丧墨子深恨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又在死人身上做出许多虚文仪节。所以他对于鬼神,只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虚文。他说儒家厚葬久丧有三大害:(一)国家必贫;(二)人民必寡;(三)刑政必乱(看《节葬篇》)。所以他定为丧葬之法如下:
桐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节葬》)。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节葬》)。无椁(《庄子·天下》篇)。死无服(《庄子·天下》篇),为三日之丧(《公孟》篇。《韩非子·显学》篇作“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服丧三月”。疑墨家各派不同,或为三日,或为三月)。而疾而服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节葬》)。
第七,非乐墨子的非乐论,上文已约略说过。墨子所谓“乐”,是广义的“乐”。如《非乐》上所说:“乐”字包括“钟鼓琴瑟竽笙之声”,“刻镂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可见墨子对于一切“美术”,如音乐、雕刻、建筑、烹调等等,都说是“奢侈品”,都是该废除的。这种观念固是一种狭义功用主义的流弊,但我们须要知道墨子的宗教“以自苦为极”,因要“自苦”,故不得不反对一切美术。
第八,尚贤那时的贵族政治还不曾完全消灭,虽然有些奇才杰士,从下等社会中跳上政治舞台,但是大多数的权势终在一般贵族世卿手里,就是儒家论政,也脱不了“贵贵”、“亲亲”的话头。墨子主张兼爱,所以反对种种家庭制度和贵族政治。他说:
今王公大人有一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尚贤》中)
所以他讲政治,要“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
第九,尚同墨子的宗教,以“天志”为起点,以“尚同”为终局。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
尚同的“尚”字,不是“尚贤”的尚字。尚同的尚字和“上下”的上字相通,是一个状词,不是动词。“尚同”并不是推尚大同,乃是“取法乎上”的意思。墨子生在春秋时代之后,眼看诸国相征伐,不能统一。那王朝的周天子,是没有统一天下的希望的了。那时“齐晋楚越四分中国”,墨子是主张非攻的人,更不愿四国之中哪一国用兵力统一中国。所以他想要用“天”来统一天下。他说: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立之以为正长。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孙说傍与访通,是也。古音访与傍同声)。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尚同》上)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这叫做“尚同”。要使乡长“壹同乡之义”,国君“壹同国之义”,天子“壹同天下之义”。但是这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天子若成了至高无上的标准,又没有限制,岂不成了专制政体。所以墨子说:
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夫者,则天菑将犹未止也。……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尚同》中)
所以我说“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天志尚同的宗旨,要使各种政治的组织之上,还有一个统一天下的“天”。所以我常说,墨教如果曾经做到欧洲中古的教会的地位,一定也会变成一种教会政体;墨家的“钜子”也会变成欧洲中古的“教王”(Pope)。
以上所说九项,乃是“墨教”的教条,在哲学史上,本来没有什么重要。依哲学史的眼光看来,这九项都是墨学的枝叶。墨学的哲学的根本观念,只是前两章所讲的方法。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他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不过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只顾眼前的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张一种“贤人政治”,要使人“上同而不下比”。他又恐怕这还不够,他又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张把“天的意志”作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因此,哲学家的墨子便变成墨教的教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