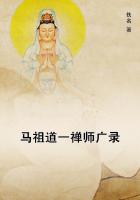然而“一·二八”的炮声冲击了他一心为纯艺术、为推动文化进步而写作出版的理想。他以作家的敏感嗅出战火在步步逼近,逐渐从唯美转向了现实。在写文艺作品的同时,他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时事评论。“八·一三”日军侵犯上海,他在战争打响的前一刻方才携家眷和工友逃离杨树浦,家和印刷厂都留在了敌占区。一夕之间,他几乎沦为无产者。眼看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军占领,加上切身的遭遇,他义愤填膺,自发地组织和他一样被迫滞留在上海的文朋画友,以笔作刀枪宣传抗日。
他在一篇《编辑谈话》里说,“我们看见新近发表的抗战诗歌,几乎每一首都多多少少要提些‘风花雪月’,好像没有这一类字眼,便不成为诗的样子……”可以看出,这时的邵洵美已经没有了“吟花咏月”的心情。在《中美日报》他的《金曜诗话》专栏里有一篇《抗战中的诗与诗人》,他写道,“……所以,抗战中,谈起诗来,我们可以说:‘发生宣传效用的诗,便是好诗。’在抗战时间的诗已不能与太平时间的诗相提并论了,况且也不必相提并论的。”
楼适夷在“反胡风运动”中
吴永平
笔者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尾声”中曾述及当年文艺界人士在“反胡风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写道:“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许多知名的文艺界人士都曾被动或主动地‘表态’或‘深入揭露’。他们大都与胡风有过交往,而当他们的参与超出了‘表态’而到达‘揭露’的层次时,由于没有了人事方面的顾忌,有时也吐露出一些在正常的环境下所不能明白道出的‘心声’。”接着,笔者详述了姚雪垠当年如何“兴高采烈”地撰文参与批判胡风的过程,还顺便提到楼适夷如何在“反胡风运动”中“侥幸逃脱”的小插曲,并引证了他的一段回忆:
“(运动中)有人找我谈话,1946-1947年在上海《时代日报》工作时,为什么发表了‘胡风分子’那么多文章。果然‘东窗事发’,这一回不是隔岸观火,而是火烧到身上来了。其实那时《时代日报》除了我这个副刊,还有(叶)水夫编的一个《星空》,算起来也发表不少这类稿子。《时代日报》负责的是姜椿芳,三个人检讨得不坏,《文艺报》发表了,《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而且都得到了稿费,便联合在北京的陈冰夷、林淡秋‘时代’同人五个人到四川饭店大吃了一顿。吃得酒醉饭饱,高兴自己过了‘关’,可没想到胡风怎么在过日子。”①
楼老把“逃脱”过程写得很简单、很轻松,实际情况却是相当复杂、相当沉重。
他是胡风的老朋友,早在一九三二年冬便与胡风相识,比聂绀弩晚一年,与冯雪峰同时。他还是胡风人生经历中几个重要时期的见证人:胡风在日本从事所谓“一些不可告人勾当”的时候(1932年至1933年),楼曾受“上海临时中央”的委派赴日本,通过胡风的关系找到日共中央,商谈“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筹备事宜,并受“文总”的委托调解胡风所在的“新兴文化研究会”与另一留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宗派纠纷;胡风在武汉创办《七月》时期(1938年),楼曾多次参与胡风以“七月社”名义组织的“座谈会”,并与胡风分别担任《新华日报》副刊“团结”和“星期文艺”的主编,关系一度相当密切;胡风对进步文坛进行“整肃”期间(1946年至1948年),楼进行了积极的呼应,在其主编的《时代日报》副刊“文化版”上大量刊发“胡风派”的文章;胡风为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关于“国统区文艺”报告苦恼时(1949年),楼曾当面责备胡风“不该不提意见”,伤心得竟至“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来”②……
以楼老与胡风如此深厚的关系,他要想在建国初期“胡风派”与“主流派”的历次交锋中“隔岸观火”,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几乎做到了——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中宣部召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周扬主张让几位与胡风有过交往的党内人士(林默涵、冯雪峰、丁玲等)担任主要发言人,周恩来则建议再增加“批评”过胡风的胡绳和何其芳。他们都没提到让楼适夷参加。
一九五四年年底,在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召集的“关于《红楼梦》问题及《文艺报》”的第四次会上,“战线南移”,批判的矛头突然转向胡风。黄药眠、康濯、罗荪、袁水拍等在发言中都对胡风进行了指责,聂绀弩也站出来揭发朋友胡风“过去反党,现在反党”,但楼适夷却保持着缄默。
一九五五年初邵荃麟为作协党组起草致中宣部和中央的报告,提出一份“为了进行对胡风思想批判”而“都要负责写出文章”的撰稿人名单,其中有胡风的老朋友冯雪峰、聂绀弩,但还是没有楼适夷。
楼适夷所以能置身事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他对文艺理论缺乏兴趣,从未参加过“论争”;原因之二是抗战期间他没有去过重庆,没有卷入胡风与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冲突;原因之三是解放前夕他曾奉中共华南局工委领导的指示“批评和帮助”过胡风,组织上对他的政治态度是信得过的。第三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楼适夷奉命撤往香港后,与邵荃麟、叶以群、聂绀弩分在同一个党小组。经过一段有组织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他们逐渐贴近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③。一九四八年三月冯乃超、邵荃麟主持的《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激烈批判,胡风其时尚在上海,便联络一些青年作家进行凌厉的反击,笔仗打得不可开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风奉命撤往香港后,中共华南局“文委”委员邵荃麟指派楼适夷出面找胡风谈话,想说服他也转到“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上来。楼适夷在《记胡风》中忆及这次谈话,写道:
在香港工委管文艺工作的邵荃麟同志把我叫去,告诉我:“全国快解放了,今后文艺界在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这回掀起对他文艺思想论争,目的就是要团结他和我们共同斗争。你同胡风熟悉,你应该同他谈谈!”这是一个重要使命,我当然是坚决执行,保证完成。我特地把胡风请到九龙郊外的我的寓所里,和他谈了整整半夜……这一晚的谈话,大部分是我谈的多,他说得少。我谈得很恳切,很激动,他看着我一股真诚的样子,只是微微地笑,很少答腔。看来我的话其实没有触到点子上,当然说服不了他,使命算是失败了。
当年,黄永玉就住在楼适夷的隔壁,曾闻楼、胡的这次恳谈。他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忆及:
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胡风先生找适夷先生来了。适夷夫人黄福炜在新四军还在什么解放区当过法官,人很善良精明,可是她不会做菜,还向我爱人“借”了两个菜请这位贵客。胡、楼二位先生就这么一直谈到三更半夜,其中楼先生又敲门来“借”点心。可惜我当时不懂事,听不懂他们谈的什么内容,只觉得胡先生中气十足,情绪激愤。楼先生是个厚道人,不断说些安慰调解的话。
楼适夷虽有“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党性,却“谈不出什么道理来”④,结果当然是“说服不了”;胡风“情绪激愤”,是诧异于昔日的朋友为何都这么快地翻脸,桂林时期(1942年至1943年)邵荃麟的文艺思想与他很接近,如今却提出要批判“所谓追求主观战斗精神的倾向”⑤;重庆时期(1943年至1944年)乔冠华曾与他一起反对整风中的“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倾向,如今却把他自己首创的“到处都有生活”观点不点名地批判一通⑥;上海时期(1946年至1947年)楼适夷曾公开发表文章,全力支持他们对文坛进行的“整肃”⑦……一到香港来,他们就全变了。楼、胡的这次长谈是中共文艺领导在全国解放前对胡风的最后一次“批评和帮助”,“使命算是失败了”,但楼的“党性”却长留在邵荃麟等文艺领导人心中。顺便说一句,楼的“党性”之强,曾一度达到了令老朋友聂绀弩咂舌的地步。聂在“反胡风运动”中曾被“隔离审查”,事过之后,他与楼有过谈话,“楼适夷问我在反省期间是否相信党,我说,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他说,即使送你去枪毙,你也应该相信党。我说我很惭愧,我就是没有达到这一步。”⑧
建国后,上层从未视楼适夷为“胡风派”,也许与认为他的“党性”比较坚定不无关系。
因此,“反胡风运动”深入开展后,楼老“隔岸观火”的好日子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即《人民日报》号召“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时期(5月18日起),楼适夷发表了第一篇表态文章《真面目掩盖不住了》⑨,文中除了大量引用该报“第一批材料”中的文字之外,也披露了一点“心声”。他写道:
长期以来,党的文艺工作者和党外的进步作家们,不断地对胡风做了许多批评和帮助,耐心地等待他的自觉。而胡风不但完全拒绝批评,拒绝检讨,而且加紧了他进攻的部署,一直发展到向党中央提出他的所谓意见书,并认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和对《文艺报》的批评,是他公开向党进攻的最好的时机,而终于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反党的狞恶的面目。
文中说“党的文艺工作者”曾对胡风进行过“批评和帮助”,当然包括一九四九年初他在香港与胡风的那次“失败”的谈话。不过,以楼老对胡风的了解,他本不该轻信报纸上的所谓“材料”,而应有自己的判断。为何人云亦云?楼老晚年曾对此有过自省,他在《记胡风》中写道:
(胡风派)从文学流派的所谓“小宗派”,一下子突然变成“明火执杖的反革命集团”,这还得了!当然得积极响应。《列子》中有一条寓言,某翁丢失了一把斧子,怀疑是邻人某某所偷,暗中窥查,越看越觉得这某某很像是偷斧子的人。不管什么老朋友,大义灭亲,我就是这样,以为胡风真是偷了斧子了。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那时人造的阶级斗争急风暴雨仍在神州大地上肆虐,集体无意识的领袖崇拜已外烁为时代精神,刚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的善良的人们绝不敢对党抱有任何怀疑,他们宁可怀疑自己的眼睛和头脑,牺牲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疑人偷斧”,这是何等可悲的历史宿命!
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人民日报》号召“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期(5月31日起),楼适夷又发表了第二篇表态文章《刻骨铭心的教训》⑩,文中除了沿袭报纸上的一些套话外,也披露了一点“心声”。他写道:
从这个胜利中,我们所得到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这是一个用怎样的代价所换来的胜利?不是一个短的时期,而是二十多年,这个革命的叛徒,美蒋匪帮的最忠实的狗,死硬的阶级敌人,潜藏在我们的队伍里,日日夜夜地进行其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阴谋。他们把中美合作所训练出来的特务送到我们党里来了,我们接受了;他们把蒋介石的信徒,胡宗南的走狗送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岗位上来了,我们接受了;他们把恶霸地主、还乡团员、对人民有血债的分子送进我们国家的文化机关里来了,我们也接受了;他们拉走了我们队伍中一些蜕化变节的分子,让他们在我们的组织内替他们当坐探,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到处散布对党对人民的疯狂的仇恨,我们不知道。我们把最可怕的阶级敌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他握手,对他微笑,团结他,争取他,认为他们只是思想上有问题,善意地帮助他们,耐心地等待他们,以为最后他们一定会被党和人民的力量改进,这是怎样的一种“天真”和麻痹。
三个“我们接受了”,两个“我们不知道”,一个结论“这是怎样的一种‘天真’和麻痹”,前两点是沿袭报纸上的说法,后一点是具有个性的表述。“我们”与“他们”之间“二十多年”来的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却是貌似清醒实则糊涂的认识。顺便说一句,时人常以“天真”或“老天真”来喻楼适夷,这是对他在某些历史阶段中政治上的轻信与盲从的恰当概括。晚年楼老在致友人信中曾自省道:“我这人说好听点叫‘天真’……”他也许已经深刻地反思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