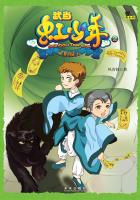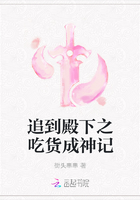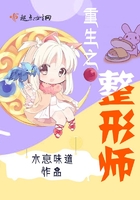成电虽然新建,但行政设施也属一流,单算接待厅、办公室的高档羊毛地毯,就是偌大一笔开支,经过一个冬天霉阴侵蚀以后,拿出来铺在主楼广场地上晒太阳,广场空地几乎全被五颜六色的地毯覆盖殆尽,这也算得上成电难得一见的风景线。
成电,从多方面、多角度展现了无限的魅力,其魅力源于雄厚的师资力量,源于充满活力的专业设置,源于具有艰苦奋斗力争第一的人文精神,更源于勇于创新争取辉煌的理念,所以这一切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成电学子不断奋发、勇往直前。50年过去了,成电已是今非昔比,更加辉煌的成就,让我们这一代为成电贡献了一生年华的老教师为之激奋、为之心动、为之骄傲、为之期待。成电,我永远的母校;成电,我永久依靠的帆船,一定会驶向更加光明的明天!成电的明天会更好!
郭老与我校校名
郭民邦
为了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1955年,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拟筹建一所培养无线电工业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并呈报国务院请求审批。在这份请示报告中,学校最初的命名是“成都无线电技术学院”。后来,第二机械工业部在给学校颁发公章时文为“成都无线电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1956年春,在第二机械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共同召开的学校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上,经讨论,筹委会副主任陈章教授、冯秉铨教授、周玉坤教授等认为:新校师生是由南京工学院通讯系、交通大学电讯系、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合并组成,而校名中的“无线电”不能涵盖有线电。因此,建议更名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上报审批。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校名经上级批准后,高等教育部给我校颁发了一颗铜质、直径4厘米的圆形公章。当时,我们希望毛主席给我校题写校名。经请示中央办公厅,未果。接着,我们请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题写,赵尔陆部长说,你们去找“翰林院”的人写吧。后来,吴立人主任同意我的建议,去请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题写。我持学校介绍信,直赴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室。一位女秘书接待了我。我说,为了鼓励我校全体师生向科学进军,请郭老能在百忙之中为我校校名题字。这位秘书立刻答应,并叫我星期五下午去取。按约定时间,我来到中国科学院,郭老在里屋埋头办公,我未敢打扰。女秘书拿了一张印有中国科学院字样的红头信笺,上有毛笔书写的两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横排),其中第二排前面画了一小圈。女秘书告诉我,郭老说,用画了圈的。(因为未画圈的那行,“成”字略小,而“院”字稍大)。郭老题写的校名,筹委会的同志都很满意,于是赶紧寄往上海,制备教师和学生的校徽。第三次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7月中旬,在成都召开并宣布结束筹备工作。7月15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公章正式启用。建校初期的院刊刊头也是用的郭老题字。只可惜,当时院刊编辑许伽同志将这题字借去制版,我催要过多次,却再也没有找回原件了。
已去世,校领导把题字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想,唐太宗写的《圣教序》想要晋人王羲之的字,唐僧怀仁奉命集之。这使我受到启发,“电”“学”两字采用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子”采用郭老手书《毛主席诗词37首》中的《采桑子》中的“子”,“技”采用“唯有花枝俏”的“枝”字,将“木”旁的接线去掉一点,改为提手。“科”采用郭老题的《中国科学》中的“科”字,“大”就多了,采用的是《科学大众》的“大”字,于是就组成现在使用的校名题字了。
成电已是第二故乡
——冯志超追忆在成电的岁月
1956年7月,上级部门一纸通知,华南工学院33岁的冯志超教授就和妻子黄月华离开生活多年的广州,作为该校第一批被抽调来蓉人员,将全家移居到成都,和交通大学以及南京工学院的师生一起,组建起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从此,这个地道的广州家庭,在成都一住就是50年,也见证了电子科技大学这50年来的风雨历程。
“扭着秧歌”去上课
刚到成都的时候,学校一切都还在修建中,甚至连教师的宿舍也都还没建好。学校只好为老师们包下东大街的一家叫做裕中的旅馆来做宿舍。一直到9月份,冯老才住进了学校自己的教师宿舍。
当时全校也只有5栋教师宿舍,房间都是木地板的,吃饭取暖也全靠烧木材,后来才开始烧蜂窝煤,房子上面也都有个很大的烟囱。冯老笑着说,那个时候不觉得木地板好,还总是羡慕洋房里的那种地砖,如今全反过来了,又都把水泥地铺成了木地板。
那个时候学校门前的路很难走,全部都是泥巴路。9月份是成都的雨季,每次雨后路就更加的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鞋子上就会粘上很多黄泥巴,越走粘得越多,整个脚都几乎陷在泥里,走起路来难免就一拐一拐的,“我们叫它‘扭秧歌’”,冯老笑着说。
当时从南院到主楼的公路也都是泥巴路,旁边还有条小水沟,不宽,但一步也跨不过去。为了方便通行,当地人在水沟上面搭了块棺材板当作桥。“当时有的老师就不敢过,因为觉得是棺材板,有忌讳,心里不舒服,另一个原因是有点害怕,不安全吧”,冯老说。
最开始南院到主楼的那条路是不开放的,不允许车辆通过。后来才慢慢开放,但还是有严格的时段限制。至今,那条路的两端也还是有允许通行的时间限制牌的,并常有交警把守。
由于时间仓促,等学校已经正式开课的时候,主楼的楼梯都还没有扶手,“但是上课总不能推迟的”,冯老开始了他在成电的教学生涯。
东草场上的第一次开学典礼
刚建校的时候,现在学校网球场那里还是一个操场,老校友们都叫它“东操场”(现逸夫楼位置)。50年前电子科技大学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的。那里时常会放一些露天电影,这种如今几乎只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娱乐形式,在当时可是冯老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都是很单纯的,学生们也都很用功,课后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冯教授回忆说。
建校伊始,一切都还在起步阶段,条件也相当简陋。“我记得,一直到1957年‘反右’开始,我们都是借人家的地方开大会”,冯老对那时的艰难记忆犹新,“更没有像现在这么气派的体育馆。”
最“先进”的电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成都,交通还极为不发达,那时的成电还属于国防管辖区,只允许自行车、鸡公车和行人通过。“那时全成都市仅有6条公交线路而已,从1路到6路,只有这6条,不像现在”,冯老边说边拿出成都市地图指给我们看,“全成都大约都有100多条公交线路了。”
和当时不发达的交通系统相对应的是,那时的通信系统也是非常简陋。冯老回忆说,那时的电话还是“共电式”的,把听筒拿起来后,需要接线员帮你把电话拨出去。而成电的总机却有着200门的自动电话,也就是说校内的这200门之间是可以直接拿起来就拨号的,虽然拨到校外去还是需要接线员转,但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真不愧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没有学位的研究生
1956年冯老刚到成电的时候,就已经是物理教研室的主任了,负责两个大班的物理教学工作。那时候一个年级是7个大班,一个大班有210个人左右,一个年级也就大约1500人。
冯老说,那个时候全校总共只有5个系,20个左右的专业,全部都是工科,没有文理科。
那时,学校里还有许多苏联专家来帮忙组织教学建设,还开设了在当时算是很新兴的半导体专业。苏联专家还负责带了一些专业的研究生,只是当时的研究生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据冯老回忆,刘盛纲院士就是当时微波专业的第一批研究生,并还兼任了苏联专家的业务翻译。同一时期的,还有张其劭和关本康,他们三人被合称为成电的“刘关张”。
成都已是第二故乡
从1956年7月到成都,至今,冯老已经在成都待了整整50年了,“当时的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比较单纯,只要组织一宣布,我们就来了”。冯老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我在成都待的时间比在广州待的时间都要长得多啊!”冯老无不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前学校都是没有假期的,我也就没回去过广州,文化大革命后,才找机会回去过几次,现在老了,人也走不动了。”
“刚来成都的时候,饮食上有点不太习惯,觉得吃的东西又麻又辣的。有次四川省委请教授、副教授们吃饭,端上一盘鸡来,我们一尝,好麻好辣啊!但是我们又必须要习惯,所以慢慢地也就好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不过直到现在也还是不能吃太辣的东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吃点辣的也不行,但一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还是都做广州口味的菜式来吃。”
作为一个在成都已经生活了50年的广州人,冯老亲身经历着成都这50年来的种种变化,也亲眼见证了电子科技大学这50年来的风风雨雨。成都已经成为了这位满头银发老人的第二故乡,电子科技大学也成为他的第二个家。
刘春晓杨仪玮
在农场劳动的日子
刘亚军
离开母校,弹指间已飞过30余载。如今当夕阳西下回首往事的时候,母校的生活却愈发清晰起来,同学们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朗朗笑声时常在耳边响起,一个个青春的身影又在脑海中泛活。
俱往矣,在诸多往事中,到校农场劳动的日子格外令我怀恋。我是1973年入学的。那时学校在仁寿县有一个农场,有稻田十几亩,甘蔗林一片,还种有许多蔬菜、花生等等。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学生轮流到农场劳动几天,每次一、两个班,一百多人。这相当于现在放长假一样令我们高兴。一来可以放松一下被高等数学折磨惨了的大脑(我们大部分同学是初一、初二水平),二来是可以改善伙食。我们在学校天天吃的是发黄的陈米饭,见不到油珠儿的盐水煮菜,其中最被大家深恶痛绝的是无缝钢管儿(空心菜)。而在农场我们天天吃雪白的香喷喷的新米,菜也比学校的油水多,每次还可以杀一只猪慰劳大家。而且那里风景如画,绿竹掩映,小河潺潺,对于我这个没下过乡的北京娃儿来说简直太美了,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巴适得很!于是乎兴冲冲坐着敞篷大汽车向校农场挺进,一路欢歌笑语。
我们先后去农场劳动过三次,干过插秧、拔秧苗、收甘蔗等农活。但是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到农场。我干的却非农活。分配工作时,班长指着我说:“你,到厨房帮厨去吧!”我连忙一路小跑来到厨房。大师傅分配我切菜,不一会儿,我把手指切伤了,师傅说,到井台上洗菜吧!那时农场没有自来水,用水都要从井里用系着绳子的小桶提上来,我想这个还不容易,可我就是摆弄不好那个桶,它轻飘飘浮在水上怎么也不进水。大师傅告诉我,要轻轻摆动绳子,让小桶倾斜,等水进去后,再上下拉动,水桶就打满了。我终于学会了打水,一桶、两桶、三桶……打上清凉的井水,把个萝卜洗得白生生菠菜洗得绿汪汪,我一辈子也没洗过这么多菜啊!足够一百多人吃两顿呢。低头一看我脚上的解放鞋(胶鞋)都被井水浸透了,手指的伤口已被水泡白了,索性把包伤口的布条撕下来扔掉,用一根皮筋把两条辫子绑在一起,又起劲儿地干了起来。晚上同班的女生悄悄从兜里掏出一把花生来慰劳我,说是从地里偷挖来的,花生壳上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剥出粉红色的尚不饱满的花生米放到嘴里,嚼起来甜丝丝的,不舍得一下子都吃光,就用手绢儿包起来放在枕边。哪知夜里老鼠前来“偷营”,不仅嗑光了花生,还把我的蚊帐咬了个碗口大的洞,由于白天洗菜累了,睡得好香,全然不知。第二天换了工种,大师傅派我和我们班的小凤(姓凤,上海籍陕西小伙儿)负责蒸馒头,原因是我们两个是北方人。我心里有点儿打鼓,我只吃过馒头,哪里蒸过馒头呀?小凤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看我的,我们插队都自己做饭,蒸馒头,小菜儿!面是头天师傅发好的,好大一堆,足有三四十斤。我和小凤就往里兑碱水,揉馒头,整整忙了一上午,哇,蒸出的馒头黄灿灿,碱大了。第二天,哇,蒸出的馒头没长个儿,酸的,碱小了。第三天,哇,馒头蒸花了,碱没揉匀。第四天,哇!两大屉雪白胖胖的大馒头出锅了,我和小凤都乐了,终于让同学们吃上我们蒸的漂亮的大馒头了,只可惜第二天就要返校了,没机会再展示我们的技术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面食作品,打那以后我再没蒸过馒头。最后的压轴好戏是杀猪。每次劳动结束那天照例要杀一头猪,犒劳大家,吃一半儿,给下一拨来农场劳动的同学留一半儿。说起杀猪我们班可有好把式,好几个男生据说都有赛张飞的本事,最后遴选了四个最棒的小伙子来执行。杀猪那天早上我离着有十几米远看热闹,不敢靠近,因为小时候父亲所在机关的食堂杀猪,猪临阵逃脱,嚎叫着,红着眼在操场上狂奔,拱倒了葡萄架,拱翻了手推车,好险!把我们这些围观的孩子吓得抱头鼠窜,可我们班男生杀猪令人拍案叫绝,只见手起刀落,猪没来得及哼几声就被放倒了,然后就是放血,吹气,下滚锅,刮毛,一气呵成,好生了得!午饭有红烧肉,那炖肉的香味儿传出一二里地去,大家都盼着班长喊收工了,好大快朵颐。开饭时我们帮厨的几个同学倒是没吃多少,内因是,师傅让我们炸些丸子留着下顿吃,男生是边炸边吃,差不多吃饱了,我是帮厨的唯一女生,自然要矜持一些,不好意思吃,不过还好,有一个同学善解人意,悄悄在我饭盆里放了几个大丸子。
就要回学校了,心里一阵怅然。告别清晨笼着一层薄雾的小河边,我曾在那里读英语,告别那光溜溜的井台儿,我曾在那里打水洗菜,告别那只看门护院的小黑狗,它总是亲昵地在我的身边转悠。大卡车启动了,一切都渐渐远去,而那过去了的、平凡的故事都变成了亲切的怀恋,在我的脑海中像夏夜晴空中的繁星一样时隐时现。
杨鸿铨吴小平杨鸿谟
科学研究是学校发展的基石,重视科研工作是成电的传统,从建校开始,科研就是学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建校初期,科研部与教务部、总务部被称为学校的三大部门。虽然建校时教师仅200余人,但从1956年起,学校的科研工作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承担了大量国防及民用科研。
1958年,学校研制成功模拟计算机,60年代中期又参与了441B数字机的研究。数年以后,外国专家仍然对我们当时在计算机领域的研究水平赞叹不已。50年代,我们研究的波导管技术领先全国,当时校办工厂的加工、制造水平也非常高,生产的波导管可直接投放市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