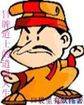一
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建造的文学王国。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一样,高密东北乡已经由莫言写入了人类的文学史。
莫言首次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是1984年秋天创作的《白狗秋千架》。尽管在此前发表的《民间音乐》《售棉大道》等作品中,莫言就已经表现出了对民间文化和乡村社会的关注,但这种关注还没有具体落实到一片同创作主体有着深刻而强烈的精神和情感联系的土地之上;《春夜雨霏霏》《黑沙滩》等有着军营文学特色的作品,尚表明莫言还处于一个艺术上不无稚拙的摸索、学艺阶段。
《白狗秋千架》触及的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上频繁出现的“离乡还乡”母题。求学离家10年的“我”重返高密东北乡,与少年恋人“暖”劈面相逢。“我”的一厢情愿的怀乡情绪受到了暖的不留丝毫情面的阻击。当“我”表明“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新的空气,婉转的鸟啼”时,暖却回答:“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尽管在作品中,暖的悲剧人生看似由偶然事件所造成(少年时荡秋千弄瞎了一只眼),但总体上并不影响这一作品彰显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必须面临的巨大矛盾和悖论:记忆、想像的乡土与现实、真实乡土的分离。时间的倒错和空间的位移是乡土文学之故乡“神话”得以成立的前提。
只有制造时间和空间的间距,并借助记忆的加工和情感的美化,才能成就美丽、浪漫的故乡传奇。换言之,只有离开故乡并使故乡沉入回忆中,故乡才有可想的。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故事,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系列,其一以作家的童年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为基础,描绘现实乡土中处于贫困年代的乡村人(特别是少年和青年)的恶劣生存处境和痛苦生存感受,并表现其顽强的生命力和试图挣脱这种生存困境的强烈愿望和向往;其一以故乡先辈的传奇生活为表现对象,渲染想像乡土中“我爷爷”、“我奶奶”、金童娘一辈人无拘无束、旷达豪放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并映衬、反观现代人和城里人的“种的退化”和人格的萎缩。前者以《枯河》《透明的红萝卜》为代表,未特别标明“高密东北乡”的《球状闪电》《爆炸》《欢乐》亦近之;后者以《秋水》《红高粱家族》《红蝗》为代表,《良医》《神嫖》等记载奇人逸事的小说也可归入此类。应当说,虽然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非地理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它已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学王国,但这两类小说却仍同作者的故乡有着血肉相关的联系,特别是作者的童年生活记忆给他的创作以重要的影响。
莫言曾说,童年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是洪水和饥饿,而故乡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都已被他童年时的感情浸淫过:“高粱叶子在风中飘扬,成群的蚂蚱在草地上飞翔,牛脖子上的味道经常进入我的梦,夜雾弥漫中,突然响起了狐狸的鸣叫,梧桐树下,竟然蛰伏着一只像磨盘那么大的癞蛤蟆,比斗笠还大的黑蝙蝠在村头的破庙里鬼鬼祟祟地滑翔着……”无论写故乡的河流(《枯河》)、白狗和桥头(《白狗秋千架》)、桥洞和黄麻地(《透明的红萝卜》)、梨园和洼地(《老枪》),还是写故乡的学校和池塘(《欢乐》)、打麦场和卫生院(《爆炸》)、草甸子和芦苇地(《球状闪电》)、棉田和加工厂(《白棉花》),都无一不充满了经过作者的童年生活经验浸淫过的主观化、感觉化的风景描绘。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莫言的两类高密东北乡故事中,人物的生存方式和人格气度却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在前一类作品中,无论是《枯河》中的小虎,还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抑或是《欢乐》中的齐文栋,都立于一种无望无助的生存困境之中,物质的匮乏、社会的畸形、文化的贫瘠使他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人生苦难和痛苦侮辱。
在黑孩那里,虽然菊子姑娘和小石匠给予了他超乎亲情之上的人生温暖,在外来的压抑下,其内心世界也变得超凡敏感并始终保持了对一个美的世界的向往,但他的爱和恨毕竟都是极端的、反常的,他只能以冷漠的、残酷的自我虐待的方式来回答外界的侮辱和嘲弄;而更有甚者,在小虎那里,只有死亡才能构成对人世不公的最大报复,在齐文栋那里,死亡则成了他短暂人生的最大欢乐。
与此相对照,在以故乡先辈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我爷爷”、“我奶奶”们却有着生机勃勃的原始本能和狂放不羁的人生品格,他们性情强悍、血气方刚、情感奔放,敢爱敢恨,敢杀人敢放火,为了爱和生存,他们既能干出杀人越货的勾当,也能爆发出杀敌御侮的举动。显然,在“高密东北乡”故事里,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莫言试图支撑起自己构筑的模糊的“种的退化”的隐喻系统。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提出了“纯种”狗和“杂种”狗的概念;在《红高粱家族》中,又突出了纯种高粱和杂种高粱的区别,并通过叙述人“我”之口明确指出曾上演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的“我的父老乡亲们”,“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虽然,叙述人“我”将“种的退化”与“进步”并举,可“进步”在具体的描绘中却付诸阙无。读者所看到的,均是“种的退化”的描绘。譬如,短篇小说《老枪》便最为凝练地表达了“种的退化”的主题。大锁奶奶用老枪收拾了将妻子当作赌物的自己的丈夫,大锁的父亲一头撞翻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的柳公安员后用老枪自杀,大锁则意外地死于老枪走火。作者用一支老枪串联起一家三代人的命运,突出的应当是一个鲜明的“种的退化”的主题。虽然,母亲用剁掉大锁一截手指作代价为大锁安排下好好读书、为祖宗争气的人生之路而大锁仍禁不住摆弄老枪的冲动,但大锁除了想像先辈的豪迈刚强形象以外便一无所为,他甚至不能成功地击发前辈使用过的老枪。从这一点上说,他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相形见绌的不肖子孙。
现代乡土文学之故乡神话的建立,有赖于时间、空间、社会身份等多种维度的比较和对照。在时间维度上,它需要将故乡纳入现在与过去的比较之中;在空间维度上,它需要将故乡纳入城市和乡村的比较之中;在社会身份上,它需要将故乡纳入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的比较之中。在《红高粱家族》中,“我”的身份是“逃离家乡十年,带着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给我的虚情假意,带着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站在“我”整个家族的亡灵之前,这实际上确定了“我”的位置是界于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村、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我”因此获得了超出这一切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叙述权力,可以超越时空的界线讲述先辈的传奇故事,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指点人生、评说历史。
在《红蝗》中,表示“即使现在不离开这座城市,将来也要离开这座城市”的叙述人“我”故伎重演,再次将故乡纳入现在与过去、城市与乡村相对照的时空维度之中:“在臭气熏天的城市里生活着,我痛苦地体验着淅淅沥沥如刀刮竹般的大便痛苦,城市里男男女女都肛门淤塞,像年久失修的下水管道,我像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声一样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但形成吊诡的是,还乡情结必须落实到一个想像的故乡的过去而不是现在才能实现。在当下的故乡土地上,正是逃离故土、前往城市而不得的困境成了齐文栋(《欢乐》)、蝈蝈(《球状闪电》)们的痛苦之源。
对于听惯了“管它中专、大专,考中了就跳出了这个死庄户地,到城市里去掏大粪也比下庄户地光彩”的齐文栋们来说,逃离乡土正是他们人生的最大理想,这些人面对城市的大便时,必然是另一种感兴。很大程度上,故乡神话只有面对一个想像的过去、面对那些业已离开乡土的乡村之子才是成立的。《红蝗》一类作品的特有的反讽气息,正来自于故乡神话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吊诡性质。在莫言那里,事实上有两个高密东北乡:“我”的高密东北乡和暖、齐文栋、蝈蝈们的高密东北乡。前者是存在于回忆和想像中,后者是存在于当下现实中。当作者侧重于前者时,笔下便更多浪漫的想像,更多包含了创作主体对乡土的热爱之情;当作者侧重于后者时,笔下便更多忧郁的写实,更多包含了创作主体对乡土的同情和仇恨(如《金发婴儿》《弃婴》《天堂蒜薹之歌》,《弃婴》中甚至出现了“生在臭气熏天的肮脏村落里,连金刚石宝刀也要生锈”的句子)。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很快深入人心,离不开80年代的寻根文学背景。寻根文学的提出,基于现实中作家的一种普遍焦虑——文学之根与文化之根的缺乏。至于“根”为何物、到哪里去寻、如何寻法,当时的作家并不一致。莫言说:“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系列就是扎根文学。我的根只能扎在高密东北乡的黑土里。”莫言的乡村之子身份使他比韩少功、王安忆等作家更有优势,可以直截了当地向自己的故乡去寻根,并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扎根文学”,而韩少功等要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扎根文学”则至少要经过类似于“上山下乡”一类的资格认证。不过,即使莫言的寻根和扎根,也必须借助于时间的倒错和空间的位移,他要想找到有生命力的根,便不得不向故乡的历史中去寻。然而,一旦进入历史叙述的领域,“根”的虚幻性质便立即暴露出来,把往昔理想化、把祖先传奇化,因此成为作家的必然选择。正如莫言所言:“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越是久远的历史,距离真相越远,距离文学愈近。
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每一个传说者,为了感染他的听众,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再到后来,麻雀变成了凤凰,野兔变成了麒麟。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人对现实不满时便怀念过去;人对自己不满时便崇拜祖先。事实上,我们的祖先跟我们差不多,那些昔日的荣耀和辉煌大多是我们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故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故事,既是他扎根故乡之作,又是他超越故乡之作。高密东北乡已成为永远的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
二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莫言是以感觉描写见长的作家。他的信马由缰、前呼后拥、不受理性思维约束的感觉描写,是他区别于同时代小说家的重要特征之一。莫言一度推崇一种“轻松、自由、信口开河的写作状态”,觉得“一旦进入这种状态,脉络分明的理性无法不让位给毛茸茸的感性;上意识中意识无法不败在下意识的力量下”。
在感性力量和下意识的驱动之下,莫言经常能鬼使神差捕捉、调动、铺陈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稍纵即逝的感觉,并实现各种感觉间的交通和转换。《枯河》中,小虎意外地弄瞎了大队支书女儿小珍子的一只眼,当众人赶到事故现场时,作者写小虎“好像被扣在一个穹窿般的玻璃罩里,一群群的人隔着玻璃跑动着,急匆匆,乱哄哄,一窝蜂,如救火,如冲锋,张着嘴喊叫却听不到声”,就成功地将小虎自知大祸临头、所有思维停止活动而进入一种真空状态的感觉表现了出来;而接下来写支书的两只翻毛皮鞋直对着他胸口踢来时,小虎“听到自己肚子里有只青蛙叫了一声,身体又一次轻盈地飞起来,一股甜腥的液体涌到喉咙。
将小虎身体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得有声有色(五脏六腑都受到了伤害),同时将小虎弱小无助、任人欺凌、痛苦到极点而近乎麻木的心理感觉传达了出来。《爆炸》开头部分写父亲响亮地打在我左腮上的那记耳光,则是另一种情形:“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着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
60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和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作者调动了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将一记耳光写得有声有色、有棱有角,传达出了“我”对父亲的交集了怨恨、尊崇、负疚等复杂情绪的心理感觉。在莫言笔下,眼、耳、舌、鼻、耳等各个官能领域可以互相打通,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不分界限,白云可以有坚硬的边角,光线可以发出叫声,空气有重量,而味觉有色彩,“我”奶奶从吹鼓手们出的曲调里,不仅可以听到死的声音,而且可以嗅到死的气息,看到死神的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莫言的感觉描写,是高度主观化和印象化的,大多难以用写实来衡量。他用感觉描写来传达情感和情绪,又用情感和情绪来增加感觉描写的深度和意义,结果既使其作品的可感度获得一个飞跃,而且也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
莫言的艺术描写,似乎常有意识地要给读者的感官造成强烈的冲击。他写声响,是“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嘀嘀嗒嗒……哞哞哈哈……吗哩哇啦……咿咿呀呀……叽哩欻啦……直吹得绿高粱变成了红高粱,响晴的天上雨帘儿挂”(《红高粱家族》);他写颜色,则大红大紫,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块儿上:“我爷爷”被曹梦九所抓、被罚在县城扫街两个月,穿的是一条红腿、一条黑腿的裤子;小酒店掌柜“高丽棒子”盖的是一张黑狗皮,铺的是一张白狗皮,墙上还钉着一张绿狗皮、一张蓝狗皮、一张花狗皮;《狗道》中“我”家的黑狗、绿狗、红狗率领群狗争吃人类尸体的描绘,则堪称充满了残酷色彩和视觉冲击效果的感官的盛宴。
为了刺激读者的感官,莫言特别喜欢写一些具有畸形、异能的人物和动物,并通过人物和动物身体的畸形、残缺、肢解、腐烂,造成一种特殊的冲击效果。在莫言的每一篇小说中,几乎都有残疾人物(或动物)出现,除了较早的《民间音乐》《秋水》可以较多从写实来考虑之外,其余几乎都是为了达成出奇制胜的美学效果。《白狗秋千架》从暖家中滚出的三个同样相貌、同样装束、有着同样的土黄色小眼珠、头一律向右倾的哑巴小男孩,加上一个哑巴丈夫,除了为结尾部分暖的看似突兀的要求做了铺垫以外,肯定还有美学效果上的考虑;《丰乳肥臀》中,孙大姑家成日骑在自家墙头五个豁口之上、用阴沉沉的眼光盯着过往行人的五个哑巴孙子,连同他们那五条蹲在墙根、眯缝着眼睛的墨黑的黑狗,给人的是一种阴郁的令人不寒而栗、胆战心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