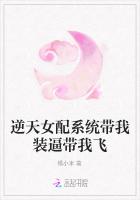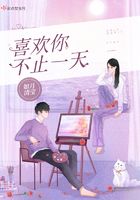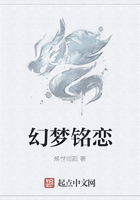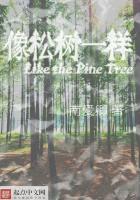王朔的小说确实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和形而上的理趣,它在叙事方法方面也无多少特别之处,它的主题既不明确也不完整,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甚至不突出。但是王朔的小说有非常自然而人性化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足以构成某种思想冲击力--王朔作品的思想不是意义模式统合的结果,而恰恰是无可确定和不必要统一的生活块状撞击产生的思想意向,这种思想意向可以被称之为“反本质主义”意义。由于对既定的本质主义先天性的不信任,王朔的小说的人物都有一种抗拒意识形态主体中心化的功能,怀疑主义是王朔赋予人物的基本性格功能,信仰和神圣性的事物在王朔的作品里经常惨遭亵渎。权威与真理的绝对性有赖于对事物本质深信不疑,而王朔恰恰与此相反。他嘲弄了生活现行的价值范型,他的叙述感觉正是从这些现行的价值规范的破裂中迸发出来。代表王朔小说特色的那些精彩对话大都是政治术语和经典格言的转喻式引用,特别是“文革”语言的反讽运用。王朔撕去了政治的和道德的神圣面纱,把它们降低为插科打诨的原材料,给当代无处皈依的心理情绪提供了亵渎的满足。信仰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是谁?
我是谁?王朔抓住了那个时期人们潜在而又暖昧的怀疑情绪,直接危及到现行意识形态的原命题。人们依靠的本质观念,人们追求的目的被彻底解除之后,人变得轻松自由,变得胆大妄为。王朔的那些嘲讽性对话不过是人物“反本质”行为的注脚而已。
王朔的人物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位置,他们是一些没有既定社会本质的人,或者说放弃原有本质的人。王朔赋予人物以非常个人化的形式,个人恰恰是在面对生活的现实、嘲弄现实同时也嘲弄自我从而消解社会的统一价值规范。王朔的“真人”只是顾及个人当下生存状态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任何神圣性的亵渎,都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认同的结果。生活的破裂、无目的、无信念、偶发性、永恒的失落、无意义等,都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种坚定的超越性信念和永恒的价值追求的幻想被摧毁之后,生活不过就是一些简明的行为和欲望。“反本质主义”意识在王朔的作品里不是通过那些激烈的反抗行为来表达,恰恰是从那些最平易的生活事实里透示出来的。王朔的叙述具有向着生活最原始的状态还原的可怕趋向。一王朔一方面嘲弄了庞大的生活信念,另一方面把生活推到最简陋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中,生活以最原始的形态显露。
王朔的反本质主义态度在这些人物身上确实透示出一种所谓“新型的世界观”,这就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的认同。在现代主义那里,“不完整性”被看成生活“有问题”的依据,作为向生活抗议的立足点,作为文明衰败的迹象来表现。而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例如美国六十年代的实验小说),则把不完整性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接受下来,寻找一种不同的适应性,一种能轻易改变主角状况的感觉方式或行动方式。正因为反本质主义构成了认同“不完整性”的世界观基础,所以王朔的人物失去行为准则,因为生活可以轻易变更,于是人的动机和终极目的都可以轻易改变。他们的行动既无可约束、无可规范,同时又没有猛烈的反社会行动。反社会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嘲弄方式。对于王朔来说,这一切都不是笨重的思想意识,不过是王朔对于这个动荡裂变时代的直接体验和最原初的认识而已。
在王朔之后,一大批更年轻的作家出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称之为“晚生代”,例如,何顿、述平、邱华栋、李洱、张曼、毕飞宇、朱文、韩东、鬼子、荆歌、东西、李冯等人。晚生代的定义本身表明他们与宏大的历史叙事构成的悖反--他们是历史的迟到者、反叛者和逃逸者。他们的写作直接面对当下中国变动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全面市场化引起的现实变动。
因而他们的写作面对“现在”说话,而不是面对“历史”或面对文学说话。他们的写作没有文学史的观念,先锋派的写作一直在思考小说艺术的既定前提,当代中国的和西方现代主义创立的小说经验,面对这个前提进行叙事革命,这是他们存在的历史依据;然而,九十年代这批人的写作没有这个前提,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史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陷入合法性危机,不再有一个明确的文学规范体系制约着文学共同体的写作;另一方面,这些“现在主义式”的写作冲动来自个体的生存经验,而他们个人的文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远离既定的文化秩序的。他们就从世纪末的分崩离析的现实边界切入文坛,带着他们的直接经验,充满了表演的欲望,他们就是这样一些末世的舞者。因而,他们关注对“现在”的书写,特别是对中国处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非历史化特征进行直接表现,使他们的叙事没有历史感。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他们乐于使用表象拼贴式的叙事,倾向于表现个人的现在体验和转瞬即逝的存在感受,并且热衷于创造非历史化的奇观性。所有这些,使得他们的叙事具有某种“现在主义”特征,表现了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迥然不同的文学流向。
不管把这个时代的生活描述成分崩离析的情势,还是完美无瑕的形态,都无法否认现实本身发生了巨变,当代生活正在以夸张的姿势奔腾向前。没有人能够抓住它的本质,触摸它的精神和心灵。没有历史感的“现在”,只有表象而没有内在本质。从个人生活的边界进入文坛的晚到者,显然与那个现代以来的宏伟叙事无关,与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也不再有直接关联,他们无须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语境中来确立叙事起点,他们就生活在这个消费至上主义的间隙,再也不能、.也不必要从整体上书写这个时代,内在地把握这个时代。何顿、述平、朱文、邱华栋等人对这个时代的直接书写,确实构造了一幅生动的商品拜物教与消费主义至上的时代的全景图。这是一个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性的时代,一个美妙的“时装化”的时代,一个彻底表象化的时代。后来者既然捕捉不到“宏伟的意义”,他们也只能面对现实的生活表象展开叙事。事实上,九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作家正是以他们对表象的捕捉为显著特征,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构成了他们写作的基本法则。
那些“宏伟意义”、那些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式的“巨型语言”与他们无关,只有那些表象是他们存在的世界。对表象的迷恋,一种自在飘流的表象,使九十年代的小说如释重负,毫无顾忌,彻底回到了现实生活的本真状态。
当然,经历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晚生代”的生存经验和文学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种单纯回到生活现实的直接经验的方式,也不可能完全支撑作家的写作。文学写作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情势,面对更为坚硬的文学问题。
1998年,刘震云的超级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出版,给这一年的文坛增添了分量。这部历时六年写作的小说,篇幅长达四卷200万字。这部小说还未完稿,就为多家出版社青睐,最后北京华艺出版社以几十万元之巨的稿酬,夺得出版权。小说尚未正式出版,数家大型刊物争相刊载,《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作家》都争先恐后,开出大量版面先行发表,生怕错过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后的汉语文学名著。尽管刊物已经发表大部分章节,华艺出版社还是成绩不菲,首版印刷三万册,据称已经销出二万册。然而,批评界却保持足够的沉默,大多数人的态度暖昧或不置可否。
这部小说无疑是刘震云的力作,也是近年来少有的鸿篇巨制。与过去按照革命现实主义范式创作的超级长篇小说不同--这类小说通常是讲述一部“客观的”革命历史故事,而刘震云的这部小说则是以非常主观化的叙事,讲述故乡(家族)的历史。令人惊异的是,如此篇幅庞大的小说,却没有明晰的故事线索和严密的叙述结构,这在汉语小说中几乎是从未有过的先例。这部小说看上去漫无边际,杂乱无章,没有明确可归纳的主题,也没有可把握的核心人物,但深入分析还是可以看出贯穿于其中的主题意蕴。那就是表现经历革命与现代化冲击的乡土中国所发生的异化(alienation),以及在这种异化状况中保持着的和变异着的人性。但这种主题并不出自刘震云明确的思想意念,而不如说是一系列荒诞反讽叙事的副产品。小说以人物为叙事线索,这些人物的故事都以极其夸张的形式加以表现,人物的漫画化其实也就是精神异化的外在形式。像孬舅、小麻子、六指、娘舅以及各个出现的人物,他们的言行或存在状况显然非常夸张,在充满荒诞感的叙事中,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被放大,而那些错位和谬误则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荒诞感来制造反讽效果,这是刘震云近年来的小说叙事愈演愈烈的表现方式,《故乡天下黄花》还是在写实的笔法中穿插着嘲弄情调;而《故乡相处流传》则完全是打乱历史,强行给历史重新编码,以循环论的非历史主义观念,使历史变得可疑和荒诞。显然,《故乡面和花朵》则更加激进,荒诞色彩更加浓重。对于刘震云来说,明确的思想观念和主题动机并不重要,他关注的是那些生活情境的细枝末节,给这些细枝末节注入兴奋剂,使之长出奇花异葩,这就是刘震云的叙事目的。
小说叙事摆脱严格的时空限制,把过去/现在随意叠加在一起,特别是把乡土中国与现阶段历经商业主义改造的生活加以拼贴,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反映乡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转型中,人们的精神所发生的变异。我说过,刘震云并不直接去表现那些重大的历史性命题,也不去表现重大的历史场面和事件。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些宏伟叙事。但他有意从侧面关注那些生活琐事,在枝节方面夸夸其谈,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庞大的历史过程,让历史淹没在一连串的无止境的卑琐欲望中。这就是刘震云用四卷200多万字的篇幅为人们提供的乡土中国的“历史图景”--不在的历史。由经典叙事讲述的历史变迁,那些铁的必然性和一系列壮举,甚至于个人关于家乡的记忆,在这里完全被一些平凡无奇的草民生活所替代,甚至于变成鸡零狗碎的乡土生活。刘震云的叙事如同对历史行使一次“解魅化”(disenchant)。
因而,失踪的历史因此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喻,它使刘震云那些散漫无序的叙述具有了某种思想底蕴。当然,刘震云的整部小说也并不只是荒诞无稽,经常也可见一些对人性的内在的复杂性和微妙的心理变化的刻画,这类细节有时也表现出刘震云对人性的某种古典主义式的观察。但就小说叙事而言,荒诞感和对人性的嘲讽,以及毫无节制的夸夸其谈还是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在那些看似混乱不堪的表述中,其实隐含着刘震云对一些崭新而奇特的主题介入的特殊方式。例如,对个人与本土认同关系的复杂思考;特殊的怀乡母题;乡土中国历经的奇怪的现代性;对权力与外来文化瓦解本土性的奇特探究等等。这部小说发表后,在评论界并未获得热烈的反响,这与出版社争相以高价购买版权的姿态大相径庭。人们保持沉默并不是出于审美知觉力的麻木,这部小说在不同的人看来,或者说以不同的立场去看,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它也许被看成想象力奇诡的天才之作,很可能是汉语写作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解放;但也有可能被看成是东拉西扯的大杂烩,毫无节制的胡说八道,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最大的胡闹和骗局。
但不管如何,刘震云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一部如此冗长的小说却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试图去重现历史。当刘震云试图讲述乡土中国(故乡)的往事时,他发现历史已经支离破碎,他不能、也无力去虚构乡土中国的完整历史。现实主义观念(或写实主义手法)重现历史也就是虚构历史,它包含一整套的关于历史与现实的意识形态认知体系,对于刘震云这代作家来说,特别是像刘震云这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的中国作家来说,旧有意识形态体系已经难以支持文学观念及具体的创作方法,这使他这样的依然怀有重建文学帝国梦想的人陷入困境。一方面,他还迷恋文学霸权,试图恢复文学对这个世界的说话的权威,因而,他不惜以数年的时间去完成一部超级长篇小说;他本人对文学经典(史诗),对成为文学的权威也怀有梦想,否则他就不必要以如此宏大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创作冲动。但另一方面,他再也不能构造一种完整自足的经典性的文学叙事,刘震云的写作却不得不变成一次对文学帝国的损毁,对经典叙事的恶作剧般的颠覆。东拉西扯夸夸其谈的语言放纵,居然构成这部卷帙浩繁的超级长篇小说的叙事主体。文学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重建历史的虚构功能,受到严重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是最后一部汉语言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此后,人们已经无力构造一部完整自足的乡土中国的历史(精神史或心灵史)。留给怀有创作经典作品之梦的作家的,不过是剩余的想象力,他能从过去的历史中捕捉到的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个人记忆,对这些经验不着边际的任意发挥,这种发挥已经放弃了文学叙事的功能,而是语词的自由戏谑。
事实上,刘震云不是不能,而是不愿去讲述完整的乡土中国记忆。在他的一些关于个人的直接记忆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刘震云的现实主义式的叙事运用得非常老道,他显然不愿陷入温情脉脉的怀乡病中,他一面忧伤地怀乡,一面恶作剧般地把怀乡记忆打碎。断断续续的个人记忆总是在集体式的乡土中国记忆的裂痕中涌溢而出,它们奇怪地具有起源与终结的完整性。乡土中国在整体上已经破裂,被现代性侵入的乡土中国生活以断裂的方式呈现为一系列的喜剧现场。在刘震云的整体叙事中,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以分裂的方式展开,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记忆形式。这些形式也是分裂的,叙述人无法恰当地把握这二者的关系,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恶作剧的方式把二者拼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