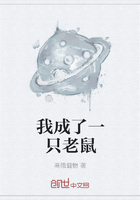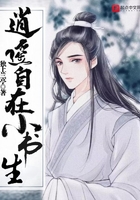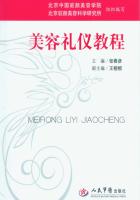我喜欢徐光耀
读罢《昨夜西风凋碧树》,在连续的强刺激下,涌上心头的第一句话竟是:我喜欢徐光耀。喜欢他什么呢?是喜欢他行文的质朴刚硬,他记忆力的惊人,抑或他直面历史沧桑的勇敢?好像是,又不全是。应该说,我喜欢的其实是他的人格与人品。
我早有所感,“右派”和“右派”是不全一样的。这话现在讲比较好,过早地讲会被视为无情无义。面对历史强加的悲惨厄运,我们对每个受难者都一样地寄予深深的同情,但是,每个受难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不期然地表现出来的情操,意志,怯勇,尊卑,以及心灵的坚韧程度,又是各不相同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文革中为我们大家所共同品尝。一个人既不能因为曾经受难就必然伟大,也不能因为曾经受难就能推卸掉他应负的良心责任--即使没有任何人追究,良知也会发出问询。有时候,重要的不在于外在的灾难来了,而在于大难临头时的灵魂状态和担当程度。我这样说,决不是要放弃对历史的严峻反思而陷入恩恩怨怨的纠缠,对历史的反思我们要一直坚持下去,不反思就不能前进。但是,一旦步步逼近了历史的深层真实,对人性的追问和人的质量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了。历史的主体毕竟是人。这也是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正像徐光耀文章中说到的,“中国文人有个老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就有人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互相丑诋,互相厮咬,互相欺诈,互相葬送……”。当此之时,正是对一个人的良知的最严酷的检验。当时年轻的徐光耀恰好就收到了这么一封以中国作协名义发来的绝密字样的调查丁玲等人的外调函。这显然是一封充满了暗示、诱供、高压、威胁气息的信函,容不得你不按来信的调子老老实实地配合。徐光耀的可爱,就在于他认死理儿,凭良心办事,非要坚持什么“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他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一丝不苟地写好了复信。在他是做着一件庄严的工作,孰不知他正在自掘陷阱。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敢在信中说:“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的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意见。”似乎意犹未尽,他在信的末尾竟然又强调:“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受,只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的什么影响,却没有要我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这简直是反了天厂,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敢用这种口气跟“组织”讲话,在那时,不打你右派打谁右派?然而,全部的可贵就在于,他不自私,不巧滑,不世故,不知利剑已悬在头顶,“傻乎平地”坚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即使在那时,在已经开展过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反胡风的那时,也未免太幼稚了,但却是一种多么可爱的幼稚啊。今天,就为这保存完整的一封来信和一封复信,这扞卫真理的刚毅,我也要向你,徐光耀同志,表示我的由衷的敬意。相形之下,文章中提到的个别人,虽也备受劫难,其情可悯,但那不检点的作风,却让我怎么也尊敬不起来。徐光耀自称是个“俭啬之人”,一个农家子弟,但尊师的诚意使他毅然掏出了七百块钱。当时的七百块钱是个什么数字,对他是多么地不易,今天不难想见。但他还是忍疼掏了。他怎么会想到就此落下了“资敌”
的罪名呢。可见他是个性情中人。这也就是我说我喜欢徐光耀的原因。
在徐光耀的这篇回忆文字里,那个特定时期窒闷而恐惧的气氛,那说真话的危险、艰难、肇祸,那说假话的厚颜、霸道、径情直遂,已达令人吃惊的程度。我看丁玲也是一个爱讲真话的、漏洞较多的人。丁玲的器重和偏爱徐光耀大约是真的。对一个十三岁就入党的红小鬼,一上手又写出了《平原烈火》这样有冲力的长篇,怎么能不讨老师的欢心呢。丁玲对《平原烈火》的评价,似乎有点偏高,这里面不无夸耀自己得意门生的感情因素。但丁玲并没有要徐光耀骄傲,而是反复地提醒他、敲打他不要骄傲。“臭名昭着”的“一本书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徐光耀提供的版本应是最可信的。徐光耀出了一次国,那在学生中是招人艳羡的,丁玲就说,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了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只有周围的同学们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得有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丁玲这番话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我很爱听,是真话,就是对今天的作家也有针对性。倒不一定是出国,就是得了什么大奖之类,也不必自鸣得意,作家还得靠作品,而且不是靠一时一事。但丁玲的这番话里“引人注意”之类的字眼有点多,话虽是好话,是真话,理也是正理,但她没注意这在那个年代是很犯忌讳的。丁玲的性格我是领教过一回的。大概是1981年的“三八”节前夕,我和高洪波作为文艺报记者,为配合节日去采访丁玲。没想到她一听说我们是文艺报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说,你是着名女作家,三八节快到了,特来采访您。丁玲竟说,我不卖这个“女”字!30年代在上海我就说过我不卖这个“女”字,今天也一样。
此刻丁老太太是那样倔犟和凛然,弄得我俩尴尬之极。没想到,当了二十多年的反党集团头子,右派,她的个性居然丝毫未变。虽然丁玲给我们难堪,我们并不在意。我只是暗想,她大半生的悲惨与她的性格可能很有关系,性格即命运啊。
最近,很偶然地,我读到了好几部写反右时期生活的作品,有纪实体的,也有小说的。除了这篇《昨夜西风凋碧树》,还有《林昭之死》,另有两部是尚未出版的和风鸣着的回忆《无奈的历程》和林凡的小说《苦太阳》。后两部是写甘肃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的。看这种书,常使我这后来者思绪万千,夜不成寐。我看着看着,就有掉进冰窖寒彻肺腑的绝望无助感,但放下书本,又由衷地庆幸,今天我们毕竟生活在可以随便说话而不再恐惧的时代,这多么好,今天多么好。就某种意义说,反右比文革要更惨烈,因为它早,它的受难者受难的时间漫长,因为它只是孤立打击了五十五万而不是后来的人人有份,更重要的是,它给予知识的价值和知识者的人格尊严以毁灭性的打击,斯文扫地尽矣。后来极“左”的一套就不可收拾地膨胀起来了。今天我们庆幸,我们终于告别了噩梦,但要记住,告别也是漫长的。
2000-2-9
批判要着眼于发展--评《十作家批判书》
读了《十作家批判书》,感受比较复杂,看来此书没有原先听说的那么可怕,如果抛开夸张失度、耸人视听的“包装语”不顾,应该说,在许多刻薄刺目的词句背后,其实是不无真知灼见的,只是为了引人注目,撰写者们故意把一些原属正常的异见用了极端化的判断话语表达出来罢了。在这本由多位撰写者组成的书中,水平参差不齐,在他们的批判方法、态度和指归上,是可以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话题的。当然,不可否认,此书有明显的商业炒作成分,好像不锐叫一声就吸引不了市场的注意力似的,于是,究竟什么才是拯救评论并摆脱困境的正路的问题也就提了出来。我觉得,以此书为契机,审视其矛盾所在,也许可以为“批判”正一正名,冲击一下批评界长期形成的沉沉暮气,改变一下貌似众声喧哗实则颇为单调的批评局面。
“批判”一词已经被误读的太久,往日频繁的政治运动特别喜欢使用这个词,以至此词的本义已沉埋多年,只要给谁冠以批判二字,那无异于坚决打倒,一笔抹杀,彻底否定,按之人地而后快。我甚至认为,即使这本书的撰写者们,原想在本原的意义上使用批判一词,也许写着写着,连他们自己的潜意识里也不无过去那种批判的影子了,否则好像就没有“批判相”。此书的出版者是不是也有利用昔日“批判”之余威,逗引读者的潜在动因呢。人是无法完全斩断历史的阴影的。
不过,就原本意义看,这本书可能想扬弃“批判”一语的政治异化,回到批判的本义上去。批判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评论是非之意,也即所谓“评论先代是非,批判未了公案”。批判是革命的科学的前进的必由之路,批判是否定之否定,没有批判精神,学术也好,创作也好,都无法进步。从历史的发展高度来看,没有哪个作家或作品是不能批判的(批判的本义),没有谁只能得出惟一的结论。倘若有人评论作家,能发人之所未发,读解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又切中要害,即便失之尖刻,何尝不是痛快淋漓的事。此正所谓“隔靴搔痒赞何益,入骨三分骂亦精”。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大师、前辈、名人级的作家,大家早已习惯于一味的赞扬,千篇一律的评说,一旦听说要批判谁了,便惊诧莫名,心理上先难于承受。事实上,不要说正常的批判,即便谬误的批判,过去的某些大作家也不是不可容受。鲁迅就不止一次地提出把攻击他的文章汇成一集,他说,如果把这种书和他的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另一面战法的五花八门。又说,这于后来的读者不无益处。我想,这不能仅看做鲁迅的有容乃大,还有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学术和创作的生命力总是在批判中扬厉的。那时,郭沫若曾斥责鲁迅是“封建余孽”,还有人骂鲁迅如何守旧落伍,苏雪林就骂得更苛酷了,后来证明他们都错了。当然,文化环境变了,我们不必非要重演当年的方式。由此倒要证明,一个真正的作家是骂不倒也抹杀不了的,但他一定是“真正的”。
对这本《十作家批判书》,我能接受星散于各篇什中的某些见识,但也有明显的不满意。概而言之,一是:在我看来,批判的基础首先是理解,而现在不少文章显得对其批判对象理解不够。这里所说的理解,并不是要盲目的吹捧,或一味的说好,而批判,也不该是简单的否定,执一端而推极致。我认为,理解的前提是,要充分意识到,文学的历史,与文化史,思想史一样,都是前人聚沙成塔般层层累积而成的,对某些大师或前辈而言,有人有大贡献,有人有小贡献,不必苛求他不可能做到的,对所论作家一定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尤其要顾及到作家的创作个性。说《围城》“出现了自设哲理主题与文学形象的脱节”我同意,但批评该书“理念大于形式,理智大于感情”,就属于没办法的事情了,因为钱钟书只能是钱钟书,何况这种小说虽不全合小说作法,但有个把本出来让人会心一笑也没什么不好。评汪曾棋的情形也差不多,汪老先锋不先锋都是无所谓的事,倘能“传统”到底,“散仙”到家,也不失为一种风姿,倘能为审美的殿堂添一二件小摆设,不更好吗,何必非要赠他个“佛爷”的贬号呢?理解不够还表现在,本来在指责作家们的不够文学,自己却用非文学的漫画化来评说作家,如“肾亏”啦,“圆滑”啦,“文化口红”啦,“穷途末路”啦等等。朱大可评余秋雨本来很犀利,很有独见,但非要用个妓女提包的笑话就也破坏了文章学理风格的统一性。
二是,发展的观念不够鲜明。对一些名家展开科学意义上的批判当然是对的,因为对一个名作家和名作的评价,永远也不可能结束,应是不断的认识和评价的过程,没有什么永恒的结论,一切都是相对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升沉浮降甚至修改、推翻原结论都不必大惊小怪。但是,新的评价必须要有史的意识,继往开来的坐标,把作家置入史的长河加以考察。书中一些文章,有孤立地悬置地评判是非的倾向,那就不是续接而可能是断裂。这十位作家至少都是很有影响的人,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笼统地彻底否弃的结果,是连历史一起否弃掉,导致虚无主义。这样说决不是要放弃批判,相反,我们太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批判了。
三是,此书商业炒作和市场运作的企图甚明显,什么“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等语,真是危言耸听,有靠“灭”名家以招徕读者的用意。这些话当然不是说给文学界人听的,也不是要搞真正的学术批判,而是要推向社会,抢占市场,刺激胃口,调动人们的猎奇心理的。说得好听,这是要文学批评走向社会化,大众化,市场化,说得更直白些,就是赚钱。这恐怕并非文学批评摆脱困境的正路。我们似乎可以承认有大众化的批评与学术研究性的批评的区分,但即使是大众化的批评,也只能靠它的审美性,科学性,活泼性,通俗性,敏锐性来征服读者,像现在这样的“暴动”方式是不明智的。文学批评固然没法背离市场,但非要充当市场宠儿的想法肯定是不现实的。
困境与出路
在我的印象里,文坛上好像随时随地都在议论批评的现状,有关部门过一段时间会强调一次加强文艺评论的重要性,批评家们也把它作为常设的话题不时站出来谈一通,看来对评论是优厚有加,最重视不过的了。可是反复谈论后的效果怎么样呢,恐怕是“效果甚微”。我怀疑关于评论的话语会不会也像评论本身一样,正在失去读者和文学界的兴趣。尽管如此,谈还是要谈的,效果甚微更要谈。文学不会死亡,评论也不会死亡。问题在于,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评论和我们的评论怎样才能吸引人。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按照习惯的话语方式和评论方法写就的评论文章看的人越来越少了,传统评论正在失去它的受众,它的对象。倘若一种活动失去了对象,就很难指望它有多大活力。有人挖苦说,现在的评论是自产自销,只有小圈子中人互相唱和一番,或者只对一个人有吸引力,那就是被评论的作家本人(作家好像也不买账,说他从来不读评论,是否属实,尚待考证)。这说法有所夸大,但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由于无人喝彩,评论的权威性自然大大下降。由于要读几十万言才能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评论的产量越来越低,以至批评家闻约稿而变色,视写作为畏途。的确,没有回应的写作,有如无法投递的“死信”,坚持者能有几人?所谓批评的“缺席”,该出面时不见出面,该说话时黯然无语的现象也就频频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