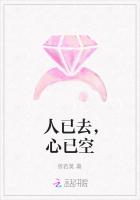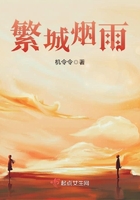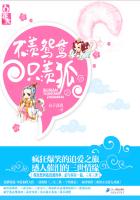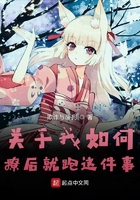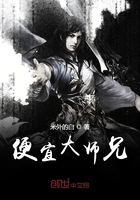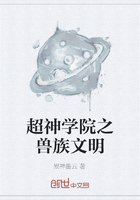人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时代在转动,文学必须围绕时代的转动而转动,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变形。就拿“时代与文学谁冷落了谁”这个问题来说,写一大本书也未必能讲得清。有人说,“现在是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没有史诗的时代和世俗趣味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只要不把话说到绝对,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根据。90年代以来(其实从80年代末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的确带来了近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审美意识的深巨变化。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凸显,也随着“斗争模式”的消解,虚浮的乌托邦理想的幻灭,生活重心从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移,使得多年来形成的以英雄史诗、革命赞歌、抗争姿态为主要形式,以崇高美、对抗美为主导特征的审美文化,逐渐让位于以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小品,轻喜剧,音像制品为基本载体的、以世俗性、消遣性、愉悦性为主要功能的大众审美文化了。何以会如此?论者金元浦曾这样描绘当今的精神现象:“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个人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向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待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日常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关怀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生存质量’……”(金元浦、陶东风《阐释中国的焦虑》17页)。依我看,这是触及到了审美文化变化的根本了。这位论者谨慎地使用了“一些人”“一批人”的限量词,当然很对,确实并非全部人和全部现象,但是,谁能说现在不是商品化的时代呢,他所指出的精神现象不足带有某种普遍的时代风尚的性质呢?
时代的风尚和大气候决定着文学的风尚和气候,应该说,是物化的时代冷落了原有形态的文学。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又发现,原先的文学的那种基于“斗争模式”的艺术思维,那种非此即彼的分析方法,那种只重视政治关系而忽视了远为丰富的其他社会关系和人性内涵的把握方式,确已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关系及其审美需求了。所以,不能只说时代冷落了文学,文学也冷落了时代。这种双向的“冷落”在一段时间里无法避免,互相适应的过程又会出现极其复杂错综的情景。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花样翻新,实验频频,尽力开拓视野和更新观念,那是文学在“争独立”,搞“接轨”,自行补课,抓紧时间完善自己。待到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自我深造的工程不得不缓一缓,于是,新写实出现了,写生存状态的文学出现了,调佩的“痞子文学”出现了,以解构为主要取向的新历史小说出现了,言情、武侠、休闲的文学大量出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出现了……这好像是文学对物化时代不得不作出的应急式回应。既想保持独立品格,又要顺应时尚,于是无法摆脱两难处境下的尴尬。不难听到人们对当今文学的不满声:对数量滔滔而质量不高的不满,对缺乏创新意识的不满,对匆忙与浮躁的不满,对回避尖锐矛盾的不满等等,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今的创作大多缺乏思想灵魂和道德理想的观照,缺乏深厚的人文关怀,不管它表面上多么缤纷多彩,热热闹闹,总体上却还算不得是有力量、有风骨的文学。物化时代最需要于文学的(尤其是纯文学),还是提供精神的抚慰,思想的启迪,人文的关怀,给物欲压抑下的心灵投注理想的光亮和审美的热力。就这个意义来看,当今文学的使命是很艰巨的。
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灵丹妙药,我们只能从直接面对的现实出发来思考文学的发展。脱离现实需要,从定义或先验出发,都不是切实的发展之途。我现在意识到,对今天的文学而言,不仅仅是个想像力够不够的问题,首先还是个真实的广度和深度充分不充分的问题。比如,今天一部分小说的审美趋势走向了日常性,就是一种向真实的深广挺进的努力。小说创作中的日常性是由当代生活的日常性所决定的。日常性是与突发性、事件性相对而言的。日常性曾使一些写惯情节小说的作者无所措手,因为借助于外力或某种模式的叙述,借助戏剧性、动作性、悬念性的写作,可使作者进入一种夸张的、假定的境界,与真实生活的间离,可能恰好帮助了它的作者的发挥。然而,生活如流,不舍昼夜,它最基本的状态还是日常性而不是突发性,今天我们的生活尤其如此。人们已经发现,侧重日常性的写作,往往更能透示生活的真谛,抵达生存的深层。人们或会提出疑问:新写实不就很注重日常性的写作吗,何劳你现在又煞有介事地提出什么日常性呢?诚然,新写实面对日常,能写出日常的“烦”,甚至如《风景》等作,写出一种深沉的生存相,但新写实太注重常态的哲学氛围,太注重“原生态”,太注重类的存在方式,切人现实人的欲望和精神矛盾的激烈程度不够,以及泼辣,不留情面和内在的力度,也不够。如果说新写实面对的是欲望之睡半睡半醒的生存,那么在今天提出直面日常性,就是要面对欲望之兽猛醒并强烈冲撞理性、道德之堤的现实,它理应比新写实发现更多更新的文学生长点。
我想以池莉为例。她是《烦恼人生》的作者,有开创性,但她近年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似更能得博市民读者的欣赏。作为小说艺术,她写得并不讲究,口语化却顾不上提炼,直白,外露,再加上调侃,结构上比较随意和散漫,还是新写实的余风,但是,你却不能不承认,她的小说是富于刺激力和吸引力的,很能抓人。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她不因纯文学之“纯”而拒绝世俗,对经济迅猛发展中形形色色的新市民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苦闷密切关注,而且,她又不满足于原先的经验和发现,不断以新的体验为创作开路。第二是,她敢于面对真实,外在环境的真实和内在灵魂的真实。她不回避今天都市的热狂甚至糜烂现象,她笔下的男女,如果是卑鄙的,那就把全部的卑鄙撕开给人看。且看这样的句子:“一九九六年的人类却已经是那么的居心叵测,利用灯光的目的是使黑暗更加黑暗,使原本单纯的黑暗变成复杂的糜烂的黑暗”,这当然是给王自力式的男人和段丽娜式的女人准备的出场词。她的作品里喧嚣着世俗的热浪,不难找到有关发财,性爱,享乐,人际关系,炒股,成名之类的最新消息,但不等于没有人文立场。第三,她的作法不停留在鲜活的展示上,而是有市民的生活哲学和人生智慧在里面,这也是吸引力来源。比如,“只有爱情在女人心中消失以后,女人才比较地聪明起来,可以用脑子思考问题了。矛盾的是,当一个女人没有了爱情以后,她的女人味也就消失了”,又如,“她的作法是自强自立,让那个男人后悔一辈子吧。当然,让男人后悔的同时女人也是很苦的了,让他后悔一辈子你就得苦一辈子,孤独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些话不是很俗又很哲学吧。
我在这里提到池莉,并非觉得只有像她这样写才好,文学的天地何其广阔,哪里会有疆界。我不过想借此指出,在今天,扩大和深化真实的领域,强化当代性,大胆揭示当代人的精神冲突,是比单独提出增强文学的想像力更能切中要害,对激发文学的活力尤其重要。整个90年代,写实的风尚占了压倒趋势,文学的视角由政治视角、意识形态视角更多地转向了民族文化视角,文学之树更加注意扎根于本土,这是很大的进步和转变。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写作,不但是作家个人的选择,更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艺术语言的新陈代谢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内外复杂因素碰撞的结果。但是,真正写出我们时代的巨大真实并与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相般配的作品还是太少了。出路不在于孤立地去写历史文化,而应是直面时代的真实,走向综合,更加自觉地追求社会层面,历史层面,人性层面,文化层面的交融渗透。
另一问题也很突出,那就是如何在创作中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理想的问题。我自己就多次写文章呼吁,一谈作品的缺点也总不忘指出这一点,弄到后来,有点像楚辞中的“乱曰”和聊斋里的“异史氏日”,成了开药方,与作品是两张皮,近似于说教和空喊。强调入文精神和道德理想当然是非常迫切的,现在的学人谁不知道它的重要,困难的是怎样在具体的创作中,在艺术形象的血肉之中将之渗透进去。这在今天难度就尤其大。被视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一些作品,写了困境,写了窘迫,写了妥协,精神的超越的确不够,对它们的某些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它们的作者却自有苦衷,他们可能认为,写了人物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妥协,并不就是作者自己也妥协,而是不得已。在他们看来,写的都是真的,生活原本就是这样,若为了人文精神的张扬让人们一反窘迫之态,而独来独往,挥舞铁腕,那就有可能牺牲了真实滑向很大空的老路。我想,能直面真的生存,写出严峻的真实,毕竟值得肯定,但若只顾及所谓真实,就事论事,那又有多大深度呢?在这里,我想引入一个观念,就是小说的“思考性”,强化思考性可能正是提升精神高度的途径。思考性的特点是,不对生活下判断,也不把生活矛盾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但它对生活进行紧张的思考,包括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富于思考性的小说,不用逻辑方式理解生活,不忙于为结果找原因,为行动找根据,为性格找特征,为心理找动机,为生活找故事,为故事找悬念。许多优秀的小说都具有这种良好的品性。这是小说这一具象的、流动的、排斥逻辑方式的艺术的本性所决定的,同时也非常适宜于我们这个特定的处于文化价值重建的时代。欲望与理智(包括人文精神、价值规范、道德、理想、信仰等等)的冲突是当今生活最主要的冲突,问题出在当今的理智层面无序、杂多,缺乏说服力。事实上,创作中人文精神的不丰沛,根源还在生活中人文精神的不丰沛,不必独苛责于作家。但作家是社会的良知,不能只当记事的“书记员”而不管精神,因而思考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这一点上,我欣赏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和《隐居的年代》。仅以前者而言,切入角度很小,写一个城市少女在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贱视人、漠视人、摧残人的年代里的成长。看起来避开了重大社会主题,却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生发出故事,在躲避“深刻”中开出深刻,在缺少诗意的年代发掘到诗意--一种忧伤的诗意。这个平常少女,遭到了双重的忽视,一是社会对她的忽视,这是不经意发生的,二是家庭、学校对她的忽视,被社会折腾得忙忙碌碌的家人,不兑现对她的承诺。这个作品揭示了人的被忽视所造成的内在的忧伤,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深刻的精神命题,同时又是世纪之交的90年代的重大精神课题。在当今物化、金钱化、世俗化、欲望化的社会,同样存在对人的忽视,只是更多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进行罢了。应该看到,90年代文化视野的进一步扩展,古今中外文学思想参照系的刺激,给文学创作注入了活力,一些高品位的文本相继出现。去年的中篇小说,以我有限的阅读所及,像陈世旭的《青藏手记》、李佩甫的《败节草》、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何立伟的《黄岩坡》、莫言的《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何顿的《慰问演出》、方方的《过程》、关仁山的《天壤》、肖克凡的《天津大雪》等,均以作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感悟为根基,是精心写作的产物。
最近从书籍市场传来的信息似乎不很乐观,“繁荣”了好几年的长篇小说订数猛然下跌,几近探底,文学期刊的订数大多也继续下滑,有人已经在设想着文学期刊“安乐死”的可能性。文学批评据说出现了“传媒化”倾向,似乎人们的兴趣已不在对文本的分析研究,而转向了关注文学事件的热闹。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的操作方式该寿终正寝了,有人在摸索如何用“跨文体写作”重新燃起读者的阅读激情。这些情况当然并不就意味着文学正在走向衰落,甚至也不必过分夸大它(圈内与圈外的逆差一向就存在,比如长篇在前几年很“热”,其实相当多的作品写得匆忙,在赶浪头,近来长篇比较能沉住气了,整体质量有上升,读者的热劲儿却又过去了。便是一例)。但是,这些情况又确实在提醒我们,现在早已不再是惊呼“狼来了”的阶段,而是切切实实面临着不变革自身、不强化自身就不能生存发展的问题了。对每一个出版社,刊物,作家,批评家来说,这种危机都是无法回避的。换句话说,文学更深地面临怎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进一步焕发活力和增大吸引力的问题。
现在大家常感慨文学读者群的萎缩,其实并非全怪读者见异思迁,兴趣转移,而是文学提供不出足以令他们怦然心动的思想和声音。缺乏思想魄力,新鲜感和提升力,是刊物和不少文学书籍平庸化的深层原因。百年中国面临世纪转折,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是不可能吸引读者的。当下出版物何其多,读者完全可以从随笔,政论,学术着作,纪实作品,以至所谓跨文体的写作中直接感应智慧的启迪,也就不必单从文学中苦苦寻觅了。必须看到,创作要有大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的问题。资源必须开掘,涵养,转化,变成作家自身的血肉。看一个作家是否是有出息的作家,要看他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的精神生活有无深刻的联系。一个作家能否写出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取决于他的精神视点的高度(这里所说的精神资源,主要是指人文精神,人文话语,价值来源,道德理想等)。现在,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发出过这样的困惑:“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安身立命的思想”,“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创造出中国的新话语和新思想”,“传统中的伟大思想也必须通过有创造性的新的洗礼,才能得到再生,与新情况新问题脱节的传统思想,即使经过所谓的转换,也仍然与现实需要是脱节的”。我们注意到,这些困惑是在经历了80年代的西学热和90年代初的国学热后,在今天真正意识到只有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既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又强烈感到必须立足于民族的本土文化来发展自身的背景上产生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