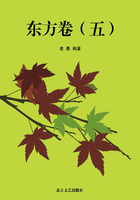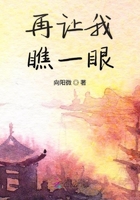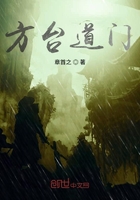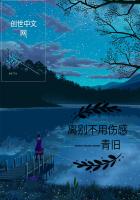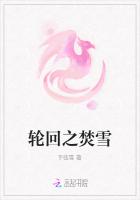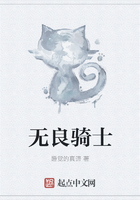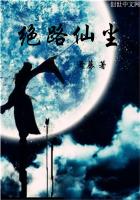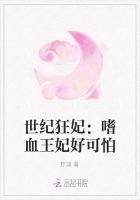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
每一个诗的季节里都有它的时尚和流俗,做一个既能传达那时代的脉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诗人是困难的。惯性力图裹胁所有的诗人用一种方式和共同的姿态发言,这对天才便意味着伤害;而天才一旦试图反抗那秩序,悲剧几乎毫无例外地便要产生。
本世纪中叶是中国新诗形势严峻的时代。绵延不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催使诗歌为契合现实需要而忽略甚而放逐抒情。民族的和群体的利益使个性变得微不足道。诗人的独特性追求与大时代的一致性召唤不由自主地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反差,在这样的氛围里诗人的坚持可能意味着苦难。对于此一时期从事创作的诗人,他们始终面对着难以摆脱的双重的压力,社会的和艺术的。国运的艰危要求并导引着诗歌对它的关注,其合理性当然无可置疑。但当时,缺少节制的直接宣泄已成约定的模式,采取别一方式而达于同一目标的艺术行为便自然地具有了反叛的性质。与此同时,艺术走向民间的呼声日隆,在此一倡导的背后,则有着近于浮表的形式上的同一化要求。这意味着诗人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表现民众,而且应当采取民众熟悉的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将诗推向一体化的极限。
我们此刻谈论的穆旦,便出现在上述那特殊的背景之中。时代孕育并创造了天才,但时代在创造天才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他的扼杀。因此,如何忠实于他的时代并勇敢地坚持自有的艺术方式,便成为对诗人品格独立性的严重的考验。因为他敏感于四方的风景,并以他特别的坚定体现诗歌的自由,穆旦于是无愧地成为一面飘扬的《旗》:
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
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
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
在长长的岁月里,穆旦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题目。他曾经闪光,但偏见和积习遮蔽了他的光芒。其实他是热情的晨光的礼赞者,而粗暴的力量却把他视为黑夜的同谋。像穆旦这样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可纪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迹的诗人不会很多--学生时代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全程3500华里,沿途随读随撕读完一部英汉辞典,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25岁以中国远征军一个成员的身份参加滇缅前线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严重的生死考验;1952年欣慰于新中国的成立,穆旦、周与良夫妇在获得美国学位之后谢绝台湾和印度的聘请毅然回归祖国--何况他还有足够的诗篇呈现着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祖国和民众的赤诚。但是,仅仅是由于他对诗的品格的坚守,仅仅由于他的诗歌见解的独特性,以及穆旦自有的表达方式,厄运一直伴随着他。穆旦自50年代以来频受打击,直至遽然谢世。他的诗歌创作所拥有的创造性,他至少在英文和俄文方面的精湛的修养和实力,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都是来不及展示,或者说是不被许可展示的天才。彗星尚且燃烧,而后消失,穆旦不是,他是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我们只是从那浓云缝隙中偶露的光莹,便感受到了他的旷远的辉煌。中国新诗自它诞生之日起,便确立了实现中国古老诗歌的现代更新的目标。对于促进和实现诗的现代化,中国诗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中国诗歌传统宏博绵远,正因为如此,它同时也拥有并体现出它的保守和惰性的特点。因而,中国诗在其引进现代性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诗学一直抗拒现代主义甚至外来的其他思潮。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尽管有诸多诗人作过成功的尝试,但它从来没有成为主流,现代主义的诗潮在中国一直处境不佳。
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忧患,从3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现代主义的余绪逐渐趋于消失。与现代主义的弱化和消失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古典和民间诗潮的再度兴起并走向鼎盛期。40年代中国新诗的民间化受到强大而权威的理论的支持,它直接承继并强化了“红色的30年代”革命诗歌运动的成果。它依然无可争议地代表了中国新诗的时代主流的地位,这种事实成为新诗引进和加强现代意识的巨大障碍。
但现代主义的火种并没有在中国熄灭。在重重的农民文化意识的包围之中,战时的中国后方城市尤其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个学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昆明,那里集聚了一批既具有传统文化积蕴又与当时世界先锋文学思潮保持最密切关联的著名学者和青年学生,他们代表了学院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联大师生以其开放的视野、前驱的意识和巨大的涵容性,在与大西北遥遥相对的西南一隅掀起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主义的“中兴”运动。当时在西南联大执教的一些著名的学者、诗人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燕卜荪等,有力地支持并推进了这一火种的燃烧。
若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称为“中国新诗的摇篮”,则此时的西南联大同样可以比喻为振兴并发展中国现代诗的新垦地。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再一次迸发了建设中国新诗的热情。穆旦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据有关材料介绍,他也就是在这里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甚至对狄兰托马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师的影响下,由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的投入,中国新诗史掀开了值得纪念的新页。
穆旦具有作为诗人的最可贵的品格,即艺术上的独立精神。这种品格在巨大的潮流(这种潮流往往代表“正确”和“真理”)铺天盖地涌来从而使所有的独立的追求陷入尴尬和不利的境地时,依旧对自己的追求持坚定不移的姿态,其所闪射的就不仅仅是诗人的节操,而且是人格的光辉了。这一点,要是说在40年代以前是一种不愿随俗的“自说自话”,那么,在艺术高度一体化的50年代之后,穆旦的“个人化”便显示出桀骜不驯的异端色彩来。
穆旦生当中国濒临危亡的最艰难的岁月,在这样的年代里,穆旦也如众多的中国诗人一样,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抗争。这表现在他的行动上,也表现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但不同的是,穆旦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传达他对他所热爱的大地、天空和在那里受苦受难的民众的关怀。在这位学院诗人的作品里,人们发现这里并没有象牙塔的与世隔绝,而是总有很多的血性,很多的汗味、泥土味和干草味。但在穆旦的笔下,这一切来源于古老中国的原素,却是排除了流行款式的穆旦式的独特表达。在《出发》、《原野上走路》、《小镇一日》等一些诗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鲜活的人生图画和真实的生活脉搏。当然最出色的表现还是《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那里有一幅旷远的、甚至有些悲哀的北京原野的风景--
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
木格的窗纸上堆着沙土,我们在泥草的屋顶下安眠,
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
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
从屋顶传过屋顶,风这样大岁月这样悠久,
我们不能够听见,我们不能够听见。
了解中国北方农村的人读穆旦这首诗都会感到亲切。腊月夜晚寒冽的风无阻拦地吹刮,风声中有婴儿的啼哭,这一切让人升起莫名的怅惘甚至哀恸。前面说的穆旦诗的泥土味即指这些,他对中国厚土层的深笃的情怀不比别人少,但他显然不把诗的目标限定于现实图景的反映或再现。穆旦从这里出发,他通过这些情绪和事实而指向了深层。岁月这样悠久,我们无法听见。但是,当无声的雪花飘落在门口那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和大车上面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诗人对中国大地以及生活在古老村落里的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穆旦的诗让我们想起恒久的悲哀:为人类的生生死死,为无休止的辛苦劳碌。
读穆旦的诗使我们置身现世,感受到真切生活的一切情味。他的诗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纯诗”,他的诗是丰满的肉体,肉体里奔涌着热血,跳动着脉搏,“这儿有硫磺的气味碎裂的神经”(《从空虚到充实》)。但是,穆旦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对于30年代以来、40年代达于极盛的把诗写得实而又实甚至沦为照相式或留声机式的崇尚描摹和模仿的潮流而言,穆旦却有他的一份超然和洒脱。他的诗总是透过事实或情感的表象而指向深远。他是既追求具体又超脱具体并指归于“抽象”他置身现世,却又看到或暗示着永恒。穆旦的魅力在于不脱离尘世,体验并开掘人生的一切苦厄,但又将此推向永恒的思索。他不停留于短暂。穆旦把他的诗性的思考嵌入现实中国的血肉,他是始终不脱离中国大地的一位,但他又是善于苦苦冥思的一位,穆旦使现世关怀和永恒的思考达于完美的结合。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众多的苦难涌向并充填社会的每个角落。普通的中国人,从农工劳苦者、士兵到知识阶层无不承受着巨大的实际的和精神的压力,他们的心灵深处都装满了关于苦难的诸多具体的图象。顺从潮流的诗人,轻易地把这些图象组装成他们的诗句。但穆旦不同,他显然仅仅把这看成是切入的初步。穆旦的始终努力在于通过这些丰富的事实进入关于整个民族生命存在的久远的话题:他的诗句穿透大地的表层穿透历史的沉积,他展现人们感到陌生的浩翰的精神空间。他写《不幸的人们》的不幸不仅是现实的“伤痕”,而是--
是谁的安排荒诞到让我们讽笑,
笑过了千年,千年中更大的不幸。
诞生以后我们就学习着忏悔,
我们也曾哭泣过为了自己的侵凌,
这样多的是彼此的过失,
仿佛人类就是愚蠢加上愚蠢--
像一名逃奔的鸟,我们的生活
孤单着,永远在恐惧下进行,
如果这里集腋起一点温暖,
一定的,我们会在那里得到憎恨
这就是穆旦的沉郁,他看到受别人忽略的东西。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的心灵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忧患。但他从不排拒他自己灵魂苦难的体验,而且往往是由此深入推进,由个人而推及整体,由现在推及绵渺。他的无情的鞭笞,抽打的首先是他自己。“虽然生命是疲惫的,我必须追求”;虽然“观念的丛林缠绕我”,“善恶的光亮在我的心里明灭”,但他显然拒绝“蛇的诱惑”而再度偷吃禁果。他不断拷问自己:
“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
为什么?”
(《蛇的诱惑》)
穆旦的这种自我拷问是他的诗的一贯而不中断的主题。写于1957年的《葬歌》,写于1976年的《问》,不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都坚持这种无情的审判。“是不情愿的情愿,不肯定的肯定,攻击和再攻击,不过酝酿最后的叛变”(《三十诞辰有感》),站立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之间,揭示自我的全部复杂性,这是穆旦最动人的诗情。穆旦作为20世纪后半叶非常重要的诗人,他展现那时代真实的残缺和破碎,包括他自己矛盾重重的内心世界。前面说的他写的不是“纯诗”,即在于他诗中出现的都是一种“混杂”的平常。他就是在这种混杂中思考社会和个人:在被毁坏的楼里,“发现我自己死在那儿”,而楼外的世界--
洪水越过了无声的原野,
漫过了山角,切割,暴击;
展开,带着庞大的黑色轮廓
和恐怖……
(《从空虚到充实》)
在穆旦的诗里找不到“纯粹”,他的诗从来不“完美”,仿佛整个20世纪的苦难和忧患都压到了他的身上。他不断听到“陆沉的声音”,他默默守护着“昏乱的黑夜”,他被“黑暗的浪潮”所拍打,这是一颗骚动不宁的灵魂。但是,“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进这黑夜里不断的血丝……”(《漫漫长夜》)。正是由于他的诗保存这么多的罪恶和苦难,我们说穆旦因传达这时代真实的情绪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恰当的。
话说回来,要是仅仅从穆旦的诗传达时代的实感方面考察他的贡献,那就等于忽略了穆旦最重要的品质。我们不能忽视穆旦作为学院诗人所具有的“书卷气”。他绝不媚俗,他的诗给人以庄严的感觉。他总是展现着良好教育的高雅情调,此种情调使他的诗具有明显的超越性。他的忧患不仅在于现实的际遇,他的忧患根源于人和世界的本身。穆旦不是“写实”的诗人,穆旦的沉思使他的诗充满哲理,这就是他的“抽象”,但又恰到好处,生活中的许多疑惧,他不竭地追寻回答,而回答又总是虚妄,这造就穆旦式的痛苦。“我不再祈求那不可能的了,上帝,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向自己说》),我们从这种绝望中发现深刻。于是我们发现穆旦对绝望的抗议--
零星的知识已使我们不再信任
血里的爱情,而它的残缺
我们为了补救,自动的流放,
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信仰,
这是死。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
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
(《控诉》)
穆旦的诗充满了动感。他无时无刻不在展示那外在世界的冲突和内心痛苦的骚动。穆旦从来不用优美和甜蜜来诱惑我们,他的无边的痛苦从不掩饰。而在痛苦的背后,则是一颗不屈心灵的抗议。穆旦的抗议有现实的触因但基本不属于此。诗人的敏感使他超前地感到了深远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基于个人,甚至也不单是社会,而是某种预感到的无所不在的“暴力”的威胁:“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到文明的精密的计算”(《暴力》);他是那样的厌恶那些与高尚心灵格格不入的世俗气以及“普遍而又无望的模仿”(《我想要走》)。作为渴望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诗人,他几乎是以决绝的姿态抗击对于个性的抹煞和蹂躏。这是《出发》里的诗句--
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
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
被大量制造又该被蔑视
被否定,被僵化。
这首诗中还有更为惊人的揭示:“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他是真实,他从这种“丰富”中感到“丰富的痛苦”。
写于1947年的《隐现》是迄今为止很少被人谈论的穆旦最重要的一首长诗。整首诗吁呼的是不能“看见”的痛苦,“因为我们认为真的,现在已经变假,我们曾经哭泣过的,现在已被遗忘”。他的诗表现当代人的缺失和疑惑,他诅咒那使世界变得僵硬和窒息的“偏见”和“狭窄”。这首诗以超然于表象的巨大的概括力,把生当现代的种种矛盾、冲突、愿望目标的确立而又违反的痛苦涂上一层哲理的光晕。这对于40年代非常流行的“反映现实”的潮流而言是一种逆向而进的奇:他在这里继续着对于心灵自由的追寻以及对于精神压迫的谴责: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