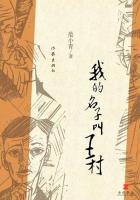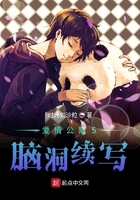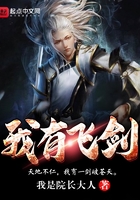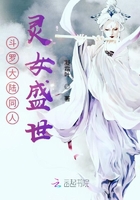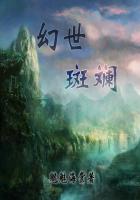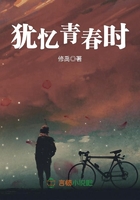在理解“晚生代”的历史位置和创造的文学经验时,同样有必要强调历史给定的前提。杰姆逊曾说过,一个历史主义者会作这样的思考:“……发挥着功能的现存意识形态的生产,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是有区别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或许会有这样的历史情境,意识形态的协调和生产都不可能了一一这似乎就是我们在当代危机中的处境。”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也许正处在这样的历史情境,意识形态创建的想象关系不再能从整体上对社会起支配作用,也不再能直接支配文学叙事。不断涌现出的新的群体,正处于文化脱序的空隙,他们的游走和进入一样,既没有目的,也没有结果。对于不再能历史化的现实来说,对于没有本质的“现在”来说,写作本身建构着可理解的现在。因而,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来说,它只依凭于“剩余的想象关系”来展开它有限的推论实践。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原载《新左派评论》,1984年夏季号。本文转引自《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的文学更像是处在一种“剩余状态”,不管是就叙述主体所处的现实位置来说,还是那种叙事方式和态度,或者是那种价值标向和美学期待,都只能抓住和运用剩余的想象。“剩余状态”表明文学及其文化实践不再依凭于意识形态的巨型寓言,不再致力于建构社会共同的想象关系,写作者与思想者退居到个人的立场,放弃永恒的、绝对的终极价值关怀,回到个人的记忆,注重那些细微的差别,试图从这里折射出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只能用可能性和相对性视点来看待人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在这一意义上,“剩余的想象”并不仅仅表征着“后新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内的某些暂时的进向,它很有可能就是后工业化社会给予文学的历史境遇,很可能是文学叙事者抗拒后工业化社会的无可奈何的武器。1977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出版了他的那部久负盛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部著作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它的理论价值。威氏把文化划分为“主导的、剩余的和崛起中的”(dominant,residual,emergent)。尽管“剩余的”与“崛起中的”文化固然有可能被主导文化吞并的因素,但威廉斯认为,这些文化代表了主导文化以外或与主导文化对抗的经验和实践。剩余文化是指那些“往日有效地建立的”意义与价值观,而“在文化进程中仍积极地在今天扮演着一个有影响力的元素”。威廉斯尤其对与主导及剩余文化都不同的崛起中的文化给予特别重视,他强调说崛起中的文化“永远不单只是一个即时的实践;它的关键是在寻找新形式或改变形式”。显然,在这里,我借用了威廉斯的概念,但修改了他的原意。在我看来,剩余文化是从主导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不完整的文化部分。它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与主导文化保持亲和性,它延续了主导文化的价值观和实践方式;另一部分更倾向于崛起的文化,不如说它是主导文化分裂时抛出来的碎片,它倔强而又怪戾地生长,但特殊的历史情境使它无法成为有巨大创造性的崛起的文化。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现实,使得任何试图创新的文化都大打折扣,它不再能形成巨大的有效的历史冲动。它是新时期有过的庞大的精神实践遗留的产品,它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对人类精神生产活动进行有效的缩减后的剩余物。因而,第一,它是历史的遗留物;第二,它是社会现实缩减的剩余物;第三,它还是自身的剩余物一一文学这个古老的文化样式,它很有可能确实是走到它的尽头了。正如米兰·昆德拉在预言小说的未来道路时说的那样:“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已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描述文学的命运。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在后工业化时期,在视觉符号帝国的霸权之下的生存,就被注定了它的“剩余性”的境遇。因为这样的历史前提,“晚生代”面对“现在”的写作也就被决定了它的特征和有限的意义。他们被历史迅速造就成咄咄逼人的“新锐”,但历史同时也只给他们提供一夜狂欢的模拟剧场。
对“现在”进行直接书写,这本来并不是什么惊人的艺术创造,但是当代文学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无力把握当代中国的生活现实,无力揭示新的生活经验和提供新的现实图景,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缺憾。因此,当有一批人以现在进行时来书写当代生活时,他们就迅速站在当代文化的前列。如果说“先锋派”的形式探索,乃是文学史的历史语境给予其以特殊的革命意义,那么,“晚生代”作为一种创生的历史力量,则是当代现实直接给予他们存在的依据。90年代初期,新时期的宏伟叙事实际上已经无法整合多元分化的文学格局,新时期构造的那个“巨型语言”已经破裂,那些现代性企图,那些启蒙主义的伟大规划,已经为当下的生存利益所替代。只有经济能改变人们的生存境遇,人们也只相信经济利益构成全部生活的意义。商品拜物教与消费主义构成了这个社会轰轰烈烈的外表,没有人相信精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切都变成“现在”一一没有历史、没有未来、没有内在性的“现在”,就是人们存在的精神飞地。因此,富有现实敏感性的人们,如何顿、邱华栋、述平、张竁、东西、刁斗、李冯……抓住“现在”,直接表达他们的“现在”感受,则构成当代文学的特殊景观。然而,正因为他们只有“现在”,只有“现在式的”书写,这也就使他们的写作存在根本的局限。
他们的写作没有与文学史对话的愿望,对存在与意识之类的复杂关系一概弃之不顾,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融为一体,他的那些不加修饰的逼真性的叙事,带着生活原生态的热烈和躁动,使那些粗痞的日常现实变得生气勃勃而无法拒绝。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叙事从来不诉诸于形而上观念的批判性表达,而是限定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体验和感觉之中。非历史化的现在表象,转瞬即逝的个人化感觉,语言表达的任意喷涌,情绪宣泄的狂欢特征……所有这些都在建构一个无历史也无本质的“现在”的幻象。无可否认,建构这种“现在”的幻象是必要的,它是逃离真实的历史现在的精神飞地。由此,这代人的文学叙事在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特征方面,具有其他人所不具有的那种直接性。但过分生活化、过分经验化,也显得缺乏文学的历史感和思想的复杂性。这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也使他们的叙事缺乏变化和更强、更长久的冲击力。无法找到准确的插入点,这使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受到相当的局限。如何进入当代生活的多重结构,如何在更复杂和深广的意义上,去书写我们面对的“现在”,以“本质性的写作”去写作当代本质性(无本质)的生活真相,这是他们面对的困难。年轻一代的作家基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不再依靠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给出现实的本质性意义,但是,面对“现在”的写作,也不是单纯表面化地记录生活,自然主义式地描写生活。对“现在”说话,也不只是建构“现在”的幻象,提供仿真式的“现在”文本,给当代消费主义时尚提示粗浅的精神地形图。年轻一代的作家也许更应该在拒绝把先验本质强加给“现在”的同时,在多元性的意义上,给出“现在”丰富而生动的存在。这种“给予”,不是证明式地给出它的必然的、绝对的、永久性的本质存在,而是在开放的、变动的、谬误的、自我颠覆的意义上,给出“现在”的复杂的历史情境。这当然是一种高难度的文学叙事,但也不是说就根本做不到,关键取决于这一代作家是否积极而主动地去认识和理解他们所面对的“现在”。
新时期的“宏伟叙事”解体之后,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倾向于“小叙事”。文学不再去表现时代惊天动地的变化,去呼唤或指引人们朝某个共同的目标行进。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变成生活的抚慰剂,变成填补闲暇的精神消费品。因此当代小说看上去呈两极发展,对古旧历史生活的叙述和对当代生活的表现。前者大部分不过是些年代不明的古代传奇,后者则更像是后当代传奇。当代生活变成一系列的奇观,这使当代小说在寻求新的适应性方面找到一条捷径,但也牺牲了当代小说叙事已经创立的那些艺术经验。更年轻一代的作者在制造当代生活的奇观性方面无疑提示新的生活经验,但其叙事视点缺乏变换,人物没有必要对抗性和生存位置的颠倒,在人物与他人、与社会的权力网络、与庞大的历史潜本文之间缺乏复杂而多重的关联。他们显然无力给出“现在”的本质,因此,他们只是写作“现在”,而不是“反映”现实。在他们的叙事中,这个“现在”本身处在一个历史的断裂带,或者说,“现在”正在制造这种断裂带。没有历史本质的现实,只能是“现在”,所谓回到生活本真状态的现实,不过是没有本质的“现在”的另一种表述。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都要进行形式主义实验,而是说小说应该有一定高度和复杂度的叙述意识,这种叙述意识未必要延续先锋派小说曾经进行过的探索老路,恰恰是融化在对当代生活的全方位表现方面,对当代有生气或没有诗意的生活重新进行编目,这需要更高的叙述视点,更广阔的叙述视野,更强的思想穿透力度。
三、激进的断裂:超越现实的异类写作
如何面对“现在”说话,确实是当代中国作家最为困难的处境。大部分作家采取了把现实虚幻化和仿真化的书写方式,把个人的直接经验作为文学表达的基础,这样文学表达就很容易与当代社会和解。文学的写作和传播都立足于当今消费社会,而文学也不再具有传统的经典化期待,也不期望成为永恒价值关怀的必然延续。但现时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代,总有人试图面对现实说话,试图去抓住现实本质。这无疑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反抗困境的奋战,凭着尖刻的长矛,现时代的堂·吉诃德并不能击中现实的本质。也许90年代最后几年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作为文学生产的主体,作为最能切中当代生活的文学写作者,他们不再是文学总体性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企图(或者已经?)突出墙围,而站到文学史的另一面。现在,有一种处在文学现有体制之外的“异类”写作的存在,他们几乎是突然间浮出历史地表,占据当代文学的主要位置。尽管大多数人还对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只要稍微客观地了解一下当代文学实践的实际情形,那些主要文学刊物的主要版面,那些销量最好的文学图书,那些为青年读者和在大学校园谈论的对象,就不难发现,过去文坛的风云人物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都是一些怪模怪样的“新新人类”。实际上,人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十年前,对当代文学最有影响(其好坏另当评说)的作家是王朔这个叛臣逆子,他改变了作家对文学和对社会的态度。自从王朔之后,文学在其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民族一国家的事务,时代精神的象征,而是个人的一种职业选择或业余爱好。数年之后,王小波再度成为文坛的一股旋风,虽然这股旋风由一起悲剧性的死亡事件引起,但王小波突然间打开了文学写作者的社会空间,这个人长期在文学体制之外生存,他对自由写作和个人化写作这种闪烁其词的说法,提供了公之于众的契机。作为一种象征行为,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打破了文学制度垄断的神秘性,表明制度外写作的多种可能性。1998年,对于中国文学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年份,但却是所有的矛盾和暧昧性都明朗的历史关头。这一年有几个事件值得注意,它们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多数人也许毫不在意或不以为然。但我想这些事件在这同一时期发生,使每个事件都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
1.断裂:符号权力的生产与分配
1998年,《北京文学》发表由朱文主持的问卷调查,题为《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以下简称《断裂》),断然对文学现存的秩序,文学面对现实的态度和方式尖锐提问。这在平静慵懒的1998年的文坛,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尽管见诸于媒体的反响极少,但私下的议论还是掩盖不住人们剧烈的反应。尽管贬斥的意见远多于肯定的见解,但依然无法否定这个行为具有的空前的象征意义。中国文坛居然有一群人敢于突然公开他们的态度,把自己明确界定为主导文化之外的“异类”,这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还是首次出现的咄咄怪事。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推崇的行为,但它的象征意义却不可轻易忽视:它标志一种异类的文学,一个异类的文学群体正在茁壮成长,它们生长于强大的总体性制度之外,但却又奇怪地构成当代文学有活力的部分。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习惯理解的文学、文学界、文学群体、文学流派、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等等,总之,传统的文学从社会化组织结构到精神实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也没有理由对此熟视无睹。
问题可以回到那份问卷。在这份称之为《断裂》的东西中,汇集了56位6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对现存文学秩序的直率批评。他们中有些人对前代作家充满了敌意,毫不掩饰他们的蔑视,他们拒绝承认与前辈作家有任何精神联系。他们对几家主流刊物进行了攻击,对文学批评和大学的文学教育以及汉学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贬损。这份问卷的发表,几乎是突然间公开了这代人对文坛的态度,其带有表演性的激进而不留余地的姿态,当然也激怒了不少人。一些人认为,这份问卷显得过于偏激和自以为是。无可否认,这份答卷中有些人出言不逊,某些言辞无疑过激偏狭,不无恶作剧的味道。但个这里之所以用“异类”这个词而不用“另类”,是因为“另类”这个词被用滥了,它只是某种时尚化的文化象征;而“异类”则多少包含真实的革命性和反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