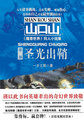这个一直得不到“父亲”认可,并且一直为“父亲”所拒斥的观念之子,现在却如此急切与父同化,这个融自然、历史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父亲”显然是超现实的更加观念化的“父亲”。通过想象性地与父同化,也就是在“超现实”的想象性放大中,与自然之父同化的苦难之子结束了他的幼稚而孤独的岁月,畅游北方四条河不过是一次想象性地施行“成人礼”的伟大仪式:“我就要成熟了……我就要成人了……他心里充满了神圣的豪情。我感谢你,北方的河,他说道,你用你粗放的水土把我哺养成人,你在不觉之间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同时注入了我的血液。你用你刚强的浪头剥着我昔日的躯壳,在你的世界里我一定将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战士。”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正是那个时期个性解放、寻找自我的最充分的表达。
80年代中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引起强烈反响,那种洋溢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给一代青年及时提示了自我意识(自我观赏)的镜像。那已是一个自我意识与日俱增的时期,当然也确实是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时代: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过热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消费指数急剧上升,抢购风与通货膨胀展开角逐……不满与期待,忿恨与躁动,希冀与梦想,混为一体;挡不住的诱惑,摸着石子过河,跟着感觉走……人们既为现实的不公不平痛心疾首,也为眼前的机会激动不安。在这初具规模的竞争时代,人们需要成为强壮的自然之子。张承志的激情其实不过是焦虑的最高表现形式,通过狂乱的激情式的宣泄,焦虑的化解也获得了虚假而夸张的形式。张承志的抒情是对焦虑的浅薄理解,正如梁晓声对焦虑的草率超越一样。人们不再需要深思熟虑,不再需要忧伤徘徊。
“文革”已经过去近10年,人们不再是被那个狗杂种抛弃的无父之子,在现实与历史的重新结合中,人们找到了生命之源,找到了现实的力量。由于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并渴望迅速成为历史主体,历史的边际效应不再是以政治无意识的形式构成一种冲突性张力,而是与主流历史达成同化,最大可能地构成主流历史的最有活力的部分。80年代中期真正是这代人的黄金岁月,他们刚刚步入历史中心,一切都似乎刚刚开始,也因此预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他们的精神和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似乎必然要决定着历史的真实方向。随后的历史变动,才使这代人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实的历史潜本文。
六、跨越现实的两种方式:寻根派与现代主义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期,已经汇聚了多样化的经验,历经“朦胧诗”论争,伤痕文学与人道主义讨论,改革文学的热潮,知青文学重新唤起的理想主义,这些阶段性的高潮,使文学在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就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言,它已经达到巅峰状态,这使文学不得不反省,这时它也有能力开始寻求艺术上的突破。80年代中期,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反反复复进行着各种斗争,但关于人道主义和主体论以及异化问题的讨论,必然使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主流历史构成一种张力,若隐若现的历史边际效应似乎预示着更剧烈的历史冲突一一要么分离,要么断裂。而文学方面,普遍为一种乐观情绪所支配,似乎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可以标志整个社会的变革,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变得理直气壮,因为它反映了历史的主导精神一一它是现代化的文化象征,也是它必然的精神成果。这种想当然的推论却使历史的边际效应得到一次空前的强化,自以为与主流历史同步并且同化,但实际却是在撕扯和突破疆界。文学上的现代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资源,实际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沿着另一边际推进。这就使90年代的学院思想具有了一一也许是因为代际的变化而被迫地具有了一一某种独立性。但那时与时代精神(现代化)相契合的整个思想基础,却无疑是后来的前提。
很显然,寻根口号的提出和具体实践都是历史主流要求的反映,这一切都源自于现代化现代性的历史愿望。“寻根派”的崛起显然与当时国内风行的“反传统”思潮有关(反传统当然是典型的现代性的思想动机),然而,在当时激烈的反传统呼声中,文学界何以会热衷于“寻根”?何以会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时与海外儒学复兴潮流遥相呼应?实际上,“寻根”也依然是一种命名,在这个名义之下,历史实践则要依据它直接的现实前提,“寻根派”由知青群体构成则是这一现实前提的基本事实。知青文学其实过于专注个人的情感记忆,当他们要以群体的姿态跨越现实进入历史时,依然抹不去个人的经验与情感记忆。酿就“寻根”的契机可以追溯到1984年12月在杭州西湖边一所疗养院里的聚会,随后(1985年)各种关于“寻根”的言论见诸报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这些文章引起热烈反响,标志“寻根文学”形成阵势。虽然“寻根派”在1985年底打出旗号,而事实上被推举为“寻根派”的代表作品不少是在此之前面世的,甚至更早些的知青文学在“大自然主题”中就蕴含了那些异域文化风情。韩少功明确提出要寻找已经迷失的楚文化的源头,他声称:寻根“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的浅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但事实上,“寻根派”的写作不是遵循“寻根”的宗旨(寻根本来就没有宗旨),而是遵循知青的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那些记忆中的贫困山村,那些异域风情,那些人伦习俗,原来不过是作为找回失去的青春年华的背景,作为蹉跎岁月的精神磨难的陪衬,现在却浮出历史记忆的地表,成为写作的前景材料,先是获得自然的生命强力,随后被赋予了历史的和文化的意义。其意义也奇怪地具有二重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二重性:或者具有温情脉脉的人伦美德,显示出中国传统的精髓;或者是令人绝望的劣根性。就是把楚文化想象得无比美好的韩少功,一旦落到具体的写作中,却写出保持古风的山民文化的愚昧与顽劣不化。
郑义的《远村》(1983)后来被推为“寻根”的代表作。郑义以极其细腻的笔致刻画西北山村的风土人情,夏夜的温馨,山坡上的青草味,凄楚的山歌,牧羊人的忧伤……这一切纯净而亲切的气氛,给杨万牛18年“拉边套”的爱情悲剧注入无边的抚慰。郑义写出生活境遇中的那种绝望的忍耐,写出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情调。与其说在寻找民族生存之根,不如说是在发掘历史残存的苦难,它无助于反省现实,却足以提示一种审美观照的情境。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当推韩少功的《爸爸爸》(1985)。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尚处于蒙昧状态的落后部落的故事,这里远离现代文明,贫穷、野蛮、懦弱而无知。每个人都没有独立的价值,不过是这个愚昧集体的一个被动角色,他们自觉屈从于宗族的权力和习惯。祭祀、殉古、打冤、迁徙……一切都习俗化、仪式化了。不管是老辈人之间的冤仇结恨,还是有点改革意识的人物仁拐子,都不妨碍这种生活习惯的日常运转。作为故事主角的丙崽却是一个白痴,由他提示的视角则使整个部落的活动显得更加怪诞。《爸爸爸》表达了对国民劣根性的寓言式的批判,精当地运用了象征、隐喻等手法,特别是丙崽这一叙述视角的强制性运用,有效地捕捉到了那种疯狂与麻木相交合的生存状态。阿城的《棋王》、《孩子王》以及后来的散文集《遍地风流》,明显是“知青文学”的变种,其中也确实有一种淡泊沉静的文化意味,直逼庄禅境界。开始是史铁生,后来是阿城,把这个书写时代和历史的文本,转换成知青的个人记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转折,但这一转折并没有在原来的个人化和私人性意义上被认同,而是同样向着时代精神的宏大叙事方面加以展开。阿城的文笔清俊精炼,自然天成,但他的文化领悟并没有更深地回到个人的内心生活,而是更多地依赖某种传统典籍。在80年代中期,阿城的平淡居然令寻求现代主义创新的文坛一片叫好,这看上去多少有些奇怪,除了李陀的推波助澜起到一定的作用外,也与阿城表现的所谓的文化品味缓解了时代的精神焦虑有关。不管是阿城的语言文字,还是文体风格,那种平静的莫测高深,都显得似是而非却耐人寻味。思考历史、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命运这些宏大的主题,中国作家一直力不从心,经历过张承志和梁晓声的激情的冲击,一代青年作家几乎是精疲力尽。寻根是对现实的回避,是对明确的现实责任感的背叛。例如,寻根是对改革文学的背叛,寻根显示出它的机敏与狡智,它不作笨拙的、虚假性的历史承诺,它避实就虚,越过一道并不存在的历史界线而回到个人记忆。寻根以其不可知论的神秘与含混,使一代知青作家采取逃避的方式。它并没有被认为是回到个人的记忆,而是被理解为一一也理所当然被这些作家自己理解为一一站在文学创新与历史反思的双重边界。寻根与其说是对时代的精神焦虑的超越,不如说是掩饰。寻根的意义从来没有在个人记忆的意义上得到理解,而是作为艺术创新和思考“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宏大神话被加以塑造。结果,寻根依然像是丢失了某种生存依据式的焦灼和找到后的夸大的兴奋和激动。(例如寻根在莫言那里达到高潮和结束也可说明这一点。)当然,寻根文学回避了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暴露出的尖锐的现实矛盾,在审美的客观效果上也掩饰了那种紧张的焦虑感。作家们确实沉浸在文化之根的寻找中,这使他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寻根不再是解决紧张的处于困境的现实难题,而是寻求一种历史记忆,寻求一种文化趣味。如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张炜的《古船》(《当代》,1986年第5期)并不是刻意的“寻根”作品,文化价值及其折射出的美感,构成作品最重要的美学品质。作为知青作家的王安忆,《小鲍庄》显然与她的知青记忆有关,但现在知青的视点已经隐匿,那些乡土中国的背景成为叙事的主体部分。这个与现代文明几乎隔绝的小鲍庄显然保持着一整套的宗法制社会的制度习俗,当然也保持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仁义道德”几乎就是它的核心。贯穿全书的小主人公“捞渣”几乎也是“仁义道德”的化身,他最后舍己救人,也就是舍身成仁,这使人想起小英雄雨来,只不过王安忆把意识形态的经典叙事,改变为中国传统的“仁义”在显灵。为了加强文化感,王安忆甚至不惜加上一个“文化”,作品中曾有两个小孩对话:“你知道,人是打哪里来的?”文化问。
小翠扑哧笑了:“娘肚子里生出来的呗……”文化微微一笑,不与她斗嘴,继续深入问道:“娘是打哪儿来的?”
为了探讨文化之根(生命之起源),不惜将两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变成小大人,思考人类的起源,“文化子”则像是乡间智者,甚至还粗通现代进化论。
张炜的《古船》写鲁北某小镇两户大姓人家几十年的斗争历史,传统的宗法制社会里的斗争延续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作者力图揭示的是中国社会内在的封建主义本质,从古至今,乡土中国的掌权人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力结构,封建伦理根深蒂固地支配着乡土中国的群体社会,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任何独立自由,而统治者也被权力所异化。张炜以及其他相当多的“文化寻根者”变成文化劣根性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这使人想起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传统。说到底,二者都是基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来写作中国历史中隐藏的文化结构,从现代的文化启蒙到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依旧,而中国历史在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人们知道,在当代中国,“文化”经常也是政治的代名词,文化反思不过是政治反思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实际上,被称之为“寻根派”的文化群体,其“寻根”的动机各异,效果也不尽相同,相当多的人,则是去寻找一种美学风格。那些“文化之根”其实转化为叙事风格和审美效果,一个文学讲述的历史神话结果变成文学本身的神话。一个关于文学创新的美学动机,被改造为重建历史的冲动之后,结果再回到文学本身。尽管这有点烦琐,也不无讽刺性,但是,它的文学意义总算没有完全迷失于虚幻的历史空间,因为文化的意义最终呈现为审美效果,它实际完成了一次文学观念和审美风格的变异。寻根文学还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学经验,并且群体效应并没有淹没个人化的风格。贾平凹刻画秦地文化的雄奇粗砺而显示出冷峻孤傲的气质;李杭育沉迷于放浪自在的吴越文化而具有天人品性;楚地文化的奇谲瑰丽与韩少功的浪漫锐利奇怪地混合;郑万隆乐于探寻鄂伦春人的原始人性,他那心灵的激情与自然蛮力相交而动人心魄;而扎西达娃这个搭上“寻根”末班车的异乡人,在西藏那隐秘的岁月里寻觅陌生的死魂灵,他的叙述如同一片神奇的异域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