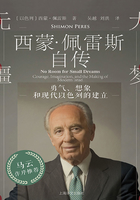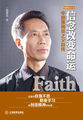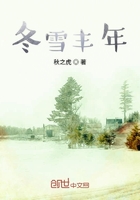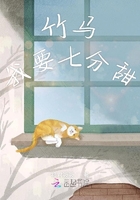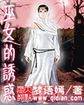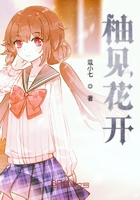张居正是一位功业卓绝的改革家,也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政治家。可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却受到清算,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为什么张居正的身后事如此的可悲?
国之后事与身之后事
张居正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而且重病缠身,精力也越来越不好。他已经到了需要处理身后之事的时候了。然而,作为首辅的他不仅需要处理身后之事,而且需要处理他去位后的国家之事。这样一来,年近六十的张居正只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鞠躬尽瘁了。
俗话说得好,人食五谷杂粮,岂会不生病?一般人尚且如此,何况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的张居正。
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时,张居正已经五十七岁了。那年的夏天天气极为闷热,加上首辅繁重的公务,终于使这个精力过人的老人倒在了病床上。
按理说来,这时的张居正完全可以功成身退了,然而或许是老天爷也舍不得这位治世的能臣吧,一方面年少的明神宗断不肯放他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大事也的确让张居正不能释然而去。
他只好拖着虚弱的病体,继续呆在首辅的位置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那么,又是怎样的一些国家大事让张居正放不下心呢?不是说,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大明朝已经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和富庶时期吗?难道张居正对这样的结果还不满意?的确如此。
大明朝经过张居正的励精图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兴盛。然而,这只是一些微小的改进。对于积弊已深的大明朝来说,要改革的事情还很多。并且,在一些方面得到改善的同时,另外一些棘手的问题又来了,比如外患问题的变化,比如内阁人选的增定等等。年将耳顺的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偶尔有退休的想法,也不可能真正释怀退去。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用病体与那些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国家大事搏斗到底了!于是,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全部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
大家应该还记得,张居正上台后进行的所有改革,都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个方针进行的。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这个方针既是张居正个人的抱负,也是大明朝在当时所必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只有国家富强才能给军队的强大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军队强大了,才能解决明朝政权最担心的问题一外患。可以说,明朝外患的严重史无前例,因为几乎在明朝疆域四周都有外族入侵。
外患问题严重地威胁着明朝的统治和安定发展,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他自己就生长在外患问题最严重的嘉靖年间。亲眼看见京城几次戒严,明朝军队却兵败如山倒,年轻的张居正心中就下了解决外患问题的决心。等到他上台,经过十年的努力,整个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原先领导鞑靼从北边进攻的俺答,已经向朝廷投降。在大体上,明朝的外患问题此时并不明显。
然而,这只是在大体上。在局部上,外患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其实,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俺答归顺了朝廷,明朝的边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肯定会有一些人不服气,或者基于利益的驱使,觊觎着明朝的财富和权力。很显然,张居正也是了解这些事实的,他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他采取的是两手抓的方针:一方面,对于已经归顺的俺答,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他采取的是“一味羁縻,但是决不曲从”的方针;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胆敢进犯和造反的外族,他决不留情。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俺答准备修筑城墙,派人向朝廷请求提供人力和物力帮助。
这个消息传来,朝廷上议论纷纷,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主张给予帮助,有的则主张拒绝给予帮助。最后,这些人都来向生病中的张居正请示。
张居正认为,鞑靼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逐水草而居,四处迁移,形成了极强的机动作战能力,可以随时采取进攻,根本没有被敌人围攻的危险。现在俺答准备筑城,我们完全可以答应他,因为他这样做是在自己包围自己,实属下策。
众人闻言,无不赞同首辅的英明。经过商议,张居正最后这样答复了俺答:“夫、车决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也就是说,朝廷只给予物力上的帮助,人力上的帮助就免了!
办完这件事后,病中的张居正在名为《答宣大巡抚》的一封信里高兴地说:“在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宣大巡抚》)
这个问题很容易便解决了,可是第二年的一个问题又让张居正大费了一番心思。这一年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春天的时候,俺答死了。
张居正听说这个消息后,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他的焦虑是有道理的:俺答的死是小事,北边的国防才是大事!这些问题是不得不引起思考的:俺答死后,西部鞑靼的领导权应该如何归属?最让人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俺答的死,使西部鞑靼全部投向辽东土蛮的领导,进而和朝廷作战?
稍好一点儿的情况似乎是,俺答死后西部鞑靼有可能分裂,分裂后的西部鞑靼势力就更小了,就完全没有了跟朝廷作对的力量。
然而,他们的分裂也许对朝廷并不有利,因为辽东土蛮也会乘机扩展势力,这就对朝廷有害了。
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苦苦地思索着。最终,他想到了俺答的后妻三娘子。大家或许还记得,当初正是由于这个女人,才使得把汉那吉投降,最后造成封贡的成功以及北边的安定。
换句话说,只要北边还有三娘子,即使俺答死了,还是能够维持安定。况且,要想三娘子帮忙,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当年她人关进贡时,时任宣大总督的吴兑曾经赠她八宝冠和百凤云衣,让三娘子非常开心。从那之后,三娘子就成了朝廷和鞑靼友好邦交的红人。
可是,完全依靠三娘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到底是谁上台接俺答的班。在这方面,张居正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也就是说,让这些有继承权的人先决个高下,等到局势明显了,再全力支持那个即位者。在俺答才死的时候,张居正命令沿边的督抚们对于各个候补者,分别都给予应得的帮助。不久,黄台吉即位的大局确定了下来。于是,张居正就向黄台吉表示支持其上台,但是同时要求黄台吉归顺朝廷,并告诉他说只有服从朝廷,才能得到“顺义王”的尊号。经过考虑,黄台吉最后答应了这个条件。
那么,三娘子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张居正认为,三娘子的作用仍然是做朝廷和鞑靼交流的红人,替朝廷控制住鞑靼。可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就需要三娘子再嫁给黄台吉。然而,就在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便带着自己的部众走了。气急败坏的黄台吉认为三娘子及其部众都是父亲的遗产,只有自己才有继承权,于是就带着部队追三娘子。就在这紧急关头,宣大的总督也意识到三娘子的重要作用,于是连忙派人和三娘子说:“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的恩赐当然络绎不绝,不然的话,你也只是塞上的一个鞑靼妇人,那就没有什么恩赏了。”三娘子听完这话,就停止了西去的脚步,重新回到了“顺义王”黄台吉的怀抱。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又解决了,明朝又赢得了宝贵的边疆安宁。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张居正不能完全放下心来离去。首先是辽东的问题。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三月,辽阳副总兵曹盙(音同“辅”)在长安堡打了一个败仗,死亡了三百多人。兵败的奏章上到朝廷以后,曹盙被关进了监狱,四月份将吴兑由兵部左侍郎改任了蓟辽总督。这次的兵败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在吴兑赴任后,写信给他说:
“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曹盙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重惩,勿事姑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蓟辽吴环洲》)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让病中的张居正牵挂的仍然是国家的边防。或许,所有的国家大事中,这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相对说来,内政方面,由于张居正从万历元年的努力,到万历九年时,已经没有什么太让人头疼的问题了。然而,那么大一个国家,就算没有什么大事,各种杂务也够让张居正烦心的。如果在张居正已经病倒的时候,还出现一些关系重大的政务,那就更让病重的他劳形损神了!或许是老天爷故意跟能人作对吧,这一时期,偏还出了一些棘手的政务。
第一件大事便是政府机构的官员选定。可以想见的是,张居正又病又老,肯定需要考虑安排政府中的各级官员人选。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官员没选好,政治就会出现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在内阁方面,从万历八年以后,便没有什么更动了,内阁大学士除了张居正以外,还是张四维和申时行两人。
政府的六部人选基本都是张居正亲手选拔的,现在仍然是那些人,只有礼部尚书潘晟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十二月结束任期辞官了,因此需要人来接任。经过考虑,张居正最终让刑部侍郎徐学谟继任了这个位置。
这个安排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按照明朝官员选任制度的惯例,要当上礼部尚书,必须曾经是翰林出身,可是徐学谟却偏偏不是翰林。于是,就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觉得不满。后来,靠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和威望,事态很快便平息了下去。这件事情,自然也花去了他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件大事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蠲除宿逋”。什么意思?就是说请求罢免以往的带征钱粮。按照当时的财税制度,如果一个纳税人上年还有没有交足的钱粮税,就连同今年的钱粮税一起征收。
本来,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开始实行考成法,国家的赋税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整顿。相应地,国家财政也有了很大的收入。到万历十年时,国家财政不说已经富足,至少也是入能补出了。因此,在张居正和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当时已经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可是,带征钱粮制度却大大阻碍了百姓们的休养生息。
关于这种制度的害处,张居正在万历十年二月的上疏《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中如此说道:
“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夫百姓财力有限,即一岁丰收,一年之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不幸遇荒歉之岁,父母冻饿,妻子流离,见年钱粮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完累岁之积逋哉!有司规避罪责,往往将见年所征,那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今岁之所减,即为明年之拖欠,见在之所欠,又是将来之带征。如此连年,诛求无已,杼轴空而民不堪命矣……”(《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指出了带征钱粮制度的危害。他先解释了带征钱粮制度在实际中的意思,就是“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这种制度是极不人道的,因为老百姓即使遇上丰收年,所收获的粮食也仅够交纳当年的钱粮。如果遇上灾年,当年的钱粮都凑不齐,家人饿死,哪里还有钱粮交纳上年的。这样的时候,征收钱粮的人为了完成任务,就将当年所收的钱粮虚报为包括了往年钱粮的,因此实际上减少了当年的收入。如此一来,一年接着一年的拖欠,就会越积越多,老百姓欠的钱粮也越来越多,只好疲于奔命。
如此看来,带征钱粮制度危害多多,必欲废止而后快!在分析了这种制度的害处之后,张居正还指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夫以当年之所入,完当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办纳,在有司易于催征,闾阎兔诛求之烦,贪吏省侵渔之弊,是官民两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盈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宇,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
张居正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一年就交该年的钱粮税,不再追缴过往年份的。这样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样也减少了征收机关的事务以及连带而来的吏治弊病。
第三件事情是平定浙江的兵变。这件事发生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二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浙江巡抚吴善言奉皇帝的诏书裁减了浙江东、西二营士兵的月饷。士兵们不服气,于是就闹了起来。由于领导没有及时控制局面,使得两个士兵,一个叫马文英,一个叫刘廷用,聚集了很多士兵,闯进巡抚大院,捉住吴善言痛打了一顿。
更严重的是,由于士兵的造反,使得当地的一些无业游民也趁机哄抢市民,形成了“民变”的局面,情势非常紧急。张居正听到消息后,立即将已经内调为兵部右侍郎的张佳胤,改调为浙江巡抚,并派其立即赴任,平定动乱。
张居正没有看走眼,张佳胤果然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还在到浙江去的路上,张佳胤就向逃难的人打听消息,当知道“变兵”和“变民”还没有联合起来时,他立即快马加鞭,迅速赶到了杭州,期望在“变兵”和“变民”联合前将他们分开。新任巡抚张佳胤到杭州后,看见“乱民”在城中放火抢劫,就对将军徐景星和东、西二营造反的士兵说:“你们不要害怕,虽然有前面的罪过,要想赎罪的话,就得先把‘乱民’平下来。”这些士兵们在痛打吴巡抚后,本来就怕得要死。这下好了,他们立即拿上武器,上街对付那些“变民”。
没有多久,就捉住了一百五十个造反的无业游民。张佳胤下令将这些人杀去三分之一,同时把马文英和刘廷用召来“领赏”。这两人高高兴兴地带来了另外七个造反头目,都是事变的首领。谁知,徐景星在席间埋伏了人手,把他们捉住就地处决。就这样,浙江的“民变”、“兵变”得到了镇压。
以上便是张居正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中,解决的一些主要的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倒是处理好了,张居正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了!
他的病到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九月的时候,突然变得很重。张居正只好上疏,既感谢皇上对他病情的关心,也请假休养。明神宗得到上疏以后,派了文书官太监孙斌前往探病,带去了很多慰问品,但他还是担心张居正会因病耽误政事,于是又下圣旨叮嘱:“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意思就是要张居正在家里办理公务。
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神宗不会轻易放开张居正,就算其病人膏肓,也要张居正为大明朝尽最后一份力。这样的情形从此时,一直到张居正死,反反复复出现了好几次。以至于每当张居正因为病重而请求辞去官位时,明神宗都会下旨慰留。
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张居正从生病一直到死,不止一次地上疏请求退休,其用意到底如何?是否就如其所说,只是由于自己年老体衰,已经不堪国家重任了呢?事实上并非如此。促使张居正想要早些辞去官职的主要原因是:自己权力太大,恐怕会功高震主、权重欺君。在张居正的《杂著》中,他如此写道:
“赵、盖、韩、杨之死,史以为汉宣寡恩,然四子实有取祸之道。盖坤道贵顺,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为人臣,止于敬也’。四臣者,论其行能,可为绝异,而皆刚傲无礼,好气凌上。使人主积不能堪,杀身之祸,实其自取。”(《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在张居正看来,汉宣帝手下的赵、盖、韩、杨四大臣就是因为不尊敬主上,没有礼法,甚至欺凌君主,使得主上难以忍受屈辱,因此才招致了杀身之祸。这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张居正的心理:虽然自己不像汉宣帝手下的赵、盖、韩、杨四大臣那样刚狠,但是这四人的权力也同样不及自己的权力大,汉宣帝对这四人的依赖也不及明神宗对自己的依赖。自己的威权的确太重了!
可以说,从万历八年起,张居正不断地提出退休请求,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他可不愿意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权力欲,而把自己的晚年给毁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生病的机会早日辞去官职,既打消了明神宗将来的嫉恨,也保全了自己。然而,张居正的主意打得不错,可是他岂能料到自己身后的事情。明神宗要整垮张居正,不会因为他主动让出权力就心慈手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另外一些人的报复,终于使得悲剧在张居正死后发生了!
尽管张居正为保全自己的晚年花了不少心思,然而老天爷却并不想让他在世间多留些时日。到了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二月,张居正再次病重。这次虽然查出了病根,原来他长了痔疮,必须割治,但是手术后的情况并不见好。张居正在写给徐阶的一封信中描写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贵府医官赵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日来渐次平复,今秋定为乞骸计矣。”(《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四》)
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本来!年纪那么大了,整日操劳国家大事,还动了手术,身体状况自然不好了。因此,他在这封信里,就说到了准备在那年的秋天再次请求辞去官职回家。到了万历十年的三月以后,张居正就只能完全待在家里了。可是,他还是没有闲着,该办的重要公务还是在家办理。这种精神实在让人觉得可敬!然而,这样一来,他的病情就越发严重了。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再次请假:
“缘臣宿患虽徐,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须再假二十余日,息静休摄,庶可望痊,盖文书官所亲见,非敢托故也。”(《张文忠公全集·恭谢赐问疏》)
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就算有再多的假日,整日养病,也是于事无补了!从血气亏损,到脾胃衰弱,张居正的病状日渐严重。到了四月,看着天气渐渐回暖,张居正又开始打起精神办公了。这时的内阁中其实还有张四维、申时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二人仍然不敢擅自作决定,一切都送到张居正的病榻前,让这位病人膏肓的老人裁决。
到了六月份,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结果如同以前一样,明神宗再次下旨慰留:
“朕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方计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览之,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宜安心静摄,痊可即出辅理,用慰朕怀。”(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希望张居正安心调养,不要想什么辞官的事情。并且,只要张居正身体一好,他就要出来辅佐。张居正想退休也退休不了,病情却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候。明神宗不是不知道这个隋况,只是或许他还在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可是,奇迹毕竟没有出现。到了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经病得昏昏沉沉了,神宗派了司礼太监带来手敕慰问居正:
“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神宗是在考虑张居正死后的政府官员人选了。昏沉之中,张居正上疏推荐了大量的人才:推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进内阁;推荐户部尚书张学颜、兵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等。对于张居正推荐的人才,神宗都予以了重用。这之后,张居正进人了完全昏迷的状态,没有再说过话!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最终丢下了他热爱的权力,死在了北京的寓所里。他留给后人的,除了那些改革成就以外,还有七十多岁的母亲、三十多年的伴侣和六个儿子、六个孙子。或许在他死的那刻,他会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牵挂的吧!神宗不是跟他说过要照顾他的子孙吗?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不能让他心满意足地去呢?
盖棺如何论定
张居正死了。他死的时候受到了极高的待遇。然而,这种待遇并没有维持多久就逐渐消失了。更让人觉得心寒的是,他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政敌的攻击、神宗的报复。一场关于如何给张居正盖棺论定的政治斗争,正在明王朝的最高层展开。
张居正的心满意足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他刚死的时候,他享受到的待遇可以说是顶级的。
首先是神宗下诏罢朝数日,两宫皇太后、神宗和潞王各赐银一千两,并派司礼太监张诚专门监护丧事。接着,按照传统,对于功勋卓越的大臣,死后都要给予谥号,并追封一些爵位。张居正则被赠予了“上柱国”,赐谥号“文忠”。而当他的灵枢出发的时候,太仆少卿于鲸和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则一路护送回到了江陵。张居正就这样带着平生的才学和成就,被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张居正得到了安葬,他的家人得到了朝廷的看护。然而,张居正并没有得到多久的安宁,他的家人也并没有享受多久由他带来的福荫。很快,无休止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就找上了张家门。
来看一下张居正悲惨的身后事吧!张居正死后的悲剧命运,是从他的政敌对他的亲信进行攻击开始的,以后逐渐变成了对张居正本人的攻击,最终酿成了张家的惨剧。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张居正去世前,曾经向神宗推荐潘晟进入内阁。这一方面是基于潘晟与张居正的友情,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基于潘晟当了多年礼部尚书,具有进入内阁的资力以及处理政务的能力。在张居正生前,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推荐人选提出质疑。可是,就在他死后不久,弹劾潘晟的奏疏便接二连三地来了。事情闹得很大,以至于本来已经从原籍浙江新昌出发来京赴任的潘晟,只得在路上就上疏辞去官职。
看着情势无法控制了,张四维只得拟旨允许了他的辞呈。事情并没有这样就结束,形势对张居正越来越不利。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经过御史李植的弹劾以及司礼太监张诚、张鲸的攻击,冯保倒台了。他的结局很惨,家被抄了,查获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跟冯保一起“下课”的还有梁梦龙、曾省吾和王篆,这些人大多与张居正结交深厚。
很快,事态就波及到了死去的张居正。首先遭殃的是他那些名垂千古、功业显赫的改革措施。为了减少驿道沿线老百姓负担的驿递改革,在已经取得很好成效的时候被取消了,官员们现在又可以任意乘驿了;为了监督行政绩效而制定的考成法,现在也已经对六部没有控制力了,它很快被取消;为了减少地方财政和百姓负担而实行的严禁滥广学额措施,现在也取消了,学额一并从宽……太多已经开始见效的改革措施,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消失得毫无影踪。制度上的废除,意味着明神宗对张居正的依赖和宠信已经荡然无存。
如果说上面这些变化对死去的张居正及其家人发生的都是间接的影响,那么到了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些残酷而又直接的影响就开始降临在了张居正一家人身上。万历十一年的三月,明神宗下诏夺去了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爵位,接着又下诏夺去了“文忠”的谥号。他的儿子跟着遭殃,已经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的张简修被贬为了平民。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张居正去世后九个月之内,如果张居正在天有灵,看到这些情况,一定会悲哀地体会到墙倒众人推的含义!想想他在世时,哪个人不会颂扬他的功业卓著?就在他病重的时候,北京各部院还替他建斋祈祷,这种形式很快还风靡了半个中国。可以说,那时举国都在为他祈祷。然而,张居正一死,风向就变了。实在让人觉得心寒!
对张居正的攻击并没有停止。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御史丁此吕检举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己卯科应天府乡试主考高启愚出的一道试题:“舜亦以命禹。”他认为高启愚图谋不轨:“舜就是当今皇上,禹就是张居正。舜将天命传与禹,岂不是叫明神宗奖掖张居正上进?”
这个攻击涉及的问题严重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是叛逆大罪呀!明神宗看到奏章后,虽然很气愤,但是却仍然拿不定主意,因此就向时任首辅申时行请教。
“丁此吕用暖昧不清的话诬陷别人有大罪,”申时行说,“我担心以后会有很多谗言,这不是清明的朝廷所应该有的现象啊。”
经过申时行的努力劝解,虽然最后的结果没有伤害到张家人,但是与之有关的官员就惨了:丁此吕、高启愚同时被免去了官职。其实,在这次的奏疏中,丁此吕还攻击了张敬修、张嗣修、张懋(音同“帽”)修三人应乡试、会试时的考官,认为这些考官为了巴结迎合张居正,故意给予张家人照顾。他还诬赖当时的礼部侍郎何雒(音同“洛”)文代替张嗣修和张懋修撰殿试策。对于这些诬陷,申时行向神宗解释道:“考官在考察时,只是根据考生的文学技艺水平的高低,并不知道姓名,不宜以此为罪。”最终,那些考官被免了罪,但是何雒文还是被解职了。
“失算”的身后悲凉
关于如何对死去的张居正盖棺论定的政治斗争,逐渐导向了不利于张居正的形势。进而,张居正的家人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家被抄。虽然有一些正义之士为张家人求情,然而明神宗却铁石心肠地下令抄家。一场悲剧发生了,这是张居正身前未曾料及的。
这一系列的风波到了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时达到了顶峰。
这一年,先是御史羊可立旧事重提,他向明神宗上疏追究张居正在十七年前曾经陷害辽王朱宪。这本来是一件已经盖棺定论的事情了,然而现在却被重新提起。可以想见,当时的政府官员正在抓紧明神宗对张居正失去宠信的机会,大肆展开报复行动。
就在羊可立上疏后不久,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也上疏了,在疏中她一面为辽王伸冤,一面还诬陷说:“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这里的庶人就是当年的辽王。
看到这句话,贪财的神宗终于等不急了,于万历十二年四月下诏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前去查抄的人有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橓,另外还有锦衣卫、给事中等人。
情势危急之下,一些比较正直,而且跟张居正关系很好的官员,不忍看见张居正家遭此横祸,纷纷上疏请求从轻发落。左都御史赵锦上疏说:
“世宗籍严嵩家,祸延江西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严氏,若加搜索,恐遗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其翼戴冲圣,夙夜勤劳,四外迭谧,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荫、赠谥、及诸子官职,并从领革,已足示惩,乞特哀矜,稍宽其罚。”(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这个上疏的意思是说,就算张居正再怎么腐败,也赶不上严嵩,况且他的专权已经得到了很严重的惩戒,没有必要再抄家了,因此请求从宽发落。
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
“居正为顾命辅臣,侍皇上十年,任劳任怨,一念狗马微忠,或亦有之。今……上千阴阳之气,下伤臣庶之心,职等身为大臣,受恩深重,惟愿皇上存天地之心,为尧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颂圣德,则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并行而不停矣。此非独职等之心,乃在朝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这个上疏则搬出了张居正以往的功劳,认为他以前还是比较任劳任怨的,因此劝神宗要学习尧舜的仁爱,恩威并施,实质是要神宗从轻发落。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已经动了杀机和贪心的神宗,全然不顾大臣们的劝解,仍旧我行我素,执意要查抄张家。看到向皇上求情已经无效时,申时行等人只好向前去查抄的刑部侍郎邱橓这些人请求手下留情:
“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终留神,以仰承圣德,俯慰人心。”(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意思是说,请求这些人手下留情,不要让张家人全部遭难,放掉那些无辜的人。
在这些请求信中,写得最感人的应该是左谕德于慎行的了,他如此写道:
“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郤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于慎行的意思明显是在褒扬张居正过去的功劳。他认为,张居正在当政时期,的确因为执法严明而得罪了不少人,但是当时没有一人不对他歌功颂德。现在他倒了,大家又群起而攻之。这些行为,实质上都有所偏离事实。张居正身虽死,但还有八十老母和涉世不深的几个儿子,如果抄家就肯定处境凄惨。因此,希望神宗能够“帷盖之仁”。
可是,不管这些求情的言辞有多么感人,邱橇和神宗仍然是不置可否,实际上也就是理都不理。此时的他们,抱持的就是一颗把张居正整得家破人亡的歹毒之心。哪里还会理这些正义之言!
不仅邱橇一干人,就是荆州府和江陵县的官员也闻风而动,在邱橓等还没有到江陵前,就亲自带人把张家给封了。张家被封,吓得张家人都不敢外出。等到五月初五邱橓到了,打开张家大门,就已经饿死十多个人了。
一阵拆屋揭瓦之后,就连张居正兄弟和儿子家的私藏都找了出来,一共才得到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
但是,贪心的查抄官们还不满意。他们重刑拷打张家人,要其招出寄存在外的二百万两白银。可是,这根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张家到哪里去找这些银两?无可奈何之下,查抄官就顺势将罪名栽在了曾省吾、王篆和傅作舟三家人身上。
要想知道当时的惨烈情形,看一下张敬修在临死前写的血书就明白了:
“……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
五月初十日写完此帖,以期必遂,而梦兆稍吉,因缓。十二日会审,逼勒扳诬,慑以非刑,颐指气使,听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这篇遗书描写了张家被抄之时的惨状。既表达了在那种紧急情况之下的惊恐和害怕,也表达了对抄家之人凶恶嘴脸的憎恨。
是啊!别说张家是知书达礼的书香门第,就是平常人家,见到这般如虎豹豺狼凶狠的查抄人,也只会是吓得半死!经过多次的拷问,张敬修忍受不了酷刑,自缢身亡;张懋修则自杀未遂。可怜张居正的两个儿子,竟然要因为父亲执掌的十六年大权,而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很快,张敬修的死讯传到了朝廷,百官哗然!看到张家的惨剧,痛心疾首的申时行联名六部大臣上疏明神宗,请求从宽发落张家人。刑部尚书潘季驯也上疏请求:
“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
在众官的苦苦哀求之下,心狠手辣的神宗这才发了一回善心,下诏留出空宅一间、田十顷,用来赡养张居正的母亲。张居正家的惨案,终于在张家家破人亡之后,草草了结!
在哀叹张居正悲惨的身后事之余,我们也需要弄清楚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
看张敬修的血书,让人不禁产生这样一种疑问:张家的惨案真的是张四维整出来的吗?张敬修如此写道: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这句话里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只不过,张敬修是文人,他的怨恨也显得很文人气!尽管如此,他怪罪张四维(张四维字凤盘)是确定的。那么,张敬修的这种怪罪对张四维公平吗?在我看来,这是不公平的。原因很简单:张四维早在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的四月就辞官了,即便是他对张居正把持政权有所积怨,到万历十二年时也已经没有报复的机会了。
与此相似,有人将张家的这次大祸归罪于高拱,同样是不恰当的。原因也很简单:高拱早在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就死了,那时的张居正还正是得势的时候呢!
那么,张居正凄惨的身后事,究竟应该归罪在谁的身上呢?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应该既怪他自己,也要怪明神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来解释缘何要归罪于明神宗。
按照明朝的刑法制度,能够被定为抄家之罪的只有下面三种情况:第一,谋反;第二,叛逆;第三,奸党。
如果依据这个规定,张居正的罪状是不足以被抄家的,因为他顶多就是收受贿赂。如果要说他谋反、叛逆和组织奸党,那是一点儿都没有沾边的。况且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势,如果他真有野心造反,明神宗早就当不稳皇帝了,还需要等到明神宗来除他吗?
这样说来,张居正被抄家,跟他所“犯”的罪行(姑且这样说吧)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又应该怎样来理解呢?我们只能说,这是明神宗的一意孤行!
前面已经说过,明神宗是个贪财的人。张居正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几次想要花费大量财政资金用于享乐,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劝止才没有得逞。张居正一死,他就开始大量动用国库钱财。用到不能支持时,就需要想办法筹钱了。恰巧,冯保家的被抄,使得他看到了出路。于是,当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告诉他张家“金宝万计”时,他就动了贪心和杀机。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为什么又说张居正被抄家有他自己的原因呢?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张居正为什么会在生病的时候,几次三番地提出要辞官?原因就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权力太大,权重欺主啊!
张居正虽然有权,但那只是皇帝给予的权力;自己的权力太重,皇帝就失去了君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别说明神宗还是一个有着几分傲气的皇帝,就是一个平庸的帝王也会受不了的。因此可以说,张居正虽然在当国十年里尽忠尽孝,对明神宗是忠心耿耿,但他同样也是明神宗的最大威胁。
也许是张居正的确在生前压得住明神宗,所以在他活着时,明神宗几乎对他是百依百顺。然而,也就是在这百依百顺的背后,开始出现了不满、怨恨甚至杀机。
终于,张居正死了,复仇的机会到了。于是,在一些本来就不满张居正官威的官员的陷害下,明神宗心中的那座天平倒向了这些人那边,张家的悲剧也就跟着发生了。这就是张家惨剧出现的第二方面的原因。
或许这便是人生的悲哀吧!没有权力,不能实现自己报国安邦的理想,会觉得生活得没有意义。可是,有了权力,而且是很大的权力后,却又陷入了另外一场悲剧之中!然而,不管怎样,张居正还是作了自己的选择,一个勇敢而又悲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