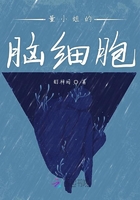这件事情起因于爱尔多拉朵酒店里的一次谈话,人们都喜欢吹嘘自己所宠爱的狗。因为过去的辉煌的历史,鲍克很快成了众人议论的话题,桑德不得不********。
他们不停地争论着,一个人说他的狗可以拉得动载重五百磅的雪橇。第二个吹说自己的狗可以拉动六百磅。第三个人说七百磅。
约翰·桑德说:“呸!鲍克拉得动一千磅。”吹说自己的狗可以拉动七百磅的家伙——马修斯,一位博内扎的金矿大王,追问:“能拉着走吗?能走一百码吗?”
约翰·桑德冷冷地说:“能!当然能拉着走!走一百码!”
马休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说:“好!我用一千块钱作赌,我认为他决不可能。”说着话,他向桌子上砰地扔出像意大利香肠大的一袋金沙。
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桑德虚张声势的大话——如果真的是这样——立刻可以见到分晓了。桑德感到一股热血冲到脸上。自己的舌头欺骗了自己。半吨!他简直不能相信,他相信鲍克的力气很大,曾经也认为过鲍克可以拉动如此之重的负担。但是,他不清楚鲍克能不能拉动一千磅,他从来没有让鲍克拉过这么重。
人们用眼睛紧紧盯着他,默默等待。
他也没有一千块钱。哈斯与彼得同样没有。
马休斯继续说:“我现在恰巧有辆雪橇车停在外面,装着五十磅一袋的面粉二十袋,你不用操心好了。”
桑德此刻失去了思维能力,从一张张面孔上无奈地望过去,到处寻找可以重新启动脑筋的东西。
他无话可说,所以没有回答。他从前的老伙伴——杰姆·奥勃爱恩——一个马斯特登金矿的金矿大王的脸色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脸上的那种神态,好像是在鼓舞他去做一件想都不敢想事。
他几乎是悄声问道:“你能借我一千块钱吗?”奥勃爱恩答道:“没问题,”说着,他将一个满满当当的口袋扔到马修斯口袋的旁边,“约翰,我在想,我认为这家伙干不了这件事。”
爱尔多拉朵酒店的桌子全空了,人们都走到街上看这场试验。赌钱的人纷纷下注,看它的结果如何。好几百人距离雪橇不远围成了一个圆圈。
马休斯那辆载着一千磅面粉的雪橇早在那里停了两个多小时。外面是零下六十度的严寒,滑板早就结实地冻在压得硬如石头的冰雪上面了。
人们以对折的彩头赌鲍克拉不动。而且,人们对“拉动”这句模棱两可的话的理解存在争议。奥勃爱恩让鲍克将雪橇从静止的状态拉起,主张桑德拥有除去冻住了滑板的冰块的权利。马休斯则坚持认为,“拉动”包括将滑板从冰雪冻结的状态下拉出来。耳闻目睹了这场赌博的人们多半支持马休斯。赌鲍克必输的放彩比例现在已达到了三比一。
然而,没人相信鲍克可以拉得动,因此,没有人接受挑战。
当时赌得特别草率,本来疑虑重重,看看雪橇前面,十只狗组成的队伍正蜷缩在雪地里。摆在眼前的事实,更加证明鲍克无论如何都办不到。
马休斯得意洋洋,宣布:“桑德,三比一,我按这个金额和你再赌一千块钱,怎么样?”
桑德脸上的疑虑明显可以看出来,然而,他那种超越胜负的斗志被激发了起来。除了喊杀声,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他相信鲍克能办到。他叫来哈斯与彼得。他们没有多少钱,连同他本人的,三个人凑够了二百元。他们手头正拮据,这是他们全部的资本。然而,他们意志坚定,孤注一掷,去赌马休斯的六百块。
人们解开了那十条狗,将鲍克连带挽具一起拴在了雪橇上。那种兴奋之情令他感动,他感到自己一定在用某种方式为约翰·桑德去完成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对他的仪表堂堂,人群中发出一阵啧啧的赞叹。他的状态现在很好。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多余的肉。有一百五十磅的体重,也就有一百五十磅的勇猛和力气。毛衣闪闪发光,顺脖子而下的大片鬃毛披满双肩,并且似乎随着他的一举一动一起一伏,每一根毛因为过于旺盛而有生命力,非常活跃。胸脯宽阔,前腿粗壮,看上去强健有力。皮下的筋腱结实非常,圆圆滚滚,摸上去可以感到坚硬如铁。
于是,赌注的比例降为二比一。
最近暴富的王朝的一个成员,一个坐头把交椅的贩狗大王,十分吃惊地说:“天呀!天呀!先生,先生,在考验他之前,我出八百块,八百块买他。”
桑德摇一摇头,走到鲍克身边。
马休斯抗议:“你不要靠近他。让他自己干。不能影响他。”
人群肃静下来。只有一些赌徒枉然接受对折彩头的声音。
人人都赞同鲍克确实非同一般,然而,二十袋面粉——每一袋有五十磅之重,实在太庞大了。他们不愿往外白白扔钱。
桑德在鲍克的身边跪了下来,然后捧住他的脑袋,脸偎着脸。他与往日不一样,既不开玩笑摇晃他,也不是小声地温柔而亲热地骂他,而是冲着他的耳朵轻声说:“鲍克,你是爱我的啊!你是爱我的啊!”
鲍克满腔热情,呜呜地叫。事情看上去很神秘,好像在施魔术一般。人们注视着,十分好奇。桑德站起身来,鲍克用牙齿咬住他的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慢慢地,非常勉强地松开了,这种回答用的字眼不是语言,而是爱情。
桑德后退几步,说:“鲍克,加油啊。”鲍克按照自己学到的方法,拉紧缰绳,然后又放松了几寸。
与四周充满紧张气氛的寂静比较,桑德的声音格外尖锐:“向右!”
鲍克向右斜冲,冲力绷紧了那根松弛的缰绳,一百五十磅重的身躯用尽全力猛地一拉,滑板下面拆裂的声音清脆响起。
雪橇颤动了。桑德十分沉稳地命令道:“向左!”
鲍克向左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方法,坼裂声成了咔喳声。
雪橇旋转了,滑板向旁边滑行了几寸。雪橇终于脱离了冰面。人们屏住呼吸,周围安静极了!桑德的命令再次响起:“走!”鲍克以一种猛烈的冲刺绷紧缰绳,由于用出了最大的力气,全身紧紧缩成一团。丝绸一样的皮毛下面的筋肉扭动着,集结在一起,凝聚出最强大的力量,头朝向下面,宽阔的胸脯低低地俯在地上,爪子疯狂地向前飞扒,雪地上显现出两条平行的深沟印在地面上。
此刻,颤动着向前移。他的一只脚滑,有人大声呻吟了一下。以后,雪橇不断地半寸…一寸……两寸……时而停顿时而向前,但并没有完全静止下来。显而易见,挫折渐渐减少,雪橇有了足够的运动量以后,震动减小了,雪橇平稳向前行进。
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曾经在刹那间停止过呼吸,在喘了一口气后,又开始呼吸了。
桑德跟在后面,用简短有力的话语激励鲍克。距离早已量出来了。
他靠近标志着一百码距离的终点的那堆木柴的时候,欢呼之声几乎是爆发出来。
他走过木柴,听到停止的命令。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吼声。大家——当然也包括马休斯,兴奋欲狂,帽子与手套在空中胡乱飞舞。人们胡乱握手,大家沸沸扬扬乱喊一气,也听不出说些什么。
桑德在鲍克身边跪下,来回推搡着他。匆忙围过来的人们听到他在骂鲍克,骂得温柔,亲热,热烈,长久。
此刻贩狗大王唾沫星子乱溅:“天啊!先生!天啊!先生!我出一千块钱买他!先生,先生,一千——一千二啊!先生!”
桑德站起身来,他早已泪流满面,泪水在脸上无所顾忌地流着,他向那个坐头把交椅的贩狗大王说:“先生,不行。我给你最好的回答就是,请你滚吧,先生。”
鲍克将桑德的手含在牙齿间。桑德推着他不断地前后摇晃。
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驱使着人们一起礼貌地后退一步,不再鲁莽地上前打扰了。
七、野性的回归
仅仅五分钟的时间,鲍克就为约翰·桑德挣了一千六百块。主人因此得以还清债务,还可以与伙伴前往东部,寻找一处地点不明的金矿。
金矿的历史和东部的历史一样悠久,许多的人都曾前往寻找。可能有极少的人发现了,但更多的人一去不复返。悲剧淹没了它,神秘的气氛笼罩着它。
没有人知道谁最先发现了金矿,就算是最古老的传说也说不清楚。奄奄一息的人们用一块块和北方已知的各种等级的金子完全不同的天然的金块证明,发誓说那里有一所小屋子,只要找到小屋,就找到了金矿。
然而,大部分人没能活着回来,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曾经找到这座宝藏。桑德、彼得和哈斯带着鲍克与其他六条狗,沿一条无名小路向东走,去完成许多和他同样能干的人与狗在那里没有实现的事情。
他们向育空河上游走了七十里,左转,入司徒尔特河流域,途经麻约、迈科奎恩,直到司徒尔特河逐渐变小变窄,穿过这片大陆的脊梁——一座座山峰高耸入云。
约翰·桑德所要求于人类或自然的东西极少。面对辽阔而又人迹罕至的荒原,他毫不畏惧。只要有一把盐,一支来福枪,他便可以深入蛮荒的原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和印第安人一样,他每天在旅途中打猎为食,悠然自得。如果没有打到猎物,他就继续走路,坚信肯定会遇到,因此,这次进入东部的长途旅行,雪橇上装满了各式工具和弹药,菜单自然只剩下单一的肉食,时间则没有尽头地延续下去。
这种打猎、捕鱼和自由自在地在奇特的异乡的环境中游逛,在鲍克这方面其乐无穷。他们会有时连续走好几周,一刻不停。有时则随地安营,停留好几个星期。人们用火在结冻的腐殖土和沙层上钻洞,淘洗数不清的盘盘泥沙,狗们就随心所欲地闲逛。他们根据打猎运气的好坏,时而忍饥挨饿,时而尽情吃喝。
夏天来了,他们将东西驮在背上,乘着筏子渡过群山上面一片片蔚蓝的湖泊,坐着在森林里锯下的大木头做成的小船,在不知名字的河流里漂流。
时光流逝,他们穿越茫茫无际的荒山野岭,曲曲折折地前进着。如果那座“地点不明的小屋”的确存在的话,肯定会有人来到过那个地方。然而,这里却渺无人烟。
冒着夏季的暴风雨,他们越过一座座分水岭。在森林边界线与长年积雪的荒山秃岭上,半夜里太阳依旧灿烂,他们却寒冷难耐。他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夏季山谷,那里蚊蝇成群结队。在冰河的隐蔽之处,可以看到只有在南方才会看到的鲜红的草莓和鲜花。
那一年的秋天,他们到了一片湖沼之地,凄凉寂静,让人胆颤心惊。野禽曾经在此地栖息,但当时没有任何生命,甚至连生命的痕迹都无从发现,只有呼啸而过的寒风,荫蔽之地冻结的冰雪,凄凉的水浪拍打寂寥的湖岸的惊涛之声。
整整一个冬季,他们跟着先人几乎泯灭了的踪迹到处流浪。一次,他们碰到一条古老的小路穿过森林,树皮上还刻有指示道路的痕迹,那座“地点不明的小屋”好像近在咫尺可及,然而,这条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小路,和开辟他的人以及为什么要开辟他的原因一样,是一个谜。
另一次,他们遇见一座,已经由于风雨剥蚀而倒塌的猎棚的残骸,约翰·桑德还在条条腐烂了的毯子片中找到一支长杆的燧石发火枪。这是“赫德森湾贸易公司”的产品,西北部早期的枪械,当时,这支枪的价值与平着摞得与它一样高的海獭皮相等。但是,仅仅发现这些,至于它的主人——那个以前修建这个棚子,将枪丢到毯子中的人的情况,则一无所知。
春天到了,他们的艰辛漂泊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并没有发现那座“地点不明的小屋”,却看到了一片宽阔的山谷中有一条浅浅的沙金冲积矿床。金子在淘金的盘底闪闪发光。到这里,他们不再往远处寻找了。
每工作一天,他们便能获得价值几千元的纯净的金沙和金块。他们不停地工作,金子五十磅一袋地装到麋鹿皮的袋子里,一袋袋堆在枞树枝搭成的小屋外面,他们辛勤劳动,跟巨人一样。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他们的财宝梦幻般堆得越来越高。
狗们除了随时拖回桑德的猎物以外,便没有其他的活可干。鲍克便卧在火边,用沉思默想来打发时间。现在,既然无事可做,那个短腿的毛人的幻象在他面前出现得也就越加频繁,鲍克眨着眼睛卧在火边,他们经常一起漫游鲍克回忆起来的那一个世界。
恐惧仿佛是这另一个世界中最显著的东西。那个毛人两手抱住脑袋,垂在膝间,睡在火边,鲍克观察着他,发现他并没有沉沉地睡去,常常惊醒,他向黑暗中窥探,多加一些木柴到火堆上。如果他们走在海边,毛人就一面吃东西一面采集贝壳,与此同时,保持高度警惕地四处张望,担心有没有潜伏着的危险,随时准备快速逃走。他跟在毛人的后面,在森林中悄无声息地潜行。
他们机智而且小心谨慎,因为人的听觉嗅觉与鲍克同样敏锐,他们扭动耳朵,张着鼻孔。那个毛人可以纵身上树,摆动胳膊便可以十分轻松地从这个树枝攀到另一个树枝上,这边一松手,那边早已牢牢抓住,虽然两个树枝有时相距十几尺远,从来不曾失手摔下来,而且如履平地。实际上,不管在地上还是树上,他都同样应对自如。鲍克想起自己曾经在树下守夜的情形,那时候,毛人栖在树上,紧抓住树枝睡觉。
与毛人的幻象紧密相联,呼唤之声在森林深处模模糊糊地响起,激发他心中的强烈不安的奇怪的欲望。他朦朦胧胧感到一种甜蜜的喜悦,对自己不见分晓的东西油然生起一种疯狂的渴慕与不安。
有时候,他把这种呼唤看成可以触摸的实体,去森林里追寻,轻声叫唤或叫着挑战。他将鼻子伸到冰冷的苔藓或满是很高的杂草的黑土里,嗅着肥沃的土地的气息从而感到心情舒畅,要么躲在倒在地上,生满了菌类的树干的后面,双眼圆睁,耳朵竖起,仔细倾听着周围的动静,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仿佛在埋伏着准备打仗一样。他这样卧着,可能是想要吓一吓那种他不理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