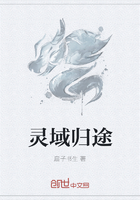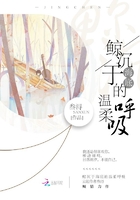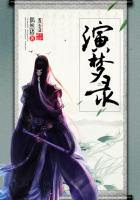口述 傅上伦 整理 韩斌
那是1980年6月初,新华总社国内部把陕西分社记者戴国强、甘肃分社记者胡国华和我(宁夏分社记者)电召至京,要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到陕甘宁去做一次系统深入的农村调查。
据可靠消息,中央将在9月份召开一个高层次会议,专门研究包产到户问题。因此,总社要求我们尽快行动,为党中央制定有关政策提供第一手的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如此重大的任务落到我们三人头上,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然农村经济政策已开始放宽,虽然1979年10月对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修改,“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被删去,但仍规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变为“也不要”,口气缓和了,但终究仍未开口。要最终突破“禁区”,肯定还要经历一番艰苦的过程。在此之前,我已就包产到户问题打过三桩惊动高层的“官司”,更深知突破“禁区”的艰难。
面对“禁区”,知难而进
那是1978年底,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兴建“绿色万里长城”——华北、东北、西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重大决策。为在舆论上配合、支持这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宏伟工程,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穆青同志要求国内部组织记者组到万里风沙线上作一次实地考察调查。多年从事林业报道的农村组编辑黄正根和我有幸担当了此项任务。
本来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调研活动,与包产到户并不相干。可是,1979年2月一着手调查,尖锐的矛盾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兴建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绿色长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当时,比较普遍的倾向是,希望国家拨出大量资金,兴办国有林场和集体林场。而我们在一路调查中却发现国有林场大部分办得不好,花了国家大量资金而少有效益。如果按照老路子、老办法去做,建设“绿色万里长城”很可能是纸上谈兵。
新办法在哪儿?在陕北榆林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苗头。这个县百分之六十的面积是沙漠,解放以来年年造林治沙不见林,连农民的烧柴问题也解决不了。
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县委解放思想,在我们到来之前刚刚作出一项决定:沙区社队可以划给每户社员五至十亩荒沙,植树种草,谁种谁有。
这项决定大得人心,我们也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便立即向总社发了一条《榆林县划给沙区社员荒地植树种草》的短新闻。总社播发之后,4月10日的《陕西日报》全文刊登了。
然而,见报的第二天,陕西省委办公厅就打电话给榆林地委,传达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榆林县到底有没有此事?如果有,要立即停止。
隔了两天,省委办公厅又一次打电话给榆林地委,传达省委领导的命令:“规定每户划五至十亩荒地的,要停下来。”
陕西省委为何坚决反对?我们分析,这与“张浩事件”有关。这年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张浩来信”,并且加了编者按,说农村不能从以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田不能分,山自然也不能分,陕西省委采取此态度也就不难理解。
当时我们正在西行途中,无法了解张浩来信的背景。但凭职业敏感,我们判断这不是《人民日报》编者的态度,一定有更大的来头。可是,面对事实,我们无法理解:让荒沙荒地闲着,是社会主义,分给社员栽上树,种上草,农林牧并举,反倒变成了资本主义,这不依旧在坚持“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那套谬论吗?
于是,我们以提问题的方式,发了一篇内参,题目是《“三北”地区能不能划给社员一些荒沙荒坡自造薪炭林?》稿子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据了解,‘三北’地区广大群众是盼望给他们划一些荒沙荒坡的,不少领导干部心里也认为这么做肯定是有益的,但是由于他们被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棍子打怕了,担心弄不好再戴上‘助长资本主义’的帽子,因此想搞也不敢搞。许多地方是一级级向上请示,又一级级推下来。他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件事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再作一些原则的规定,替下面的干部壮壮胆,撑撑腰。”
我们估计,此事可能会引起中央重视。结果也不出所料。胡耀邦同志在看到清样的当天,就批示给林业部负责同志:“此事我举双手赞成。在农业的问题上,我们已放开了手脚。在林业的一些问题上,也到了放开手脚的时候了。你们以为如何?”
可是,清样连同胡耀邦同志的批示传到林业部之后,一部分同志表示赞同,另一部分同志依然反对,并且要求同我和黄正根当面辩论。
经总社同意,我们回京,到了林业部。一些同志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向农民灌输爱社如家,爱护国家集体的一草一木,反而鼓动划自留山?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官僚式的责问,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回答,而只是举了林业部大院里的一个现象:公家的自行车都是破破旧旧,私人的自行车都擦得干干净净。我们由此发问:国家领导机关的干部尚且没有做到爱公物如家,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农民做到?对方默然无言,辩论也就不欢而散。
在陕西,问题也并没有因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而马上解决。直到当年10月底,《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批评陕西省委《对农民有好处的事为什么要下禁令》的文章后,才由省委农工部通知榆林地委:“省委最近重新研究,认为榆林县将一部分明沙划给社员植树造林的做法是正确的。”
第二桩“官司”直接触到了要害。那是1979年深秋,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陈大斌带领安徽分社采编主任张万舒和我,到安徽去调查包产到户。在合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对我们说:“包产到户好不好,你们要去问农民,他们最有发言权。”
于是,我们来到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一家一户登门拜访。然后又到凤阳其他社队调查,再扩大到淮北平原的几个主要县,接连跑了一个多月。
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使我们确信,包产到户是治穷良策,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篇题为《在生产关系调整中前进》的长篇通讯,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并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基本理论出发,对其必然性和重大意义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采访很顺利,发稿也很顺利,一送到总社马上就播发了。但是,北京没有一家报纸采用。不登的原因,大家心里都清楚。万里同志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说,北京不登,《安徽日报》全文登。
第三桩“官司”是1980年6月初,我赴京接受任务之前发生的。那年5月,我听说六盘山区固原县张易公社也推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户”,马上赶去调查,很快写出了一组三篇调查报告。报告在内参清样上登出后,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当时的农业部长霍士廉马上打电话到宁夏,要区党委积极支持(事后得知,这是胡耀邦批示要霍士廉转告的),但区党委不予置理。
寻觅真相,山高路险
以上三桩“官司”,事情不大震动大,解决起来都很困难。由此,在投入陕甘宁农村调查之前,我充分估计到此行不会平静。
当然,我们三人没有畏缩不前。虽然当时我们都是小记者,并不知道邓小平同志已于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包产到户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作了充分肯定,对凤阳县的大包干也作了充分肯定,但从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看,我们断定:情况已起变化,农村改革的禁区一定会突破。
新华社领导对这次调查极为重视,出发之前,穆青同志亲自找我们谈话,作了两点重要指示:一是这次调查既要以考察包产到户问题为主要任务,又要扩大视野,广泛了解陕甘宁地区各个方面的情况;二是要沉下去,到农村的最底层,直接倾听农民的心声,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不要道听途说,更不要人云亦云。
他特别强调,要说实话,写实情。他说,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为什么过了几十年,至今读来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为他们真实地记录了大量的事实。他们当时发的新闻,今天成了历史。你们这次调查,今天看是新闻,明天也就成了历史。你们一定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历史的责任感,不要有单纯的任务观点。要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写一路。
1980年6月中旬,我们从北京飞赴西安。6月23日,我们从西安出发到延安,开始了陕北调查。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先后到了富县、延安、安塞、子长、绥德、吴堡、佳县、米脂这八个县的十多个公社、二十多个大小队,并就黄土高原的生产方针问题和放宽政策问题,同延安、榆林两个地委和所到各县的县委进行了座谈,连续写成六篇陕北通讯,题目依次是:《陕北处在转折点上》、《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再这样大搞了》、《放宽政策就有粮食》、《退耕应该立即付诸实践》、《鲜活商品之流务需畅通》、《迫切的要求》。
陕北之行,十分艰苦。许多村庄不通公路,自行车也骑不成,全靠两条腿走,而时间又十分紧迫。我们只有尽量减少睡觉时间,拼命干。我清楚记得,子长县西部丛山中有个叫白季峁的生产队,离县城九十多里,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里发起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白季峁的农民听说北京的记者要专程到他们那里调查,连夜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来迎接我。第二天,我坐在一把竹椅上,由四个精壮小伙子抬着走,走到天黑才到白季峁。我心里明白,不是我本人有多珍贵,他们是盼望着中央给个好政策呀!因此,工作再苦,我们心头甜。
比较起来,政治风险的压力,更使人难受。六篇内参,几乎篇篇触及重大问题,有的还触及重大理论问题。譬如,在第五篇《鲜活商品之流务需畅通》中,我们就大胆写上了制定价格政策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这在当时,以至以后的十来年中,都是“禁区”,写上这样的话,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我们坚信一条:对中央一定要说真话。
稿子发出之后,触犯理论“禁区”的事无人责难,倒是第二篇通讯在内参清样上登出后,陕西省委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记者的观点(主要是指我们反对违背自然规律大搞“人造小平原”等)是错误的。胡耀邦同志看了报告,立即作了批示:记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请陕西省委再议。此事发生之时,我们已到六盘山下,当时并不知道,是回到总社之后才知道的,但事情已经了结,无需再费口舌了。
一线情报,火速递京
当年7月底,我们从陕北进入宁夏,在银川休整了几天,于8月1日抵达六盘山下的古城固原,开始了六盘山区调查。
六盘山的情况,我是相当熟悉的。我于1966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在校等待分配一年,于1967年底正式分配到新华社宁夏分社当记者。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年都往六盘山区跑几趟,每趟少则一月,多则两三月。1970年,我还在固原县黑城公社诸家湾子大队蹲点劳动过一年。最近一次上山是1980年5月,正在陕甘宁调查开始之前。因此,我估计这次调查会比较顺利。然而实际进展大出意料。就在我最熟悉、以为不会发生麻烦的地方,却又发生了一桩惊动中央的大事。
那是8月9日,听说固原县什字公社有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罢工”了,成熟了的麦子也不去割。我们立即赶去调查,才知原因是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但县里坚决不同意。县里不同意,是因为地委反对。地委反对,是因为自治区党委有明确而且强硬的指示。这么一级级压下来,农民还是不买账,他们干脆“罢工”,不干了。他们说,干了也是白干,不如不干。胆子大一点的队干部则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头搞了包产到户,说“我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先把肚子吃饱再说”。
山区的农民是最老实的,上级不让搞就不搞,即使是那些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也几乎都是瞒着上面偷偷干的。现在,六盘山区农民公开干了,为争得包产到户而“罢工”了,可见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眼看“火山”就要爆发,我们心急火燎,决定立即向总社报告。那个时候,山区通讯条件极其落后,我们赶回固原,在邮电局用手摇的老式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同志的电话。老杜听了我们的报告,马上说,这事情太重要了,不必慢吞吞写稿子了,你们口授,我叫杨克现(时任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来记录。一会儿,老杨来接电话,我便捏着电话筒,一句一句说,国强、国华在一旁帮着编成句子。约摸记了两页多,五百来个字,老杨就叫起来:就这些已足够说明问题,我马上编清样发出,详细情况你们随后写好再报。
稿子传出,我们在固原等了一天,得不到北京的指示,第三天一早就沿着西(安)兰(州)公路,越过六盘山,到了甘肃的平凉。一路上,我们看到往日冷清的公路上,站满了警察。看那情形,我们不断猜测:这是一级警卫,一定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要过此地。
我们的猜测没有错,是胡耀邦同志来到了六盘山。但我们没有想到,他就是看到我们口授、杨克现记录的那500多字内参而来的。看到清样的当天,他就决定亲赴六盘山,直接来做宁夏干部的思想工作。他还让中央办公厅通过总社寻找我们。可是,我们身处深山,哪里找得着呢!不过,我们也无遗憾,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一篇五百多字的报告能够引起中央如此重视,促成包产到户在宁夏全面推开,这是我们最大的快慰。
在六盘山调查期间,我们一共写了三篇通讯,题目依次是:《包产到户呼声急》、《实行包产到户的张易公社近况如何?》、《关键在于敢从实际出发》。
随后进行的甘肃调查,主要在平凉地区进行。我们从平凉沿泾河到泾川,再向西到崇信、华亭,翻过关山到庄浪、静宁。一路上,无论是受灾严重的地区,还是长期贫困的地区,都看不到昔日大灾后的那种凄苦景象,相反,倒是处处看见安定、兴旺、向上的景象。其原因,主要是地、县党委根据甘肃省委的指示,放宽了政策,充分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平凉调查着重于总结经验,我们写成了四篇通讯,题目依次是:《政策放宽,人心安定》、《从实际出发的果断措施》、《包产到户后集体的一些企事业怎么办?》、《活跃市场的必要措施》。
平凉调查结束之后,我们沿西(安)兰(州)公路到了兰州,此时,已是9月上旬了。杨克现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兰州,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又召集陕甘宁三个分社的采编主任到兰州聚会,交流了情况和经验。我们的陕甘宁调查到此告一段落。
在我们进行陕甘宁调查之际,我们的老朋友、新华社老资格的农村记者冯东书同志从另一条路线独自进行着内容大致相同的调查。他从北京到太原,然后一路向西,渡过黄河到陕北,在米脂与我们相遇。以后,他从陕北进入宁夏南部,经甘肃定西到了兰州。
1980年国庆前夕,我们两路人马四个人都回到了北京。这个时候,我们高兴地听到,中央果然在9月份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形成的中央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已经发下来了。文件中明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我们为“禁区”开始突破而兴高采烈,国内部农村组和内参组的同志也向我们祝贺:这里边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采访笔记,珍贵史料
本来,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可以回到各自所在的分社去了。但是,穆青同志在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说,已经发的内参只是你们一路调查到的大量材料中的一小部分。把那么多珍贵材料“烂”在你们的笔记本里,“烂”在你们的肚子里,太可惜了。你们要把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汇编出来,打印成书稿。这书稿,眼前可能出不了,但将来终究有一天会问世的。因为它是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档案馆中也难以找到的宝贵资料。
按照穆青同志的指示,我们先是各人清理自己的材料,提出要写的篇目,然后四个人一起讨论。题目确定之后,再分头写作。这样,到11月初,包含五十多篇文章,约十九万字的初稿出来了。这部书稿,大约印了二十来份,其中十来份送到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余下部分分送社、部有关领导,我们四人也各存一份。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曾商谈过出版事宜。但在当时形势之下,根本没有可能,此后我们四人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再加上各人都忙于自己的工作,那出版的念头也就渐渐淡薄了。更倒霉的是,由于几次调动工作,几次搬家,我保存的那份书稿也不知丢在哪里,再也找不到了。冯、戴、胡三人保存的书稿,据说也找不着了。这使我们万分痛惜。
1997年,杨克现同志偕夫人丁文来杭州旅游。我尽地主之谊,陪他们绕着西湖逛了一天,喝了地道的用龙井水泡的龙井茶,又到“楼外楼”吃了一顿地道的杭州菜。酒酣耳热之际,我们天南地北地闲聊,不觉又聊起那难忘的陕甘宁调查。我记得,当年的书稿打印本,也给老杨送过一本,便问他是否还保存着。老杨也记得有这么回事,他说回去一定认真找,如能找到,一定马上告诉我。
1998年1月8日,老杨来信说,书稿找到了,并推荐给人民出版社,列入了他们的出版计划。大半年之后,梦想成真,《告别饥饿》出版,当年写的新闻一如穆青同志所说变成了历史。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告别饥饿》又将再版。抚今追昔,怎不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