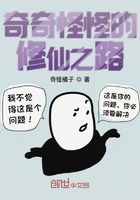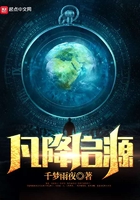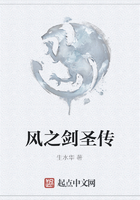建安作者多懷濟世之志,並形成一股相當鮮明的態勢,已為多家所論,但因其與本節直接相關,故不得不再予以申述。濟世之志可以從兩個方面表述,一是欲成功業之理想,一是對世亂時艱之關注及反映。強烈的功業理想是建安作者文中的一個顯著現象,其中之顯著者,如曹操的《對酒》,勾勒了一幅理想的社會圖景:“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白不負戴……”雖是對古代“大同”社會的一種嚮往與描述,但作為一個統治者,其中是蘊含了對自己政治藍圖的某種展望和期待的;如果這還衹是曹操的“展望”,那麽《短歌行》(周西伯昌)就是對自己欲效仿的人物直接進行描摹與比照,文中對周文王、齊桓公、晉文公的稱頌,明顯帶有“思齊”之意;《短歌行》(對酒當歌)表達了建業過程中渴求賢才的憂急心情,“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希望自己也像周公那樣,使“天下歸心”。曹操的理想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當時“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薤露行》,前揭《曹操集》,第3頁。),“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雄”,“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蒿里行》,前揭《曹操集》,第4頁。)。当时正是諸侯亂爭,“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讓縣自明本志令》,前揭《曹操集》,第42頁。)的亂世局面,這種情形下,曹操把“慨當以慷”之壯思與削平靖亂之志意並抒於懷就很自然了。但靖亂談何容易,創業本就多艱,故曹操詩中又充滿了悲壯蒼涼的意味,這在《苦寒行》(北上太行山)、《卻東西門行》(鴻雁出塞北)中表現得很鮮明,然而曹操詩的基調不是低靡,而是昂揚,“不戚年往,憂世不治”(《秋胡行》其二,前揭《曹操集》,第8頁。),“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步出夏門行》,前揭《曹操集》,第11頁。),文中充溢的是深摯的感人力量。
另外如曹植,其雖“生乎亂,長乎軍”,但他的經歷和感受並没有其父那麽深刻,故其反映社會殘破、苦難的作品不是很多,比較優秀的作品有《泰山梁甫行》及《送應氏》二首。曹植作品最突出的情感還是對功業理想的執著表達,他在《與楊德祖書》中說:“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在《求自試表》中自述:“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勳著于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白馬篇》:“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薤露行》:“願得展功勳,輸力於明君。”《雜詩》其五:“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雜詩》其六也表達說:“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欞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閒。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撫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除了這些直言的“慷慨”之音,其他如各帝王《贊》對帝王們功業的頌贊,《輔臣論》中對賢臣的要求,《請招降江東表》、《陳審舉表》、《諫伐遼東表》對時局、政事及以公族自固等重大方面頻頻發出的懇切的評議,無論是前期風光之時還是後期屢招打擊,濟世之志不改,反而愈為執著急切,這些雖有曹植身為宗族一員自身的責任,但其身上表現出的矢志不渝的濟世情懷自有其個體積極追求理想的因素在。建安其他表現作者濟世之志的作品,如曹丕《黎陽作》三首之一:“我獨何人,能不靖亂!”《令詩》:“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千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以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王粲《從軍詩》其四:“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其五:“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病。”陳琳《遊覽》其二:“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劉楨《贈從弟》其三:“於心有不厭,奮翅淩紫氛。”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無不洋溢着積極慷慨的意緒。
反映民生征戍等現實狀況的作品,如曹丕《泰山梁甫行》、《送應氏》,王粲《七哀》、《從軍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七哀》,應瑒《别詩》等,在感歎、悲思、憂心中表達世人對現實的關注,於低沉中透着責任。
當然,建安作者詩中絕不衹這一類主題和內容,但功業之思、憂時之想確實是建安詩歌中奏出的最鮮明、最有力度的調子,它構成了“建安風骨”最基本的底色。就這種思想本身而言,並不是什麽新鮮的創造,它無非是儒家立功濟世觀念的反映。在這個層面上,建安作者的思想與非“文士”的經學士大夫並没有多大的差别,並且在曹氏陣營中,真正在實際的濟世立功中起着骨幹作用的,反倒是後者而非建安作者(大略言之,不包括三曹)。吳質《答魏太子箋》中的一段話頗能透露個中事實:
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前揭《文選》卷四〇,第566頁。)。
當然,吳質的話要具体分析:一是建安諸子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確實在參與並發揮着相當大的作用,曹氏對他們與對待其他的僚屬一樣,並没有多大的差别,在某種程度上,曹氏對他們還親近一些,在以文人身份進行的來往中,曹氏與他們是“平等”的,諸子有較為獨立的人格與方式;二是諸子不以攻伐治守等實際功業行為為最擅也不值得詬病,所長有不同、所事有差異乃是自然之理,這與李白、杜甫汲汲于大道黎元但並不一定就有實際治世理政才能的情形是一致的。諸子所擅長的是他們的“文事”,他們的創造及貢獻正在於此,他們在文學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普遍地用文學來表現功業理想、濟世情懷,使文學也灌注了儒家積極與世的“經學精神”。正是在他們手裏,文學的地位與品性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徐幹《中論·藝紀》的一段話頗能透露個中信息:“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前揭《百子全書》,第274頁)“事”、“藝”一嚮居於被輕視的“下列”,從徐幹的敍述中,已經透露了“事”、“藝”地位發生改變的事實,純粹的“事”、“藝”從事者地位依然很低,但“君子兼之則貴”,也就是說“君子”從事之,其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徐幹描述的或當正是彼時社會“道”、“藝”從事者身份發生混淆、不再如先前截然而分的社會存在事實。“文學”此前一嚮居於“事”、“藝”的行列,但“文學”在漢末同其他嚮被輕視的“事”、“藝”一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而且在眾多的“事”、“藝”之中,“文事”改觀還是最突出者之一,所以徐幹所論,未始不包含着文學等發生轉變的認識與事實。),這是後世文學得以順利、獨立發展的前提,而這一前提條件是由建安作者來創造完成的。
這裏需要涉及兩個和經學精神有關的傳統“文事”現象:一是漢賦的諷頌功能,一是“詩言志”傳統。
按理講,漢賦的“奏雅”及諷頌功能最與經義有關,為何不言其也灌注了“經學精神”呢?漢賦這一現象的實質有些不同。諷頌是文化傳統、尤其是經學強加給漢賦的一種功能,賦在認真履行這一職責的同時也就戴上了“附庸”的枷鎖,這一功能並不作為漢賦自身的質素存在。經學的作用,不是使漢賦這一樣式因沾溉了經學的影響而品格有所改變,反而在經義的約束及比照下,漢賦突出了其作為“技”存在的實際面貌(許結在《漢代文學思想史·緒論》中曾概括說:“漢賦以描繪性文體特徵對自然、現實的摹寫、再現,以及對環境事物淋漓盡致的刻畫,強化了一種文學技藝美;但在賦體文學創建之際,這種技藝美是出於政治的需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頁)指出了漢賦確有“技”之存在層面的事實。),它離後世“文學”不但不以符合經義為存在目的而且經義反而成為“文學”精神及內容的一部分、是為表現文學精神而存在的这个要求距離還太遠。賦要在與經學的交往和聯繫中獲得自身獨立的發展品性,還有相當长的一段路要走。
關於傳統文化中的“詩言志”,其說雖一直從古用到今,但它的內涵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其中,有實質意義的改變發生在魏晉,“詩言志”轉換成了“詩緣情”。但理論的提出往往要在實踐有了一定的發展之後。“詩緣情”理論之前的實踐,建安創作是一個關鍵。先秦與漢儒時期的“詩言志”,“詩”大體指《詩》或《詩》中之“詩”,而不是個體造作之詩;“志”大體指《詩》中所蘊含或表現的儒家禮儀與規範,是符合儒家之旨的群體的、社會的道德觀念,而非個體的情志表達。所以先秦兩漢時期的“詩言志”不但不指作詩以言己志,反而成為高懸於個體詩歌創作頭上的一種禁忌,我们虽不能遽言其阻礙了詩歌創作的發展,但其與後世“文學自覺”時期的“詩言志”有極大的差别確是事實,因此先秦兩漢之時,既缺乏造作之詩,以詩來表達一己之志的情況就更是少見。在東漢末年倒是出現了一些“迪志”、“述志”、“見志”詩,但其時文人創作面貌既顯單一,文人們作詩“言志”也不構成非常鮮明的時代創作風貌,詩歌創作尚處在起步之中,當然也就難以形成詩歌品性發生質變的局面。
這一局面的改觀是在建安作者的手裏完成的。建安作者通過作詩來言志,促使傳統“詩言志”發生了兩點重大改變:一是“詩”已非指《詩》或《詩》中之“詩”,而是指由建安作者普遍參與、大量造作的“個體”之詩;二是建安作者所言之志就包含了上文所反映的功業之思、憂時之念,雖也是儒家關心民瘼、積極與世精神的體現,但建安作者把這種精神援引入詩,以“文學”的方式進行表達,使這種精神變成了“文學”內在的質素。也就是说,此“志”雖關乎經義,但卻不是為了闡釋經義,而是作為創作者個體情感的內容而存在的。關於第一點,建安時期的詩歌創作,無論是詩歌總量、個人平均量還是創作局面、詩歌體式及所反映的內容,與漢代詩歌相比,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從兩个時期的詩歌情況一覽表及相關分析中可以直觀看出。關於第二點,需略為之說。前已有言,文士在曹氏陣營中取得了略可與傳統經學士大夫等同的地位,由於他們本身也都不乏儒家文化背景,故在一同參與曹魏文化政策建構的過程中,他們的文學觀念融入某些儒家的精神內涵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這看似自然的舉動卻對“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文學”藉以提升了自身的“品性”,已不是“小技”的模樣、“厥品甚卑”的地位,而成為可以表達作者觀念與理想的獨立的文化樣式。承載着作者理想及認識的文學著述本身就有了價值,是“不朽”的方式和途徑之一。建安作者中一個較為普遍的認識便是創作已成為與孔氏之業“相提並論”的著述行為,曹氏兄弟的見解具有代表性,至於說把作品直接上攀《雅》、《頌》的意識,在建安作品中更是多有。“文學”在曹魏時期的變化除了緣於外部強力的超拔,與外部作用相應,其內部質素也同時在發生着重大的改變,而這正是建安作者堂皇地把“文學”比於“經藝”的內在依據。
“文學”內部發生的這種變化,從傳統中藉助的文化理據就是“詩言志”。“志”在傳統文化中有其特殊的規定性,表達的是合乎儒旨的群體性社會意願,故傳統文化中的“志”一直就被賦予嚴正、高級的意味。建安作者開創的“詩言志”局面依然自覺地延承、遵守了這樣的內在規定,他們詩作中的“志”依然保留着鮮明的“經學精神”,憂時念世、欲建功勳的積極情懷是他們所言之“志”的主旨。但這一“志”又不同於傳統之“志”。傳統“詩言志”之“志”是先儒認識理念的一種積累,後人解“言志”,基本是對先儒認識及規定的一種抽繹和解說,須“述而不作”,言說者一己之“志”是被排斥的。建安作者之“志”並不藉助别人的規定來透露,而是把自己的理想、志意直接付諸語言形象進行表達,個體情志的表達在詩中得到恢復和突出。當然,這種個體的“情志”又不僅是“小我”的一己窮通,其中灌注了關注現實、積極入世的“經學精神”,這樣“文學”與“經學精神”就深相接納起來。
傳統文學常常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每當文學出現言之有物、言之有意的健康發展局面,其內在精神往往就表現為高度關注社會現實、積極參與社會的精神品性;如果文學出現華靡、柔弱、流蕩的風貌,那麽批評者予以糾正的參照或手段,往往就是向“風騷”傳統回歸。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它構成了傳統文學流變的基本表現形態,之所以如此,原因多元,機制複雜,但其基本的發生前提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文”之地位的提高及“經”、“文”發生某種程度的交融。這樣的事實正是在曹魏時期出現的,“建安文學”邁出了實踐的第一步。可以說,“建安文學”改造了傳統的“詩言志”內涵,並通過自身的實踐對其中之“志”確定了大致的內在規定性,也正是如此,“建安文學”成為一種典型的範式而為後世批評者所推崇。
當然,建安作者在創作實踐中所言之“志”衹是個體情懷之一義,以個體之“情”的面貌出現,以個體不能不發之“情”的方式表達,是以個體的真情實感為依託的,“情真意切”是建安作品表現出的鮮明特徵。建安作者誠摯、自然地表達個體情感風氣的形成,應與現實的生活需求有關。《文心雕龍·詔策》篇曰:“魏武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章表》曰:“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章表,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現實應用之需要求文風簡明直接,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曹魏文章“簡約嚴明”(《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前揭《魯迅全集》第三冊,第502頁。)的情況。這種風習與曹氏大力提舉下層文藝樣式也有莫大關係,下層文藝樣式往往真摯質樸、直接自然,曹氏大量擬作樂府詩,從中接受良好的影響是很自然的事情。上述兩個原因在促動作品表達不虛隱、不依違的“直接性”上有它們特殊的功績,但個體的“情感”因素在建安作品中大量出現並成為顯著的代表性特徵卻不僅僅由於上述兩方面因素,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即漢魏之際個體精神之自覺(余英時認為“所謂個體自覺者,即自覺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不與其他個體相同,並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所在,以期為人所認識之義也。”(《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前揭《士與中國文化》,第310頁)之後作者從個體外在之表現、內心之意趣等方面對“個體自覺”的表現予以論述,可參看。)。個體精神自覺之顯要一端,就是對自己理想、情懷的確認與高度重視,抒發、表現于文即為作品中言志述懷的內容。“文”為文人表達情懷的最重要的途徑與工具,故值個體自覺發展蔚為鼎盛的漢魏之際,文人“自覺”之精神自然在“文”中有更為顯著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