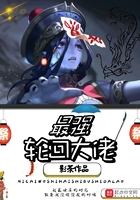对朱子来说,颜回与曾点的共性在于:二人都有极高的天资,都能见得大本。与子路相比,二人都见得细。但二人的差异更是明显,也更为朱子所强调:颜子之乐实,曾点之乐虚;颜子之乐真(自然、平淡、恬静),曾点之乐劳攘、外露;颜子前途未可限量,曾点很可能流于佛老。由此,朱子既肯定和推崇二人的见处之同,但更强调颜的乐更为自然,更为真实;同时,他也注意区别颜曾在工夫之有无上的相异处,强调二者的虚实之分:
问颜子乐处,曰:颜子之乐,亦如曾点之乐,但孔子只说颜子是恁地乐,曾点却说许多乐底事来,点之乐浅近而易见,颜子之乐深微而难知,点只是见得如此,颜子是工夫倒(到)那里了,从本源上看方得(林赐录)。《朱子语类》,卷三十一。
颜子之乐平淡,曾点之乐已劳壤了,至邵康节云“真乐攻心不奈何”,乐得大段颠蹶。或曰:颜子之乐,只是心有这道理便乐否?曰:不须如此说,且就实处做工夫(林学蒙录)。同上。
朱子显然认为,颜回更近于儒学的理想人格。不过,朱子有时还会在不经意间把二人相提并论,如《论语或问》云:
程子答鲜于侁之问,其意何也?曰:程子盖曰,颜子之心,无少私欲,天理浑然,是以日用动静之间从容自得,而无适不乐,不待以道为可乐然后乐也。
以此内容和朱子在《答万人杰》书所引的《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相比,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四、曾点与漆雕开
上文已經提到,朱子曾反复提到曾点与漆雕开的优劣,这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不下十多处:
问:漆雕开与曾点孰优劣。曰:旧看皆云曾点高,今看来,却是开着实,点颇动荡(郑可学录)。《朱子语类》,卷二十八,《论语十·公冶长上》。
如漆雕开见大意则不如点,然却是他肯去做(曾祖道录)。同上,卷四十。
若论见处雕未必如点透彻,论做处,点又不如开着实(李儒用录)。同上,卷二十八。
朱子认为,论见地,曾点无疑要优于漆雕开;而论做工夫处,则“颇重工夫”的漆雕开更为着实。表面上看,二人各有所长,似乎点还略高于开。但是从虚实之辨的角度来看,则开实而点虚,因此开更能获得朱子的青睐。为了突出与曾点之乐的区别,朱子特别用“灰头土面”来形容漆雕开:
漆雕开想是灰头土面朴实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虽见大意,也学未到(潘时举录)。《朱子语类》,卷二十八。
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子认为漆雕开较之曾点更能有进步的潜力:
开是着实做事,已知得此理,点见识较高,但却着实处不如开。开却进未已,点恐不能进(董铢录)。同上。
事实上,越是在晚年,朱子就越重视做工夫处,也就越希望弟子们能以漆雕开为师,不要去空头的羡慕“曾点气象”。这也是朱子越来越强调虚实之辨一个具体体现吧。朱子的这一精神,对于限制理学发展的过分玄虚化,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与上述几人相比,曾点的长处在其见处,其不足在其做工夫处。于朱子,曾点有许多东西需要向这几个人学习。
五、曾点与庄子、邵雍
在朱子眼中,曾点和庄子及邵康节也有很多的共性——天资高,却缺少儒家法则的约束而失之于狂,只是曾点不及二人更放荡罢了。
在《朱子语类》中,邵康节经常被引为曾点的同调,而二人之间的相似性,通常被指为一味追求快活,对乐的追求超出了儒学基本价值观的约束。如邵康节的《和君实端明》诗曰:
养道自安恬,霜毛一任添。且无官责咎,幸免世猜嫌。蓬户能安分,黎羹固不厌。一般偏好处,曝背向前檐。劭雍:《击壤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邵康节视“官责”为人生的一种负累,认为注重安乐自由的精神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了无滞碍的生活。我们固然可以在程明道甚至朱子的诗文中偶尔发现类似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并不是他们思想的主流。反观康节,他的所有作品中都缺少对儒学基本价值观的肯认,而一味宣扬这种情绪。毋宁说,安乐已经成了他所追求的最高原则,这种态度明显与理学的基本价值观不类。对于康节之乐,朱子说:
看他(邵雍)诗,篇篇只管说乐,次第乐得来厌了。圣人得底如吃饭相似,只饱而已。他却如吃酒。《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朱子显然以为,邵康节滔滔不绝地咏叹生命的快乐感觉,乐得太过分了,乐的太张扬了,乐得有些以玩物为道,会有淡忘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流于佛老的危险相对而言,朱子认为康节较之庄子还算是有规矩。庄子则完全“无礼无本”。我们也能在朱子晚年对曾点的批判中看到类似的话语,而这同他对时人一味渲染曾点之乐的忧虑是相关的。朱子的这种态度,也能让我们想起叶水心对邵康节的批评。
在《朱子语类》中,朱子也经常对曾点和庄子进行比较:他认为二人的共性是狂,是超然于礼法绳墨之上和“不犯手”。
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辅广录)。
要之他(庄子)病我虽理会得,只是不做(郭友仁录)。
庄子见处亦髙,只不合将来玩弄了(潘时举录)。
庄子之鼓盆而歌,曾点之倚门而歌,在朱子眼中已不仅是失之狂,而且是失之怪了,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对此的批判也格外严厉。不过,朱子也时时对庄子的见处赞叹有加,并称其能见“尧舜气象”:
因言庄子,不知他何所传授,却自见得道体(钱木之录)。《朱子语类》,卷十六,《大学三》。
他大纲如庄子。明道亦称庄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庄生形容道体尽有好处(叶贺孙录)。
(曾点)其见到处直是有尧舜气象。如庄子亦见得尧舜分晓(徐寓录)。
而对于“尧舜气象”,朱子则明确释之为:
或问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说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见得尧舜气象出(徐寓录)。
此“尧舜气象”即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天理流行气象。至于为什么庄子能见到此气象却还那样非礼无法,朱子的回答必定是庄子有体却无用,较之曾点更为过分,这是由于庄子的所见更为“空疏”。
于朱子,邵康节和庄子都不是学者所应效法的榜样。他更不希望人们所推崇的“曾点气象”,会变成“康节气象”和“庄老气象”。
六、曾点与谢良佐
本文已经反复指出,谢良佐之推尊曾点,也是谢本人气象的反映。这种气象曾长期令朱子着迷,而后来朱子对谢思想的清算过程,大大促进了其“曾点气象论”的成熟。事实上,朱子对二者的批判常常搅在一起,难以分开。概言之,朱子认为二人的共性是妄为高论,颠倒为学之序,不屑卑近,忽视下学。在朱子的逻辑中,这也和佛老仅隔一线,尽管其较之邵康节和庄子来说还略强一点。
朱子之于谢良佐,同样是爱恨有加:一方面,朱子对谢的禅味始终心存警觉,《语类》和《文集》中也反复在强调这一点:
问:谢氏解颜渊季路侍章,《或问》谓其“以有志为至道之病”,因其所论浴沂御风,何思何虑之属,每每如此,窃谓谢氏论学,每有不屑卑近之意,其圣门狂简之谓欤?《集注》云: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曰:上蔡有此等病不是小,分明是释老意思(吴必大录)。《朱子语类》,卷二十九,《论语十一·公冶长下》。
朱子当然并不认为谢无工夫,但却认为其脱略下学工夫的嫌疑,近似于有体无用的佛老。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对谢之“曾点说”能落脚在人的心性上,以及谢以“曾点气象”来形容道体流行,抱有相当的好感:
此(“曾点言志”)一段,唯上蔡见得分晓。盖三子只就事上见得此道理。曾点是去自己心性上见得那本原头道理(辅广录)。
上蔡说鸢飞鱼跃,因云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看来此一段好,当入在《集注》中舞雩后(沈录)。
朱子很注意一分为二地对待谢上蔡和他的“曾点说”:既贬抑其的立言过高和过玄的成分,同时又赞扬突出其反映道体、天理流行的内容。
七、曾点——朱子心中的圣人气象
朱子对前贤气象或人格理想进行了反复的辨析,对于诸多前贤更是颇有微辞。那么在朱子心中,理想的人格气象又是什么样子呢?朱子的回答必定是圣人气象。《文集》、《语类》包括《或问》、《近思录》等书中,都收录了朱子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同时,钱穆先生也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这里只是结合本文的主题略做讨论。通过对朱子之圣人气象看法的考量,我们能对他的“曾点气象论”有更为准确的理解。
在宋明理学中,朱子的气象论可谓别开生面。上文已有提及,儒家之论圣贤、之希圣希贤的情节,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其间每个人对圣人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大概在唐宋之前,人们心中的圣人是“生知”的代表,其重心在德才兼备,无所不通,甚至是博施济众,一般人是难以企及的。随着儒学转向内在,人们对圣人的理解开始落在道德纯粹上,其代表就是阳明的重成色不重分量的说法。儒学的这一转变也使得圣人不再远离世人,不再以神的面目示人。与此相应,儒学的成圣成德之路也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和容易,渐修与顿悟的问题也开始进入了儒学的论域。陈来先生就指出:古典儒学与道家中都没有顿与渐问题出现,顿悟与渐修一类问题在儒学内出现,肯定与佛教讨论的影响有关。其实,在儒学内部出现顿与渐的问题,其对圣贤之学的理解由智识主义向德性主义的转变,未必不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此,余英时先生有精彩的论述。但是在此转变下,儒学的圣人理想也有变得干枯的危险。
不过,只要儒学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堕,那么她就不可能在对圣人的理解上完全把智识因素排除在外。而朱子气象论的根本点,就是强调以理而非心来统摄气象,并强调理的天地自然意,强调圣贤气象不能限于自了,不能陷于个人超越。这大大突出了圣人智识的一面,使圣人的形象变得更为丰满。
具体到本文,虽然大程子宣扬“曾点气象……便是尧舜气象”。但在朱子看来,“曾点气象”乃至颜子之乐,与圣人气象天悬地隔,不可同日而语。在朱子的所有文字中,他从来没有把孔子与曾点相提并论之处,也没有把孔子与颜、孟、曾参、漆雕开相提并论的意思,可谓明证。即使是在与人讨论大程子的那一段话时,他也一再强调大程子仅仅是就“与圣人之志同”这一点上说的,并没有真正把曾点等同于尧舜。于朱子,圣人气象应该纯而又纯,无懈可击。反之,无论是颜回、曾参,还是孟子、曾点、漆雕开等人,都是贤人之属,都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缺陷。
那么,朱子心中的圣人气象又如何?钱穆先生论之甚详。概言之,朱子认为圣人气象即“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以及由此而发而中节,时时事事都能做到恰当好的气象:
圣人只是做到极至处,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谓之圣(沈录)。《朱子语类》,卷五十八,《孟子八·万章上》。
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常人终日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圣人要求备,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寿昌录)?《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
显然,朱子决不会认为,端茶童子在一时一事上能做到动容周旋,便是圣人。他眼中的圣人不但要规模宏大,而且要兼德性与事功为一,兼眼界胸襟与工夫为一,兼极高明与道中庸为一,是裁成辅相天地之化育者——继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外极规模之大,内推至于事事物物处,莫不尽其工夫”同上,卷十七,《大学四·或问上》。一句话,圣人要集“成色”与“分量”为一体。
朱子强调,“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同上,卷三十六,《论语十八·子罕篇上》。不多能又怎么能做到博施济众?不如此至多只是一个困居家中的善人而已,充其量只是一堂堂之人而已陆王也不否定此一立场,只是他们极大地压缩了人们学习外部知识的空间而已。可见,朱子认为做圣人千难万难,并不容易。朱子云:
有德而有才方见于用,如有德而无才,则不能为用,亦何足为君子(吕焘录)?《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
圣人何事不理会?但是与人自不同(曾祖道录)。同上,卷十五,《大学二·经下》。
有德无才,尚不足为君子,更遑论圣人,原因其是无用——朱子固然大力反对功利之学,却仍以为用来期许圣人,不知颜习斋对此做何感想;但若反过来说,“今若只去学多能,则只是一个杂骨董底人”《朱子语类》,卷十五,《大学·经下》。也不会得到朱子的赞赏——有才无德,被朱子视为是管商之徒,无忌惮之属,乃至是汉唐文字之儒。在这一点上,朱子反复强调儒学以成德为中心,强调“君子不器”。余英时先生早已准确地指出,“朱熹同时与两种不同的倾向作斗争——没有智识基础的简约之论和没有道德核心的博学”。在对圣人的定位上,朱子同样也是如此。这一特点,也是我们把握朱子精神的关键点。
但是,如果说圣人与凡人同样都是在理会事,他们的区别又何在?朱子的回答是圣人的理会事,服从于他的为己之学这一大本。
当然,朱子也不希望说高了、说虚了圣人,不希望在圣人和凡人之间划上一道鸿沟:
圣人之道有髙远处,有平实处(杨道夫录)。《朱子语类》,卷八,《学二·总论为学之方》。
学者是学圣人而未至者,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只是一个自然,一个勉强尔。惟自然,故久而不变,惟勉强,故有时而放失(李壮祖录)。同上,卷二十一,《论语三·学而篇中》。
只有个生熟,圣贤是已熟底学者,学者是未熟底圣贤(叶贺孙录)。同上,卷三十二,《论语十四·雍也篇三》。
于朱子,圣凡出于一本,只是圣人已经由勉强而达到了自然、自由、自在之境,已经能事事做得恰当好而已。因此朱子又注意告诫弟子们不要以为圣人遥不可及,而是要时时以成圣为志。
八、曾点与朱子气象
就本文而论,朱子与“曾点气象”的特殊渊源已如上述,而其对“曾点气象”之爱之恨,之褒之贬,都无不是其个人气象之流露。将朱子气象与“曾点气象”相对照,更能使我们把握朱子为学的精神。
我们说,朱子思想的核心是理,而朱子同样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以理为矩)”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此理想又集中反映在《格物补传》和《中庸章句》中。概言之,此理想是由即物穷理,下学上达而能够“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四书五经》本。进而在应物时从心所欲,发必中节之气象,也是复天命之本然,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气象。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德性与知识的紧张远较其他理学思想家为轻。原因在于:朱子对理的理解更多强调的是其规范意,其对善的理解不是指其直心而发,天然流露,而是强调其发动需要有以节之,使之无过无不及——因为过犹不及,爱而流于溺便会成为私的源头。如果说在孔子那里,是礼对人的仁心发动起到了限定的作用,使之发而中节;而在朱子那里,节制人心发动的最终依据是天理。这个理虽然随处发现,无少欠缺,本无所偏。但是就人而言,人对理的禀受却各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