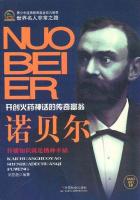重庆是战时陪都,又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在周恩来领导下,翦伯赞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呼吁爱国,宣传抗战,批判右派思想,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还写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一、二卷。这套书观点鲜明、资料丰富,而且图文并茂,便于读者阅读。在当时国共对峙的情况下,这本书反响很大。在重庆的6年中,翦伯赞也对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发起创办重庆大学教授联谊会,还到复旦大学、朝阳大学、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处演讲,受到陶行知先生格外关照。翦伯赞在《我和行知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他对于青年,对于朋友的诚恳和帮助,却是世所稀有。只就他对我而说,在抗战的几年中,他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健康,关心我的著作,真是无微不至。我有几次贫血病与心脏病发作,都是因为他的帮助才好转的。甚至对于我吸烟的嗜好都没有忘记。他自己不吸烟,但外国友人送给他香烟,他一定接受,哪怕是一支两支都替我留着,托人带给我。”一片深情,尽在其中。
在这里,翦伯赞还结识了冯玉祥将军,并给冯将军讲授了几个月的中国历史,两人遂结下深厚友情。翦伯赞素有烟瘾,而且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冯将军不吸烟,也反对别人吸烟,但每次讲课中,翦伯赞习惯地摸出香烟后,冯将军总是立即起身,替翦先生找火柴。一次,一位将军送给冯玉祥几包缴获的香烟,冯将军欣然接受并高兴地转赠给翦先生。后来,据那位副官说,冯将军送烟给朋友,这还是第一次。两人友情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翦伯赞于1946年5月来到上海,与张志让、谷城等人组织并领导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编《大学》月刊,并兼任大夏大学教授。当时上海政局形势异常严峻,蒋介石正在加紧部署反革命活动,迫害、暗杀进步青年、爱国人士,翦伯赞也在黑名单上。为了保护翦伯赞,中共中央密令翦伯赞尽快转移。这年10月,翦伯赞乘船去香港,再次开始避难生活。刚到香港,他便被达德学院聘为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历史”,同时兼任香港《文汇报》“史地”副刊主编。这些副刊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宣传阵地,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8年11月,翦伯赞与郭沫若等人离开香港,次年到达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征途上,翦伯赞又开始了新的辉煌。
建国初,翦伯赞担任了一系列职务,先是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接着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翦伯赞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同时还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大学报》和《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主编等职。他在不同的岗位上终日忙碌着,并以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从50年代开始,翦伯赞致力于史学建设。他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2000多万字的宏篇巨制的出版,留给史学界一个奇迹。紧接着,他在担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的同时,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并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为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北大任职期间,翦伯赞团结教师、倡导良好的史学风气。北大历史系是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历史系合并而成,门户之见很深。翦伯赞巧妙地团结三校教师,通力合作,消除偏见,给教学、科研带来很大方便,也为北大树立良好新风。
正是由于翦伯赞的特立人格和出色工作,以及他在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他受到大家的尊敬。毛泽东主席也多次接见翦老。1957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翦伯赞。毛泽东问翦老:“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翦老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泽东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于是翦老回到北大,对北大文科教学和科研极为重视。
有一次,毛泽东与翦老在游泳池上相见。翦老问道:“主席,您说中国周秦以来就进入封建社会,周,是西周还是东周?”
“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讨论嘛!”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受我的意见约束。我的意见也是一家之言嘛。”
翦伯赞也极为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曾多次访问少数民族地区。1956年夏,他以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身份访问了回族和维吾尔族的聚居地。1961年7月,应乌兰夫邀请,翦老率团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内蒙,工厂、学校、牧地、林场,随处可见他的身影;座谈会、报告会,处处可听到他的高论。边疆的辽阔壮美、民风的淳朴真挚,让他激动,给他诗情。他曾在百忙中吟诗:
浓云低压雨ⅲ塞外人家毡作蓬。
此是今生未曾见,草原万顷牧歌中。
锡泥河畔论英雄,万马秋风汗血红。
一代天骄今已矣,红旗插遍辽西东。兴奋的翦老一口气写下20多首充满深情的赞歌,倾注了他对祖国、对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
正当翦老为祖国建设奔走出力的时候,一场历史的悲剧却悄然上演了。
1963年夏天,以关锋为首的一群人开始“批翦”,先是在会上作报告,接着发表文章,声势越来越大。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呼声中,“批翦”逐渐升级,并普及到全国各种史学刊物和报纸,由学术批判上升为政治批判。面对这些,年近七旬的翦老并未妥协退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翦伯赞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的大帽子。不久公开、大张旗鼓的“批翦”运动达到高潮。从此,年迈的翦老遭受严重的折磨和迫害,身心受到重创。1968年12月18日夜,不屈不挠的翦老与妻子一起,双双含冤弃世。
翦伯赞的去世让毛主席、周总理极为震惊,马上指示此事性质严重,要严肃处理。对涉及此事的中央专案组、“翦伯赞专案组”成员以及北京市委、北大相关单位负责人都给予相应处分。但由于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翦老的冤情却没有得到平反。
1978年9月1日,在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北大党委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为翦伯赞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名誉。
【作者点评】
夜深人静,再读翦伯赞传,还是被他的经历、人格感动了。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翦老一生都在学术生涯、研究论著里寻觅着人生的价值,使他在学术上初放蓓蕾的是那本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从此,在漫漫书海中,翦老写下大量的论文、专著,为我国的史学建设做出不朽的贡献。
王安石诗云:“丹青难写是精神。”对翦老而言,他的骨气、高节却是罄竹难书。血雨腥风的年代,翦老辗转海内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的紧要关头,他深入虎穴,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为新中国的建立洒下一片赤诚。在建国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拉着翦先生的手,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介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这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和最大荣誉。
在漫天狂潮的“文革”岁月,翦老坚守着追求,执着于信念,始终保持心灵的一叶扁舟,把忠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
“立志不随俗流走,著说敢与世人争”,这就是翦伯赞。他用笔写下历史,用言行展示人格。其峥峥风骨,令人肃然起敬。虽然翦老含恨弃世,留给我们无尽的哀思,可他的风范长存,精神宛在,在厚重而古旧的丹青上,不是已留下他的不朽遗迹了吗?
(李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