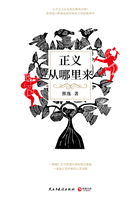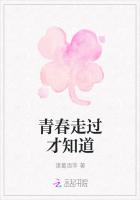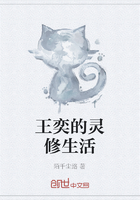自从中唐韩愈、柳宗元发动古文运动以来,古文,即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成了“文”与“文学”的正宗和文坛的正统旗帜。经过宋、元、明三代,到清代桐城派手中,古文因在内容上囿于“文以载道”,在形式上陈陈相因,早已从全盛走向衰微,以至气息奄奄,成了抱残守缺、尊古蔑今的文字工具。势穷必变。沉寂了漫长岁月的骈文,作为对前者的惩罚,到清代中叶,骤然中兴起来。一大批汉学家,不仅擅长骈文,而且公开树起旗帜,同宗法宋学的桐城派古文家争夺文学的正统地位。萧统在《昭明文选序》中给“文”下过一个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为文。”清代许多汉学家都利用这一定义来与古文家抗衡。阮元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说:“《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言说》,挟孔子《文言》而为骈文张目,说:“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名,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同上书,《文言说》。这就是明白宣称,只有既用韵又尚偶俪的骈文方才配称“文”,方才代表了“文”的正统。章太炎为“文”与“文学”所下的定义,就是针对以上这两种流行的论调而做的。
章太炎在《论文学》中写道:
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或谓文章当作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凡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彰为主。
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对这一段话又作了许多补充。直接针对阮元的《文言说》,章太炎写道:“今欲改文章为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
这里,章太炎以有文字著于竹帛为“文”,以文字著于竹帛的法式为“文学”,给“文”与“文学”下了一个界限最为宽广的定义。按照这一定义,信奉“文以载道”的古文辞固然可称之为文,信奉“以翰藻为归”的骈文也可称之为文。而“文”又不仅仅限于这二者,更不是仅局限于其中的一个。这一定义,显示了“文学复古”将在何等广大的领域内进行。
章太炎强调“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同上书,71页。,首先是为了反对将“文”引向专门崇尚形式而忽略现实内容的歧途。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说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阮元借用文与笔的这种分别,极力抬高专务华辞偶俪的骈文,而贬低朴简写实的散体。章太炎直率地指出,专以用韵、用偶等来限定“文”完全不科学。他指出,魏、晋以前,并不存在什么“文”、“笔”分别,那时,“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并非如后人那样“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晋代以后,文与笔渐渐有所区别,但当时许多著名作者都文、笔并重,并没有以为笔非文而摈之于文苑之外。他认为,由于所要反映的实际不同,骈体、散体,或文、笔,都有必要各适其所需而得到运用与发展。“盖人有陪贰,物有匹偶,爱恶相攻,刚柔相易,人情不能无然,故辞语应以为俪;诸事有综会,待条牒然后明者……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礼经》、《春秋经》、《九章算术》者,虽欲为俪无由。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各任其事。”很明显,章太炎并没有对骈体简单地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只要内容需要,运用骈俪就是完全应当的。在这一点上,他同古文家的立场就大相径庭。事实上,当他坚持应当把作品的内容放在第一位、形式必须服从内容时,他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了古文家。在作为《文学总略》姊妹篇的《论式》中,他就指名道姓地批判了韩愈、苏轼等人,说:“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权德舆、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于气矜,游豮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为错牾。古之人无有也。”同上书,《论式》,122页。这恰好证明,他关于“文”及“文学”的定义,与骈文家、古文家这两大传统流派都截然不同。
章太炎提出“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彰为准”,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探索几乎所有文章的“法式”,实际上也就提出了全部文风、文体如何改革的问题。早在《文学说例》中,他就已对这一问题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然而,言语并不等于外界事物,一旦表现为文字,则必然会与外界事物产生更大的距离。他引用姊崎正治的《宗教病理学》“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则必不得不有所表象”、“人间思想,必不能腾跃于表象之外,有表象主义,即有病质”等论点作证,说明“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他指出:“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斯非独魏、晋以后然也,虽上自周、孔,下逮嬴、刘,其病已不訾矣。”正因为如此,对中国整个传统的文辞便都有进行变革的必要。为了克服“文益离质”的毛病,章太炎提出,一要“断雕为朴”,二要勇于“解剖”。他指出,“中夏言词,盖有两极而乏中央,多支别而少概括”,“所以为名词、形容词者,亦甚纯简”,这对于缜密而准确地反映实际非常不利。所谓勇于“解剖”,就是要求能够更为细致、更为深入地揭示客观实际的本来面目。为此,他大声疾呼,要敢于打破自诩为“天然之完具”的旧文辞,而锻造出“真完具”的新文辞。他写道:“金之出矿必杂砂,玉之在璞必衔石,练钘攻锻,必更数周,而后为黄流之勺,终葵之圭。夫如是,则完具之名器,非先以破碎,弗能就也。破碎而后完具,斯真完具尔。任天产之完具,而以破碎为戒,则必以杂沙之金、衔石之玉为钜宝也。”
章太炎追溯文的起源,将文分作“有句读文”和“无句读文”两大类。“无句读文”包括图画、表谱、簿录、算草四种;“有句读文”又分“有韵文”与“无韵文”,“有韵文”包括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六种;“无韵文”包括学说(诸子、疏证、平议)、历史(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国别史、地志、姓氏书等)、公牍(诏诰、奏议、文移、批判、告示、契约等)、典章(书志、官礼、律例、公法、仪注)、杂文(符命、论说、对策、杂记、述序、书札)、小说六种。章太炎认为,“文学复古”所涉及的范围,应当包括所有这些方面;至于它们究竟应当如何变革,则应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提出具体的要求。
章太炎首先说明,“有句读文”与“无句读文”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纯得文称”,主要表现了“文字之不共性”;而前者“兼得辞称”,主要表现了“文字、语言之共性”。他说:“文字初兴,本以代言为职,而其功用有胜于言者。盖言语之用仅可成线,喻如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之委之仪象。仪象之用,可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 这里所说的“言语”,指口语。章太炎的这一段话,具体分析了形诸文字与原先的口语“共性”、“不共性”究竟何在。他指出:“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正是以这一分析作依据,章太炎分别给各种“有句读文”及“无句读文”提出了变革的标准。
关于“有句读文”,章太炎指出:“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术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然而,“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作史者即“不能为表谱书志”,中唐以后,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学说科的“疏证”之学也日渐粗疏,以至文辞“日趋浮伪”同上书,53~54页。。怎样改变这一状况呢?章太炎提出,对于书、志说来,“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繁碎”,它的要领当在于“训辞翔雅”;对于疏证说来,“必不容与表谱簿录同其冗杂”,它的要领则在于“条列分明”。他并提出:“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他以为,在“有句读文”中,除去“有韵文”情况有所不同外,这一准则应当为所有各科共同遵循。“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牍,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牍,此所以骫骳不安也。”在这里,他便将“质实”、“直截”、“训辞翔雅”、“条列分明”的写实主义,确定为“有句读文”中全部“无韵文”所应追求的共同目标。
至于“有韵文”,章太炎认为情况不同,应当按照另外的标准加以要求。他说,“论辩之辞,综持名理,久而愈出,不专以情文贵”,韵语则不然,“由其发扬意气,故感慨之士擅焉”。正因为两者有这样的区别,诗歌便应当以抒发情性为重。“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则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纵观韵语发展的整个历史,可以发现,当“其民自贵,感物以形于声,余怒未渫,虽文儒弱妇,皆能自致”时,当诗人“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时,当诗赋能够“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故温雅以广文,兴谕以尽意”时,诗歌便能兴盛,卓然有成,否则,即必然颓败惰弛。比如,中唐以后,“近体昌狂,篇句填委,凌杂史传,不本情性”,诗赋便由是不竞;到了清代,“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致使“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更是明证。韵文除去以抒发情性为灵魂外,表现形式又自有特征。章太炎认为,韵文所重,不在直叙,而是比兴,这就是所谓“韵文贵在形容”。诗体由四言而五言、七言,代有变更,反映了不同时代声律调度的差别。这一更迭是势所必至,“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据此,章太炎便将“本情性,限辞语”确定为发展诗歌创作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并断言:“要之,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从形式上看,诗歌创作所要求的似乎不是写实主义。从实质上看,其实并不例外。本情性,是反映和发抒真实的志向与感情,它同样“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而必须坚持“修辞立诚其首”同上书,《文学总略》,75页。,所以,这仍然要努力贯彻写实主义。
于此可见,章太炎所倡导的“文学复古”,中心就是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旧习气,反对雕琢、浮华、颓败、陈腐的旧文风,而要求树立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新风尚,树立立诚、质朴、抒情、新鲜的新文风。他不仅要求狭义的文学领域必须这么做,而且要求哲学、历史、公牍、典章等也必须这么做,以便在各个文化领域进行一场全面的变革。
经过对历代诗文的权衡比较,章太炎以为,魏晋古文及五言古诗最能适应“文学复古”的需要。他不仅大力鼓吹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
以文而论,章太炎认为,汉代之文与唐、宋之文都不足为法,只有魏、晋之文,最值得作为楷模。他说:“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之文,长处在哪里呢?章太炎写道:“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尤其是在注意到“名理之言,近世最短”这一情况时,能够“甄辨性道,极论空有”的魏、晋之文便更值得师法。也正因为如此,师法魏、晋之文,便必须以雄厚的学力为基础:“依放典礼,辩其然非,非涉猎书记所能也;循实责虚,本隐之显,非徒窜句游心于有无同异之间也。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预之以学。”
就实践而言,章太炎本人论政、述学、叙史的文字,确实处处表现了魏、晋风骨,处处突出显示了他雄劲的学力。他曾自述:“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非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魏、晋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秦、汉之高文典册,至玄理则不能言,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之文。……由此数事,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
在诗歌创作方面,章太炎主张:“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杜、李之徒,稍稍删节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他所宗法的,是魏、晋古诗。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实际地体现了他的这一主张。他自述:“余作诗独为五言。五言者,挚仲治文章流别,本谓俳谐倡乐所施。然四言自《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余亦专写性情,略本钟嵘之论,不能为时俗所为也。”这一段话表明,章太炎是如何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同他的诗歌理论统一起来。
就狭义的文学创作而言,诗歌代表了章太炎的主要文学创作活动。章太炎留下的诗作数量不多,但确实如他所说,他是在备尝险阻艰难的过程中,“既壹郁无与语,时假声韵以寄悲愤”而写出这些诗歌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诗作,“采之夜诵,抑可以见世盛衰”。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韵文作品总共不过数十篇(首)。以五言为主,也有少量四言、七言。除去古体诗,他还写了一批赞、颂、赋、铭、哀辞、祭文。
就内容言,这些韵文大体分作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