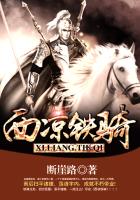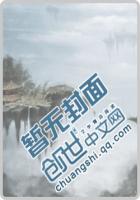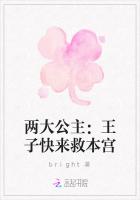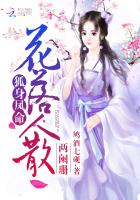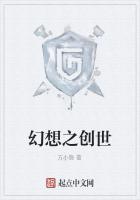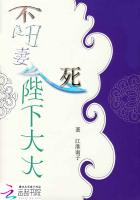以上这两篇文章 ,只是众多的有关世界史、全球史和其它史学流派结合的论著中的两个例子。但窥一斑可以见全豹 ,这两个例子指出了三个有意思的现象,为我们预测史学发展的前景 ,提供了一些线索。第一是全球史本身的巨大潜力和活力。如果史家都能挑出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现象 ,那就能创造不少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这两位作者的观察 ,显然还是设想多于实证。这其实不是一个缺点 ,而正是全球史潜力的展现 ,因为有关的研究 ,还刚刚起步,将会吸引更多的学者 ,以促进其成熟。第二 ,虽然自 1970年代以来 ,史学的总体趋向是逐步碎片化 ,但全球化的高歌猛进 ,又促使不少史家对之做出反应。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 ,当今的史学家 ,已经出现了一种整合的意图。第三 ,当今的全球史研究 ,其实与以前的宏观历史或世界史的研究 ,有很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史家不是一定要对总体历史的趋向 ,做出笼统的概括和规律性的预测 (当然这些概括和预测有其必要性 ),而是可以就一些在某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出现的现象 ,做扩文化、跨地区的比较研究 ,以获取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总而言之 ,如同本特利所强调的那样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起云涌 ,对史家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对全球化的过程 ,做一个历史的探究和解释。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用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区的角度 ,重新研究、写作历史。这两个要求 ,对当今史家来看 ,都是重要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一定的意义上看 ,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未来方向。
附录一 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兼论其外国史学史研究的洞见卓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 ,以所谓 “自下而上的历史学 ”(history from below)为主流。这一思潮最早始自西方史学界 ,延续、深化已有几十年 ,至今方兴未艾 ,并逐渐影响了世界其它地区。其主要表现,便是史家将其眼光从精英文化移向大众文化 ,从中心转向边缘 ,从国家转到社会。其影响所及 ,造成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等领域 ,不再为人青睐。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少数族裔史等逐渐成为显学。这一思潮在西方学界的形成 ,有其复杂的原因。就欧洲而言 ,连续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 ,动摇了西方文明的根基 ,使得许多人对其思想传统失去了信心 ,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而在二战之后领导西方学界的美国 ,由于其本身历史不长 ,原来借助欧洲的思想文化为其立国根基。一旦这一思想传统在欧洲受到怀疑 ,美国学界由此便轻装上阵 ,很快接受并推广了 “自下而上 ”的研究视角。其历史研究工作者更是驾轻就熟 ,从追随欧洲的思想传统转而注重自身的草根文化、民主生活 ,由此而成为国际史坛社会史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所占有的话语霸权 ,这一 “自下而上 ”研究历史的潮流 ,也开始为中国史学界所接受。近年中文学界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大有朝气蓬勃、日新月异之势。这一潮流本身 ,并没有大错 ,甚至十分必要 ,因为像 “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这样的说法 ,虽然已经流行许多年,但在九十年代以前 ,真正从事类似于印度的 “下层研究 ”(Subaltern studies)、对中国的民俗文化、世俗阶层认真钻研的学者 (五十、六十年代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或许是个例外 ,但可惜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为数并不多。可是 ,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推广社会史、文化史的同时 ,是否一定要想西方史家那样 ,排斥其它带有注重精英倾向的学问 (如思想史、政治史等 ),则似乎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与欧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比 ,中国的情形有许多不同。首先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笔者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记忆 ,向来与一些文化的精英有关 ,如孔子、老子、司马迁、司马光、李白、杜甫、蒲松龄、罗贯中等。如果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 ,抽去这些名字 ,那么这一历史记忆一定会变得十分苍白 ”。更重要的是 ,我在上面所举的这些人 ,在他们生活的当时 ,几乎都还没有处于文化精英的位置 ,因此 “精英”与 “草根 ”,本来就是历史变化的产物。如果我们在当前为了推广社会、文化史而故意无视这些人物的重要 ,而特意去发掘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所谓 “小人物 ”,那就未免有东施效颦之嫌了。其次 ,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 ,已经对自身的文化传统 ,进行了许多批判性反思。但面对西方至今仍然保持的学术霸权,中国人是否需要继续以其为准绳而无视、忽略或低估自身文化遗产的价值,则更有必要让人深思。
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就建国以来所开展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 ,如果我们无视张芝联先生 (1918—2008)的贡献 ,那么这段史学史的历史不但会显得苍白 ,甚至无从写起了。更重要的是 ,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法国史和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张先生从不主张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史学潮流。相反 ,在他的论著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中 ,他一直坚持保持自己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这一立场 ,意味着中国学者在接触、引进西方学术的时候 ,必须基于中国学术的传承 ,符合中国学界的实际需要。张先生 1986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到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 ,外国的经验有许多启发、示范作用。但他同时强调说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并不照搬一个既有的模式或者按照一个现成的菜谱做菜 ”。他在这里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形 ,但也可视为是一种夫子自道。张先生在 1991年为高毅《法兰西风格》一书写的序言中也称赞说 ,“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 ”。概括张先生的观点就是 ,史家必须与时俱进 ,不应囫囵吞枣、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照抄 ,因为学术思潮的形成 ,通常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文化背景则个个不同 ,无法等同复制、生搬硬套。
由此看来 ,如何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一个人要找一本西方流行的著作加以翻译 ,或者挑一个新潮的外国学术流派 ,加以引进介绍 ,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如何正确解读、解释该书或该学派的产生及其影响 ,则必须不但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而且还必须对它们所处的时代 ,有正确的了解。中国的古训 “知人论世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张先生的高人之处,正是在于他不但外文娴熟 ,特别是英文和法文 ,説写都十分流利 ,在中国史学界首屈一指 ,而且他还对欧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 ,有丰富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他在中国史学界德高望重 ,但他从不倚老卖老 ,对新的思潮和流派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相反 ,他十分注意了解新事物、新思想 (虽不一定赞同 ),而且不耻下问 ,活到老、学到老 ,真正做到了学问面前人人平等。张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沟通中外史学学术交流之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诚非偶然。
张先生之所以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他的作风为人、交友之道、充沛精力和上面所提到的精湛的外文水平 ,都有密切的关系。有关张先生的生平 ,虽然他没有留下完整的自传 ,但他在不同的场合 ,多有阐述。其中特别一提的是 ,虽然我们对张先生的一般印象是 ,因为他曾负笈欧美,所以学通中西。其实这一印象有点误差 ,因为细究张先生的治学经历 ,其实他在国外的时间并不长 ,并多以考察、游学为主。具体而言 ,他曾在 1946年9月至 1947年夏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 ,并考察了那里的学校教育。然后他又辗转法国 ,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那里举办的 “国际了解研讨会”,为期七周,结束以后于1947年11月回国。那次欧美之行,一共才一年多一点。接下来一次张先生出国就是在 1956年他与北大的同事翦伯赞、周一良、季羡林一起,到法国参加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因为是参加会议,此次访问的时间也相当简短。再下一次张先生有机会到欧美,要在 23年以后的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张先生有机会不断出访,在各国、各地讲演或参加会议。由此看来,张先生能成为沟通中外史学的重要桥梁,主要是他个人不断努力、做有心人的结果。因为在他那一代学者中间,在欧美留学数年的也大有人在。
认识张先生的人都知道,张先生能熟练运用英文和法文,这自然为他广泛结交国外学者提供了方便。他的许多外国朋友也对此十分欣赏。如曾留学北大、现为美国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的舒衡哲 (Vera Schwarcz)教授,便在她的唁函中回忆道,她与张先生的交往和友情,得益于双方都能操法语。舒教授形容她与张先生是一种 “知音”关系,一语双关,既包含思想的默契,也有语言上的相通。但张先生于法文有如此造诣,也是他勤奋求学、做有心人的结果。张先生出身世家,很小就接触英文,之后又求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于光华大学。他在光华的老师中,有一位哈佛博士张歆海教授 (1898—1972),其英文水平是民国学者中的翘楚。张先生有这样的名师传授,其英文之精湛便容易为人所理解。但张先生法文之娴熟,却是他做有心人、刻苦钻研的结果。据张先生自己回忆,他最初接触法文,是在燕京大学求学的时候。虽然学习了两年,但水平并不高。中断学业以后,他到上海,又随一位法国妇人学习法文,每周两次,获益不小。在这之后,张先生有机会在上海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与法国汉学家佘敷华 (Geoffroy Dechaume)朝夕相处,经常抓紧机会促膝交谈,由此张先生的法文日益精进。在 1956年出访法国参加国际汉学会议的时候,他兼任了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可见经过多年钻研,他已经能熟练运用法文了。
张先生能同时掌握英、法文,为促进学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在西方学术界,英文和法文仍然是公认的学术语言。如有史学界 “奥林匹克”之称的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其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大会 ,就以英文和法文为会议的正式语言。张先生自中国史学会 1980年重新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之后 ,每次会议他都参加 ,并在会上英、法文并用 ,广交朋友,推进学术交流 ,其巨大贡献 ,无人可以匹敌。因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及其所配的翻译 ,一般也只能运用一种语言 ,像张先生那样能双语并用的 ,几乎没有,因此就不免有所限制 ,因为许多欧洲学者和非洲学者 ,都使用法语 ,而北美和其它地区的学者 ,则多用英语。200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悉尼召开 ,张先生以 87岁高龄最后一次与会 (据说他是所有与会者中最年长的一位)。像以前几次一样 ,此次会议规模巨大、场次众多。张先生参加会议十分认真 ,每天按时到场 ,积极提问。他还应邀在会上讲述他与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交往及中法史学交流。他一会儿讲英文、一会儿讲法文 ,幽默风趣、隽永睿智 ,令许多与会者倾倒 ,由此而领教了中国史家的风范 ,敬佩中国学者的学识。可惜这一曲 “广陵散 ”,今已成绝响 ,念之不胜怅然。
不过张先生能为中外学术交流作出如此杰出的贡献 ,成为有口皆碑的 “学术交流大使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有热忱待人、提携后学的 “教书匠 ”精神。上面已经提过 ,张先生出身世家 ,其父张寿镛 (1876—1945)有 “理财家 ”之誉,并是光华大学的创办人、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和教育家。张先生兄妹众多,其中从事财经业的不少。如其兄张悦联 (1907—1992)曾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 ,并与香港富豪董浩云 (其子董建华曾任香港特首 )一家是世交。但张先生从早年起 ,便立志投身教育事业。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其父问他志向 ,他答曰:“我想当一名中学校长 ,大学教授 ”。他父亲含笑说 ,“那你的月薪只有 200元”。但张先生不以为忤 ,几十年来矢志不渝 ,以 “教书匠 ”自许。他指出 ,做一个合格的教师 ,不仅需要有知识 ,而且还必须对教学有热情 :“一个教师 ,如果没有热情 ,没有对科学的热情 ,对教学的热情 ,对学生的热情 ,没有对事情本身的鲜明态度 ,没有感染力 ,即使学问再好 ,也不是一个好教师 ,教学很难成功 ”。他更补充说 ,这一热情 ,可以表现在课堂上 ,也可以表现在课后与学生的交往上。张先生真是说到做到 ,他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 ,春风化雨,诲人不倦,泽被后学,诚为一代教师之楷模。的确,张先生的高超学识、优雅风度和交友之道,已经使他扬名国际史坛,为中国史学家争了光。他于1985年荣获法国总统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 (la Légion d’Honneur),表彰他对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便是一个卓例。但从他的志向来看,这些只是他努力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副产品;他的真正目的,是希望能身体力行,培养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将中国史学推向国际、推向世界。由于张先生每次出国,时间都不长,因此他都有备而来,充分利用时间,把握机会。譬如他在与布罗代尔晤面时,就提出要派中国学生到法国学习历史,对方爽快地答应了。张先生马上追问:“可以收几名?”,布罗代尔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五名吧。”未料张先生马上从口袋里掏出名单交给了对方,让对方大吃一惊。张先生在晚年回忆这事时,眼神充满自豪,为他的机智和聪明自豪。但显然他之运用这些机智聪明,为的是嘉惠后学,而不是为了让自己扬名海外。这是他作为一个全心全意的 “教书匠”的真实写照。自 1980年代以来,由张先生帮助送到海外留学深造的中国学生 (笔者在内),不计其数。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卓著、首屈一指,在史学界无人可以专美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