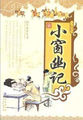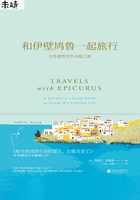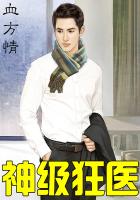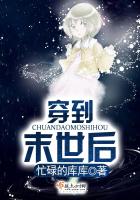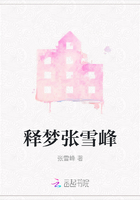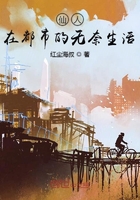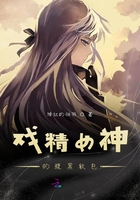顺便指出,通过在狱中的体验,绪山不仅自己大有所获,而且还对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龙场悟道”及“宸濠忠泰之变”有了更深的感悟,认为阳明是“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153];后又“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154]。所以他反复告诫同门,务必对阳明的百死万难工夫有足够的认知,认为后人习道固然简易,然阳明在创设时,却是历经艰险的。他还批评说:“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若此。
自揭良知宗旨后,吾党又觉领悟太易,认虚见为真得,无复向里著己之功矣。故吾党颖悟承速者,往往多无成,甚可忧也。”[155]这些都为整理编纂阳明著作和年谱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持。
不过绪山没多久便改变了对“无善无恶”之旨的认同(详见后述)。读其逸诗,即可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我亦当年曾脱屣,丹成原不离人间”[156];“欲留一偈酬知己,犹恐相传一顿门”[157];会归“无善无恶”之旨后所产生的悔恨与恐惧感溢于言表。他想尽快从“脱屣”、“顿门”的阴影中走出来,重返“人间”,去寻找新的“知己”。
四、“相互取益”
应当指出的是,绪山所发生的思想变化,并不仅仅是单方面地向龙溪“取益”从而向龙溪靠拢,而是与龙溪之间“相互取益”,彼此互补。邹东廓说过:“越中之论,诚有过高者,忘言绝意之辨,向亦骇之。及卧病江上,获从绪山、龙溪切磋,渐以平实,其明透警发处,受教甚多。”[158]这里不仅可以看出钱、王二人有“异形心同”、“打并为一”[159]的理论志趣,而且还说明这种“打并为一”同时也是龙溪逐渐由“超悟”转向“平实”的必然结果。所以东廓又言:“予近得龙溪子意见,言诠一针,更觉儆惕(即敬之工夫),只是时时洗刷,时时洁净,方是实学,实学相证,何须陈言?”[160]而这种“平实”、“实学”的倾向,正是阳明生前要求龙溪向绪山“取益”的“实用为善去恶功夫”。
正因为龙溪与绪山有“相互取益”的那段经历,所以尽管两人后来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分歧,但在《龙溪集》里仍可找到龙溪支持绪山的证据,从而显示出他对绪山的尊重(详见后述)。比如对万表与绪山有关“收放心”说的争论,龙溪便采取了折中而又偏向绪山的立场,并对万表的心态作了这样的分析:
君(指万表)遇应酬烦闷,或思虑耗竭,即欲以他玩适事换境解之,以此为滋养。予曰:“此犹移接之法,若能当下回照,弗令烦耗,方是不转换功夫。”君曰:“才有回照,即落渐法。”予曰:“若论顿法,应酬思虑,觌体莹然,烦闷耗竭,从何得来?总有烦耗,乃是习气硝化未尽。照破即了,更无回换,亦是顿法。须是真悟真修始得,非言语所能凑泊也。”[161]实质上,龙溪是对万鹿园彻底的佛家顿悟法心存戒虑。也就是说,龙溪的顿悟法虽与绪山“收放心”说有一定距离,但却比鹿园的顿悟法要平实得多,而并未完全倒向释家。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说龙溪与绪山有彼此靠拢、会归为一的趋势,决非臆测。
只不过龙溪有时故意要把这种原属双向的“会归于一”看成是绪山单方面的转向:“绪山兄……亦切切以从前意见为戒,乃知忧患困穷有益于人也。”这与绪山所声称的“不肖始能纯信本心,龙溪亦于事上肯自磨涤,自此正相当”[162]的双向互动关系相去甚远。[163]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它所揭示的应是钱、王关系中更深层次的一面。具体地说,就是龙溪在思想立场上的一贯性和讲学争辩时的圆滑性,而绪山则虽然“以从前意见为戒”而有所悔悟,但其内心深处对龙溪还是不信任、不服气的(详见后述)。
当然,绪山不服甚至讨厌龙溪,实乃事出有因。因为龙溪曾给人以喜欢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的感觉,所以当时“学士颇有议其后者,以为不誉人以自贤,则微人以自显”[164]。尽管管志道后来承认“此苛论也”,但仍批评龙溪“亦不无好胜之隐嫌焉”[165]。应该说,龙溪的好胜是造成他与绪山关系疏远的原因之一。
针对浙中王门两大思想领袖之间所呈现出的这种复杂现象,明末清初几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的编纂者,无不按照自己思想情感和价值标准,对阳明门人尤其是绪山学说作了精心取舍,这是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尤其是像绪山这样因著作失传而使明末清初的学术史编著成为惟一可凭之史料时,应充分考虑的问题。比如黄宗羲、周汝登等人所录的绪山著述,就因各自的学术立场不同而在选录时颇有差异,这就产生了这些文献究竟有多少可信度以及哪一种更为可靠的疑问。其实,梨洲、海门等人所录内容都是可信的,只是前者基本上是以阳明在“天泉证道”中的分析为据,而选录了绪山与龙溪思想的不同面;后者的目的则是为了强调绪山、龙溪的一致性和浙中王门的团结性,故竭力“将先儒宗旨凑合己意”[166],所选内容比较突出两人的相同面。至于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亦因“杂收不复甄别”,而“未必得其要领”[167]。然后人在解读绪山时,大都受刘宗周和黄宗羲的影响,因此只看到钱、王二人的差异性,而看不到绪山思想由于“数变”而与龙溪思想所具有的一致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绪山思想性格的整体把握。近年来这一状况已有所改变,中纯夫、吴震、彭国翔等研究者均对此予以了纠正。
五、“不失儒者之矩矱”
然而必须看到,钱、王二人在阳明在世时就已产生分歧,后又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意见相左,所以就整体而言,两人算不上是“志同道合”者,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分歧要远远大于共识。
比如在对甘泉思想的评价上,钱、王二人就很不一致。黄宗羲说绪山“不失儒者之矩矱”,这与“大都多谨守先儒之矩矱”[168]的甘泉门人极为相近。[169]而与绪山一起将《阳明文录》“刻之行世”的闻人诠,作为当时著名的出版家[170],曾分别师事于阳明和甘泉,后又刻有《甘泉文集》。绪山既然与其共定《阳明文录》,当不会在编纂方针上有何分歧。换言之, 《阳明文录》的编订出版,是在王、湛门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完成的,其中吸取了甘泉学派的某些建议是完全可能的。正因为如此,绪山才会把增录《朱子晚年定论》和重刻《山东甲子乡试录》的重要工作放在由甘泉门人史际建立的溧阳(与湖州长兴相邻)嘉义书院来完成,并且还在书院内合祀阳明与甘泉像,又带着子侄、女婿“定期来会”[171]。至于绪山本人的思想倾向,则从其先后两次直接问道于甘泉的经历中即可看出。一次是嘉靖十一年,另一次是嘉靖二十七年。两次会面,对绪山的影响都很大。在绪山看来,阳明、甘泉“终不得对语以究大同之旨,此亦千古遗恨也”。据《甘泉集》卷一七《赠掌教钱君之姑苏序》记载:嘉靖十一年秋,绪山“问教学之道于甘泉子”,在甘泉的引导下,绪山提出了一系列会通王、湛的重要意见,如“知之良者天理也”,“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夫良知必用天理,则无空知”等。
后在《上甘泉》书中,绪山又说:“良知天理原非二义,以心之灵虚昭察而言谓之知,以心之文理条析而言谓之理。……今曰良知不用于理,则知为空知,是疑以虚元空寂视良知,而又似以袭取外索为天理矣,恐非两家立言之旨也。”[172]另据《王门宗旨》卷一〇《绪山语抄》载:嘉靖二十七年冬,绪山“乞先君墓铭,往见公(甘泉)于增城”。甘泉曰:“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今游先生之门者,皆曰良知无事学虑,任其意智而为之,其知已入不良,莫之觉矣,犹可谓之良知乎?所谓致知者,推极本然之知,功至密也。今游先生之门者,乃云:‘只依良知,无非至道。’而致知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纵情恣肆,尚自信为良知者。立教本旨,果如是乎?”绪山起而谢曰:“公之教是也。”甘泉则曰:“吾子相别十年,犹如常聚一堂。”绪山又曰:“……始知只一无欲真体,乃见‘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同活泼泼地,非真无欲,何以臻此?”甘泉慨然谓诸友曰:“我辈朋友,谁肯究心及此?”可见绪山十分推崇甘泉,而甘泉亦相当器重绪山。对甘泉“只依良知……至有纵情恣肆”的严厉批评,绪山深表赞同,而对绪山的到来,甘泉则感觉“犹如常聚一堂”,两人可谓是相见恨短,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者。然龙溪却不仅自己回避对甘泉的评价,而且还认为绪山有关会通王、湛的言论,乃是“忧道苦心,不得已而有言者也”[173]。把绪山的一些言论看做违心之言,从而显露出不同于绪山的湛学观。[174]不惟湛学,绪山对朱学的赞誉在阳明高足中亦是相当突出的。
其曰:“余少业举子,从事晦庵集注、或问诸说,继见吾师阳明夫子,省然有得于良知,追寻朱子悔悟之言,始信朱子学有原本,达圣道之渊微矣。故尝增刻《朱子晚年定论》,使晦庵之学大显于天下。”阳明出于舆论压力,才辑录《朱子晚年定论》一卷,以为自己辩白;而绪山则出于对朱子推崇和为阳明辩护的双重需要,居然增录《朱子晚年定论》二卷,以表明自己坚定的朱、王折衷之立场。
只是绪山“服膺朱子”,却“不泥其中年未定之说”[175],而只强调其晚年定论。这就使绪山既保持了与阳明的一致性,又为自己维护朱学的形象作了很好的宣传。管志道《题陆少府宪峰公德政编》中所记载的陆宪峰,曾是绪山的弟子,管氏说他“渊源有自”;而其胤子陆仰峰,则学于李材和许孚远,且“有程朱之气骨”,管氏又称他“揆厥所自,则公之义方有在也”[176]。由此似可看出陆氏父子与绪山、见罗、敬庵之间的某种联系,而见罗、敬庵之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折中朱、王,出入湛门。故徐渭《送钱君绪山》诗云:“肯使异同虚白鹿,但教升散绕青毡。文成旧发千年秘,道脉今如一线悬。”[177]认为绪山是既“悬”阳明之道脉,又“虚”朱、王之异同,是立足王学、化解分歧的高手。故此笔者推断,绪山不仅有王、湛归一的诉求,甚至有朱、王合一的意愿,在阳明学的坚定性上和纯洁性上,明显不如龙溪。
至于绪山对三教的态度,则更显出他与龙溪的不同之处。由绪山编纂的《阳明年谱》中曾记述了一次发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在金陵新泉精舍举办的讲会活动,当时赴会的绪山曾应甘泉门人何迁的邀请,登上报恩寺塔游玩,其间跟与会者有一段关于佛道二教的重要对话。与会者问:“师门亦有二教乎?”绪山答曰:“师尝言之矣,‘吾讲学亦尝误人,今较来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众皆起而叹曰:“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 “下塔, (绪山)由画廊指《真武流形图》曰:‘观此亦可以证儒佛之辩。’众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无得,欲弃去。感老妪磨针之喻,复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画《尧流形图》,必从克明峻德,亲九族,以至协和万邦;画《舜流形图》,必从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渔,以至七十载陟方;又何时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后可以成道耶?’诸友大笑而别。”[178]其反对三教合一、“不失儒者之矩矱”的立场,何其鲜明!而那时离开他在狱中所发生的思想转变仅仅七年!
为进一步说明绪山、龙溪的思想异同,我们不妨再对《龙溪集》卷二〇《绪山钱君行状》中的一段对话作番解读:
予(龙溪)尝谓:“君(绪山)所造大概已坚恳凝定,中间形迹未尽脱化,未可全道功行未修,或者彻底透露处,尚有可商量在。”君谓:“彻底未尽透露,此正向来功行之未修耳。功行若修,更无可商量矣。先师云:‘眼前利根之人不易。’学者未肯实用克己功夫,未免在意见上转,遂谓本体可以径造而得,乃于随时实用功处,往往疏略而不精,流入于禅寂而不自觉,甚者恣行无忌,犹自信以为本体自然。此吾党立言之过,不可以不察也。”予谓:“君指点学者之病,大概了了,未可执以为定见。司马君实功行非不修,说者以为未闻道。吾人所学,贵在得悟,若悟门不开,无以征学,一切修行,只益虚妄耳。此非言思所能及,姑默识之,以俟日后之证可也。”君尝《与季彭山书》曰:“兄与龙溪往复辨论,未免各执所见,非所以相取也。良知是千古灵窍,此处信得及,彻上彻下,何所不通?龙溪之见,伶俐直截,泥功夫于生灭者,闻龙溪之言,自当省发。
是龙溪于吾党学问头脑,大有功力也(按:此句未见于《明儒学案》卷十二《与季彭山》)。但于见上,微觉有著处,开口论说,千转万折,不出己意,便觉于人言尚有漏落耳。”观此,君于予言,大段已无逆于心。著见之教,敢不自勉?夫子“互相取益”之言,庶几不至辜负耳。
这段对话至少向我们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绪山与龙溪的分歧后来虽有所弥合,但并未彻底解决,尤其在“入处”问题上,龙溪仍坚持“证悟”应先于“修行”的立场,所以其针对绪山有关学者自信本体自然之病的一番议论,以“未可执以为定见”予以回应。第二,绪山《与季彭山》书中对龙溪的一段肯定性评价,未见于《明儒学案》,反之《明儒学案》中对龙溪的一段批评性论述,也未见于《绪山钱君行状》。由此看来,黄宗羲确实是想消除至少是淡化绪山与龙溪的相同点,而龙溪也是只转引有利于自己的绪山之言,而删除了不利于自己的绪山之言。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绪山不仅常评论龙溪,而且其评论亦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第三,龙溪虚心接受了绪山有关“著见之教”的意见,并再次强调要不辜负阳明的“互相取益”之言,从中愈加显露出他对绪山的尊重。
实际上,绪山、龙溪二人在“证悟”与“修行”孰先孰后问题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后在阳明让钱、王二人“互相取益”的教导下,加之两年牢狱生活的历练,虽使绪山对此问题有所省悟,思想发生了转变,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绪山始终对道德沦丧、世风败坏的社会现状及其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因果联系抱有警觉,而由“入处”问题所引发的其他分歧,亦必定会渐趋增多和激烈。试看罗念庵于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间所撰《念庵集》卷五《夏游记》 里的这段实录:
……而绪山乃曰:“知无体,以人情事物之感应为体,无人情事物之感应,则无知矣。”将谓物有本末者,亦有别解欤?人情事物感应之于知,犹色之于视、声之于听也。谓视不离色,固有视于无形者,是犹有未尽矣,而曰“色即为视之体,无色则无视也”,可乎?谓听不离声,固有听于无声者,是犹有未尽矣,而曰“声即为听之体,无声则无听也”,可乎?质之龙溪未发之说,则知之为体,盖自有在,固不必若是之牵合也。
说明钱、王二人甚至在对罗念庵归寂说的批评上,都存在立场上的差异。具体地说,就是龙溪有“未发之说”,而绪山则坚持“已发之说”[179]。由龙溪的“未发之说”可得出“知之为体,盖自有在”的结论,而由绪山的“已发之说”则必得出“知无体,以人情事物之感应为体”的论断。尽管这只是念庵的记述和推论,但至少能使我们看清在批判“归寂说”时绪山的“牵合”与龙溪的“圆融”,进而证明绪山、龙溪不仅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有意见分歧,而且在处理各种学术纷争时所采取的应变之策亦有明显区别。而造成这种分歧与区别的主要原因,除了以上所述的诸多个性特质外,恐怕还有两人为争夺学术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而展开的明争暗斗。
(第三节 钱、王关系之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