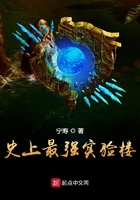三娘说:
其实,我给林驿丞出的主意也不是什么新鲜招数,以前也用过,那就是闹鬼。据王品说,甭看那个团长是个当兵吃粮的武夫,却偏又信神信鬼,动辄就拜关公,翻历书,想必是个不经吓的主儿。林驿丞也觉得这个法儿不赖,不过须先试一试他。正巧头一天地方上来人向团长告状,说有俩大兵在庙里便溺,住持过来劝阻还挨了揍;这个团长护犊子,三言两语将告状的敷衍走,对他的手下不管也不问。转过天来,他的肚子就发作起来,上吐下泻,一袋烟的工夫跑了八趟茅房。王品跟团长说:“别再是庙里供着的神佛显灵了吧,怪罪了,以前这类事也出过几次。”那个团长怕了,赶紧约束兵役,传示手下如若无故滋事,干扰地方,违命者斩,还把在庙里便溺的俩兵绑了一天,饿了一天。这样一来,团长也不闹病了。团长说:“这他娘的神佛还真灵验。”其实,都是我在饭菜里做了些手脚。见这一招真的管用,林驿丞高兴了,连声说:“这就好办了。”
过两天,吴佩孚的直军攻打京城,张作霖告急,调动四处人马赶紧增援,驻通州城的这个团也被调走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喝了一晚上的酒,放了一通鞭,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安生做生意了。谁知松快了不几日,团长带着他的人马又回来了,说是把吴佩孚给打败了。这下子,客栈上下又都堵心了,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凑到一起商量对策。后来,还是林驿丞想出一个蔫坏的办法。
几个爷们儿不知打什么地方淘换来女人的经血,也不嫌腌臜,和黑狗的血混合在一处,偷着涂抹在散住各处大兵的铺盖上和衣裳上。这事很快传到了团长的耳朵里,起初他还不信,没几天,他的床上和衣裳上也有了。审问了随从和林驿丞他们,都说没在场,也没见任何可疑的人。当兵的最忌讳这个,以为是不祥之兆。林驿丞忙前跑后,给他们请了先生驱邪,里里外外地作法,折腾了些日子。团长和他的手下都多少心存忌惮,老实了一段时间,个个求神拜佛,问卜祈签,倒顾不得糟害百姓了。
可惜,平静的日子并不长久,吴佩孚的队伍很快就卷土重来,不光围了京城,连通州城也一并给围个水泄不通。一时人心惶惶,大兵更是慌了手脚,就开始不规矩起来,偷鸡的摸狗的都是常事了,抢铺子砸饭庄的事也时有发生。团长不管这些,只派些暗探,混出城外探听消息;得到不好的信,他就发脾气,一日总要摔上几个杯子盘子。李耳心疼,就生气地说:“这么下去,客栈里的好瓷都得叫这个混账王八蛋给摔光了。”
忽然,婆子说祝氏叫我到她那边去。我当又出什么意外呢,却原来是她两三个月天癸水不至,像是有孕了;又怕是谎信儿,预先告诉了林驿丞,让他空欢喜一场。所以才找我来,意思是叫个郎中来,把把脉。我趁机讹她,问道:“嫂子大喜,要是果真了,你要怎么谢我?”祝氏说:“你先去招呼郎中,还指不定是不是呢。”郎中来了,说是喜脉无疑,祝氏才放了心,对我说:“这些日子总悬着一颗心,两天米水没打牙了,现而今倒真饿了。”我笑说:“瞧你那点子出息。”忙从厨下拿来馒头小菜。她竟跟逃荒的难民一样,大嚼起来,也不讲究个吃相。我闹着让她请客,她说:“请是一准要请的,最好是待告诉了老林之后,再请不迟。”我是个急性子,就说:“一句话的事,何须费那么多的口舌。”正说着,林驿丞回来了。
我抢着说:“林驿丞,我给你道喜呀。”林驿丞一屁股坐凳上,长吁一声道:“那个团长整天闹腾,愁都愁煞我,何喜之有?”我指了指祝氏的肚皮说:“这不就有了嘛!”祝氏一个劲儿给我丢眼色,不让说。林驿丞早蹦起来,问祝氏:“真有了?”祝氏羞红了脸,低头不答。林驿丞搓着手,在地上转了十几个来回,嘴上只是叨叨:“上苍有眼,上苍有眼。”想必有这么一桩喜事,夫妻俩未免要见个礼唔的。我赶紧告辞,躲出去只等着喝喜酒了;又挨家挨户告信儿,让他们不必忙饭了,林驿丞晚上请客。王品媳妇还问:“林驿丞一脑门子的官司,请个什么客呀?”我也不明说,只故弄玄虚道:“我也是掐算的,要是算不准,你把我的招牌砸了,我还磕头给你赔不是。”果然,祝氏不一会儿就过来招呼我们,王品媳妇直说:“想不到姐姐你还有这个半仙儿本事。”
这一晚上,林驿丞笑得口都合不拢了,只是提起那个团长来,他才掉下脸来。打仗打得不顺,上一阵儿,团长损了八十多人,其中一半还都是他从四平老家带出来的。这几日,团长跟雷打了一样,提不起精气神来,看什么都碍眼,窑姐儿同他撒个娇,还让他踢了两脚……在桌上说了一会子,骂了一会子,又尽情地喝了一会子。张目突然问道:“在座的你们谁会学鸡鸣狗叫?”李耳答话说:“这个,我是使不来,你须去问王品兄弟。”王品大包大揽道:“鸡鸣我会学,狗叫我也会学,只不知你要出什么典故?”张目又问:“可会学老鸹叫不?”王品即刻学了两声,叫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叫王品媳妇捂住他的嘴:“忒难听了,多不吉利呀。”张目却对王品说:“光你王品一个会学还是不行,还要将我们每个人都教会了,才是大观。”林驿丞跟王品他们脑瓜转轴都快,似乎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却还蒙在鼓里。问张目个究竟,他还拿上搪了,说道:“现在还不是说给你听的时候。”不说拉倒,我还懒得听呢。
转天的后半夜,客栈里的四角满都是老鸹的叫声,比猫头鹰叫得还瘆人,幸亏我们都知道这是张目他们作妖,不然非吓尿了裤子不可。我和哥儿蒙住脑袋照睡就是了,装听不见。团长跟那个窑姐儿却不知底细,三更半夜冷不丁老鸹声四起,吓得他们寒毛孔都奓起来了,浑身直抖,也不敢睡了,招呼随从出去把老鸹赶走;随从也怯阵,只忙忙地往天上打两枪,就又钻回房去。老鸹吵吵了半宿,天晓白了才清静。转过天来,团长把脸都气白了,冲林驿丞喊道:“这是个什么险恶的住处啊,老鸹叫个不停,这样下去,实在是不能住了。”
林驿丞心里高兴,嘴上却说:“往时也不曾有过老鸹,只是这几日不知怎的了。”那个团长天天闹着住不下去了,却又不搬走,一天天就这么耽搁下来。众人只能干着急。林驿丞这一程子最闲,祝氏怕肚里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一心静养,将他轰出来单睡。他就一宿一宿地在团长窗根底下闹唤,白天就跟团长说:“料想是我们这个客栈风水不济。若是佛门圣地或王公贵处,不祥之物便不敢来缠了。”那个团长只会胡卷乱骂,又在鸡蛋里挑骨头:“你们这个客栈,我前后都查了一遭,竟连个门神都没请上一对,怎能安宁?”林驿丞赶紧叫伴儿去请门神。所有的门上都粘了,夜里仍旧还是闹,团长这一回没话说了。张目一日跑回来,进屋就拉我到里屋;我还当他是又动了兴,要做那个勾当,就推拒道:“大白天的,也不挑个时候。”张目却噗嗤一声笑了:“好端端的事,也叫你想邪了。我是来跟你合计正经事的。”他这么一说,倒叫我涨红了脸。张目说:“西边有个道观,道长你可熟识?”我爱搭不理地说:“不熟识,却是认得的。”张目又说:“他观里养着一条大蟒,足有两人长,而且听得懂人言?”我说:“我也只是听说,并不亲见。”张目缠磨着说:“你能不能借来用一用?”想一想,才刚他还取笑我来着,便说:“要借,你去借,我才不管呢。”
张目见我还为先头的两句笑话生气呢,就将我搂在怀里,脸贴着脸,把手在我胸前轻薄了一回。我怕自己把持不住,又让他得手,就推开他:“借那大蟒作甚,齁吓人的。”张目两手搭在我的肩上,亲了我一下说:“就因它吓人,我才要借它。”他这一说,我就知道他的用处了,便相跟着一前一后到了道观。道长跟我是打过交道的,也不太见外,只是听说我要借蟒,不免奇怪,问做什么使。我对他说:“我借它去驱魔,断不会招灾惹祸。”道长起初还有些不舍,听我这么说,也不好不答应。临走嘱咐了许多话,怎么让它跑,怎么叫它盘,还有怎么叫它纵身跃起;并一再告诉我俩不可随便喂食,十天半个月不喂,它也饿不死。我们叫了辆车,那蟒盘起来也比两个人的腰粗,只好拿被单将它遮起来,免得把拉车的吓着。
张目说:
这条蟒要是冷不丁见着,十个有九个要吓得屁滚尿流,两眼铃铛一般。能把道观的镇观之宝借来,真是万幸中的万幸,总还是三娘的情面。不然,供了十好几年通灵性的一条大蟒,岂能轻易说借就借?将大蟒带进客栈也得神不知鬼不觉,裹在送菜送粮的车流当间儿,混进了客栈,可是又不知把大蟒放什么地界儿合适。三娘说她有办法,叫我将大蟒搁在假山边上,就不要管了。待我打发走了拉车的,再回来,不光大蟒没了,就连三娘也寻不见影儿了。四下找,也没找到,正纳闷,三娘变戏法似的又冒了出来,冲着我嘻嘻地笑。
“你把大蟒藏在哪里了,这么一会儿工夫?”
“先让它老人家迷糊一觉。”
“万万不可委屈了老道的心肝宝贝,有个一差二错,咱担待不起,老道还不得跟咱们豁出老命去?”她究竟把大蟒安置在什么秘密地方了,我绕着弯子说半天,三娘也不肯告诉我,我也拿她没有办法……
我夫妻二人温上一壶酒,喝了一会子,又叫三娘坐在我的膝头。我含上一口酒,嘴对嘴地递给她,趁机将她衣襟解开,想摩弄一下她的粉乳。她却推开我:“说着说着便就下道了,一点正行都没有。”然后就进里边看哥儿去了。待会儿又出来,嘱咐我:“晚上要闹古怪,只找林驿丞和李耳就行了,就别扰王品去了,人家媳妇坐月子还没出满月呢。”我说知道了,又扯她一道喝酒,她脸儿一变:“我就见不得你的轻狂相儿,不许喝了,免得耽误了事儿。”顺手,她还把酒壶收走了。我也只好起身去找林驿丞,合计怎么好好地将那个混账团长吓上一吓,来一回狠的,非让他尿裤子不结。
想得毕竟简单,真要把这么个大蟒弄到团长的房里,着实累了我和林驿丞他们通身的汗,好歹抓了个空儿,才将大蟒放到团长的铺底下,念个咒,施个令,叫这大家伙盘起,不可发出动静来。甭看林驿丞说起绿衣才子、红粉佳人滔滔不绝,一套接一套,遇见这大蟒就一无章法了,只战战兢兢地问我:“这么个大家伙,能听从你的招呼么,发作起来可不是玩儿的?”我安慰他说:“尽管放心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林驿丞又说:“经心些,别有什么闪失才好。”李耳虽然不言语,我知道,他也是半信半疑,摸大蟒一下,就哆嗦一阵子,眉头皱成一个疙瘩。
看似我是十足把握,其实,我心下也嘀咕,万一我号令它,它不听从怎么办?我毕竟不是那个老道,跟它厮磨了十几年,知道脾性了。本来就提溜着心,林驿丞偏还吓唬我:“万一大蟒爬出来,团长乱枪将它打死了,又怎处?”果真要是那样,就无法跟老道交代了。到后半夜,料想团长跟那个窑姐儿闹也闹了,该歇了。林驿丞说:“你施令吧。”我还有点担心,便说:“再等上一等,兴许团长淫情未足,再跟窑姐儿找个零儿呢。”李耳也催我:“灯黑了有一会子了,就是找十个零儿也够了,团长又不是驴。”无奈,我只好嘬唇尖啸三声,少时,团长那屋便倒海翻江似的闹将起来,鬼哭狼嚎一般。林驿丞问道:“不会把团长咬死吧,咬死了就给咱添了天大的麻烦了。”我说:“不碍,大蟒的毒牙尽已拔去了,咬不死人的。”林驿丞这才放心,又说:“工夫不小了,快上去吧。”我们仨就提着灯笼去了上房,嘴上嘘呼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只听团长和那个窑姐儿可劲儿喊救命,嗓子都喊哑了。我们进去时,只见两人都站在窗台上,抱成一团,瑟瑟发抖。趁着月光,偷眼瞧瞧,那个窑姐儿居然还光着个屁溜儿,倒也好,就是吓尿了也尿不到裤子上。我们几个想笑又不敢。借敞门的空隙,大蟒吱溜窜出屋去,我将它引到院子外边,三娘早等在那里,找几个厨下的下人一起把它搭上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又送回到道观去,不题。我回到房内,团长正在发脾气,骂了林驿丞,又骂随从。那个窑姐儿惧怯地说:“大人,这里实在是住不得了,快搬走吧。”林驿丞还拦着:“怎么能搬走呢,好不容易请来的,团长能住在我们这,那是客栈的造化。”团长明明已吓得泥塑一般,偏还嘴硬:“我是枪林弹雨中爬出来的,自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是这个妇道胆忒小。”我上赶着问:“闹哄半天,到底是怎么了?”那个窑姐儿说:“刚头有好大的一条蟒爬到我们床上来,吱吱地直冲我们吐信子。”我操起一根棍子说:“在哪儿了,我来教训教训这个孽障。”
团长和团长的两个随从里里外外一通找,均不见大蟒的影子,刚头团长只是怕,现在却是惊了,团长脸色焦黄地说:“活见鬼,简直是活见鬼了。”即刻发号施令,搬家走人。我们还装模作样地再三挽留:“团长走不得呀,还没伺候够您老呢。”团长说:“再不走,今日只是遇见大蟒,也许明天就会遇见牛头马面、夜叉小鬼也说不定。”两个随从赶紧传令禀示,招呼一队兵来做开路先锋,拉着窑姐儿一溜烟地跑了,跟来时的威仪光景相去甚远。我们觉得闹得还不够,追在屁股后面拼命地嚷嚷着:“团长大人请留步。”两个随从拔出枪来,镇唬我们说:“再跟着,就崩了你们。”林驿丞还可怜巴巴地说:“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长官尽可以提出来,掌嘴也随您,只是别说走就走……”随从跳下马来,竖起眉毛说:“还照顾不周呢,连五丈长的蟒蛇都来伺候了!”另一个也说:“你们那个地方,就是八抬大轿来抬我们,我们也不住了。”林驿丞拍着大腿说:“你们这么一走,传出去,我们客栈多失脸面呀,就仗着团长给我们脸上贴金呢。”再抬头,团长一行早就跑走了。
“别装了,装也没人瞧了。”我对林驿丞说。
“这个混账总算滚了。”林驿丞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我说:“还不是多亏我足智多谋。”
林驿丞翻脸不认账了:“怎么是多亏你呢,明明是大家伙的主意吗,李耳你说对不对?”
李耳也跟着说:“可不是,一两个人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气得我嘴唇都哆嗦了:“好啊,你们过河就拆桥!”
李耳说:
为庆祝将团长赶出客栈,转天,我们几个喝了个痛快,提起大蟒的事,笑得东倒西歪。老娘说:“你们天天团长长,团长短,我耳朵都听陈了,既然他已走了,往后就不要再把他挂在嘴头上了。”
林驿丞说:“老娘说得极是,从此不许提这个损鸟,我来给你们说个笑话听听。”三娘马上站起说:“我知道你那笑话是什么行子,且等老娘跟孩子们都走了你再讲,也免得污了我们的耳朵。”娘们儿们都走后,张目催道:“现在可以了,你讲来。”林驿丞便说:“三河有个傻瓜,娶媳妇头一回行房,脱下女人的裤来,露出底下的一道缝。傻瓜当下就恼了,跑到隔壁书生家去请教,说他娶的媳妇相貌头面都很俏,就是小肚子底下有个豁口,万一把肠子流出来,可怎么得了?”书生说:“不妨事,我拿我媳妇的针线给她缝上,就漏不出来了,你先等我,缝好了就来唤你。”书生进了洞房跟新娘花烛一场,然后回来,告诉傻瓜:“缝停当了。”新郎谢了他,进屋查验一番,突然骂道:“这年头,书生也靠不住了,说是用针线缝好,谁知却是糊弄局,只拿浆子糊了糊就了事了。”我们都笑了一阵子。我说:“我们这一回的糊弄局糊了团长和那个窑姐儿一脸。”林驿丞嘱咐大伙儿:“就怕有一天,团长明白过来,又来找我们的晦气,还须时时刻刻提防着才行。”张目说:“我常盯着他们就是了,一有风吹草动,我们提前可以有个防备。”转天,张目就告诉大伙儿:“团长又搬回妓馆里了,猫在里头,总不出来。”林驿丞说:“可别大意了。”不过,这一次是林驿丞多虑了,很快团长就自顾不暇,顾不上跟客栈过不去了。一日,半夜我被吵醒,听得城外各处一片嘈杂,似雨非雨,似风非风;张目他们也都披着小袄跑出屋来,听着。张目说:“你耳朵好使,细细听听,到底是什么动静。”我听了一会子,对他说:“像是枪响,只是太密集了,反而听不清爽。”林驿丞最嘀咕,派伴儿出去扫听。一会儿,伴儿回来说:“是吴佩孚的直军队伍围着通州城往里打呢。”林驿丞问他:“那个混账团长呢。”伴儿说:“也在城上带着兵往外边还击。”枪声到天明才歇,料是直军被团长打退了,我们也打着哈欠各自回屋睡去了。
城被围了,河也被封了,外头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也出不去,我们客栈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一个客也不上门了,客栈的人个个都当起了甩手掌柜。奉军的兵粮紧了,就到各处去抢,进馆子也是白吃白喝,敢说一个不字,便拿枪朝天砰砰乱打,唬得买卖家大气不敢吭一声;唯有客栈太平,没一个兵来招惹。旁的买卖家都纳闷,就四处打听,问是谁在背后给我们撑腰。大兵告诉他们:这个客栈闹鬼,双日子男鬼闹,单日子女鬼闹,逢年逢节,蟒蛇妖狐跟着一起闹。住店的人,男的吸精,女的吸血……这么一传,遍通州城人人皆知,谁打门口过都胆战心惊。孩子淘气,他娘吓唬他说,再不听话,就把你绑潞河客栈去。这不是砸我们客栈的招牌吗?我们赶忙四下里解说,解说愈多,疑者愈众,不仅老主顾们不来了,就是挑担送酱醋的,宁可生意不做,也都躲了。把林驿丞气得直跺脚,又不便解释说,客栈闹鬼都是为赶走混账团长,叫他知道了还不回来报复?也只能干着急。我们劝他:“兵荒马乱,即便没有闹鬼一说,客栈又能有多少生意可做?忍忍吧,忍到天下太平再想办法。”林驿丞愤愤道:“你们说的乍一听起来,仿佛有几分道理,可是,掉过个来想,不过是瞎掰。这个国家何曾真正有过天下太平的时候?”反正急也没辙,眼瞅着门庭日益冷落,车马也愈加稀疏,非往日情景。我和丫头子日日在菜园里跟菜农做农活,解愁释闷;张目、王品他们则闭上门,自在得受不得。我的丫头子奇怪,就问我:“他们怎么都不起床呀,病了吗?”我忍着笑说:“是,他们都累病了。”丫头子还偏刨根问底:“也没见他们做什么活路啊?”我被问得没了主意,便敷衍道:“他们做活时,你早睡了。”我的丫头子是个实心眼儿,见着张目的俩小子竟说:“你爹你娘都病得起不来床了,你们还出来玩?”那俩小子狡辩说:“谁说病来,刚头还说笑话来。”丫头子毫不犹豫地就把我出卖了:“我爹才刚说的。”我怕惹事,赶紧哄丫头子走了,说上树给她摘海棠去。
怕惹事,结果还是惹上了,张目的小子回去给我告了状。三娘找我算账:“你跟孩子多嘴多舌说什么来着?”我赶紧洗刷自己:“天地良心,犯歹的话我一句都没说。”三娘不信,捋胳膊挽袖子就要教训我。跑,我没她腿快;打,我又打不赢她,正不知如何了局。林驿丞那边厢叫嚷起来:“张目家的,你嫂子发作起来了,快去请稳婆子来。”三娘见林驿丞如此吩咐,不敢耽搁,忙忙地去叫人了。我赶到林驿丞跟前,主动请命:“有什么营生,你尽管指派。”林驿丞一把几乎搡我一个跟头:“我都使不上劲儿,你就更多余了。”祝氏在屋里叫得吓人,林驿丞就更着急了。正火上房的时候,三娘引稳婆子到了,砰地撞上门,将我跟林驿丞都关在了门外。少顷,听见一声婴儿的啼哭,我们才不禁松一口气。林驿丞趴在窗台上问:“媳妇,你怎样了?”祝氏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好着呢。”林驿丞又追着问:“生个儿,还是生个女?”三娘说:“胖丫头子。”林驿丞扭脸瞪我一眼:“都怪你跟着,闹个跟你一样的结果,要是张目在的话……”未等他的话音儿落地,我便接口说:“要是张目在的话,你就生上一对胖儿子了,是不?”林驿丞嘿嘿一笑:“不是俩儿子,也得是一儿一女。”这时候,三娘招呼说:“进来瞧瞧吧。”我跟在林驿丞的屁股后面也往屋里走,林驿丞又将我推出来:“你赶紧告诉老娘和王品两口子一声去。”没办法,我只好掉过头来,去知会王品一声。王品媳妇架着老娘,提溜着红糖奔林驿丞家去;我坐在凳上,叫王品拿酒给我喝。王品说:“待会儿有喜酒不喝,偏要在我儿这喝寡酒,真是个烧包。”我一想,对呀,不能便宜了林驿丞,得让他把家藏的陈年老酒找出来,叫我好好解解馋。
这一晚上,没人灌林驿丞,林驿丞倒是自己把自己灌醉了,端着酒盅不住地向老天叩拜:“在下蒙苍天厚恩,原以为罪孽深重,手上沾的鲜血太多,再不会有子嗣延续香火了,谁知苍天法外施恩,我姓林的死不足以报万一……”三娘对张目说:“快扶他去睡下,也省得在这里一个劲儿胡说八道。”
直军攻不进来,却又不退,围个铁桶阵。日子久了,城里的空气越发紧张了。四门口都跪着披枷带锁的犯人,那是夜里趁黑驾船企图出城的渔人和船家,也有逃兵,个个被打得遍身是血。林驿丞告诉客栈里所有人都不许迈出大门一步,反正我们藏的粮食足够吃上一年半载的了,饿不着。听说,城里穷困人家为了一口袋米面而卖黄花大闺女的不在少数,不知我就怎么无端想起了当年的九儿,眼泪就像水也似的直落下来。偏巧叫丫头子瞅个满眼,她用小肉手替我抹着泪问道:“好好的,你为何要哭啊?”我伤心得要死,也顾不得什么了,一把将丫头子搂在怀里,嘴上却说:“爹不是哭,是害眼。”丫头子挣脱我的手说:“你等着,我去给你讨眼药去。”我问她:“你去哪里讨去?”丫头子理直气壮地说:“除了张家,还能有谁家。”我又问:“为何非找张家呢?”丫头子说:“那是我婆家呀。”想来,这又是九儿做的一件功德,还是她想得长远。
这时候,照看丫头子的妇人捎话来说:“林驿丞的娘子祝氏要姐儿过去说说话。”我将丫头子送过去,老娘他们都在。因还未出满月,祝氏在里屋斜倚着个素花大靠枕奶着孩子;我不便进去,只坐在外间。祝氏招呼丫头子到她跟前去,看看小妹妹长得俊不。我听丫头子说:“景儿姐姐,你说俊不?你要说俊,那就是俊。”我心说:丫头子越大越随她娘了,能说又会道。林驿丞坐在杌凳上一口一口地抽着烟,理也不理我。我说:“你见了客,一杯香茶都舍不得奉上,像什么话?”林驿丞皱着眉说:“别招我,我正心烦。”我问他又有什么烦心事,林驿丞说:“从早上我就派伴儿出去找个奶妈来,溜溜走一天了,到这会儿了,还没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子:“风传外头正为守城人手不够抓壮丁呢,伴儿别是叫他们绑了吧?”林驿丞着急地说:“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我腾地站起来,拽着他的胳膊说:“那还坐这里磨蹭什么,还不赶紧找找去。”
我们相跟着走到大门口,刚要出去,林驿丞又犯嘀咕了,将我拉住:“咱就这么直不楞登地出外,也叫人抓去守城去怎么办?”我一想也是,那不正好送上门去吗!幸亏林驿丞人头熟,招呼俩老叫花子来,一个瘸,一个拐,估计求大兵要他们,大兵也不要。我们把伴儿的模样长相、个头高矮和穿着打扮详详细细说了一遍,老叫花子却不耐烦了:“二位爷不用费这么多口舌,我们爷们儿诚心报效,这就去了。”我冲着他们的背影喊:“慌什么呀,我还没说完呢。”林驿丞说:“论察言观色,叫花子比我们在行,他们指这个糊口呢。”回复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有了,伴儿果然是被大兵掳了去,现在东门楼子上搬砖,以加固城墙。林驿丞说:“他还是个小崽子,怎当得起这份花力气的差使。”老叫花子说:“莫说他已十三四了,就是八九岁拾马粪的孩子,那里也有六七号了。”我问:“你们知道他们夜里宿在何处吗?”老叫花子转了转眼珠儿:“怎么,二位爷是打算将孩子鼓捣回来?”林驿丞说:“讨得回来就讨,讨不会来就抢。”老叫花子笑了:“何须那么大费周章,一句话就能办妥。”我不大信,怀疑他们是吹牛,江湖上有几个不是说大话使小钱的主儿?偏偏林驿丞竟当真:“你们细细说来。”老叫花子说:“带头修墙的是曹六爷,他家三代都在工部当石匠头,皇上没了以后,他才回到通州城。”我急,抢话说:“闲白暂且别说,拣要紧的说。”老叫花子说:“曹六爷最是厚道,跟我们爷们儿也和气,只要知会他一声,叫他借故遣你们客栈的小爷去采买,就势一溜号,不就结了?”我问他们:“就这么简单?”老叫花子使劲点点头说:“就这么简单。”林驿丞高兴了,拿出一袋子大洋,递过去:“带上,也许用得上。”俩老叫花子一下子把脸掉下来:“林爷,这就是见外了,你拿我们不当朋友看。”林驿丞不好意思了:“不是给你们的,是打点别人用的。”老叫花子说:“要花钱才能办事,你们还找我们则甚,那就谁都可以了。”
我跟林驿丞打坐一般的等着,长远不见他们回来,不知风儿将他们刮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几次跑到门口去张望,林驿丞安抚我道:“就把心搁肚里吧,你可以不信当官的,但绝对不能不信乞儿和落魄之人。他们要是答应下来的事,豁出命也要办的。”我仍怀疑:“听他们讲,不是比踢球打蛋还容易吧?”林驿丞说:“许是因什么事耽搁了也说不定。”又过了一会儿,门房叫道:“伴儿回来了。”我们听了,就往外跑,果见伴儿欢蹦乱跳地站在我们跟前,而老叫花子,一个头破了,血流不止;另一个肩膀中了弹,面如白纸。我们俩一边给他们涂创伤药,一边问伴儿怎么回事。伴儿说:“本来曹六爷使个计将我放出来,拐了几道弯,偏巧遇见了几个骑马的巡逻兵。他们拿枪逼我问话,我一慌,撒腿就跑,可是两条腿毕竟跑不过四条腿,眼见就要追上了;幸好这二位爷暗中保护,放响了二踢脚,把他们的马惊了,摔落在地。二位爷拖着我跑,巡逻兵就在后头放枪,结果……”林驿丞要请老叫花子在客栈养伤,老叫花子不干,说弟兄们都在破庙里等他们,只好叫他们拿上药,拿上几块大洋,找个洋大夫把肩膀上的子弹取出来。老叫花子倒烦了:“哎呀,真是啰唆,我们赶着回去,改日你给我们预备两碗素面就行了。”林驿丞送走老叫花子,转脸给了伴儿几巴掌,又问了几句寒温;伴儿也不还嘴,只是垂首听着。要我看,他们更像是一对父子。林驿丞叫伴儿去厨下吃东西,伴儿却不忙走,说奶妈已经找下了,又把奶妈家的情形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林驿丞踢他一脚:“吃了再说。”瞅着伴儿远去,林驿丞似乎很是动容。我感慨道:“难怪你这么欢喜与下九流相交,看着他们腌臜,其实个个都是忠勇汉子。”林驿丞说:“你也看出来了吧?交这样的人,你若遇到七灾八难,上天下海他都替你奔走,官场上能找到这样的忠义人才怪?”我使劲儿点头说:“是是是。”
街上的饿殍越来越多,似这样下去,要么就是通州城不攻自破,要么就是激起民变,闹将起来。林驿丞干脆把大门锁上,生意不做了,免得被抢。老娘每晚上都焚香对天,保佑一城的百姓平安。王品怕老娘着了惊吓,就跟我商量,是不是先送她老人家返乡去。我说:“眼下境况,一动不如一静,只有等兵退了才能再作打算。”王品却说:“兵退了,也就安生了,我哪里还舍得让老娘离开?”我笑了:“这倒也是。”王品突然问我:“你还记得静怡师父住持的那个庵堂吗?”我说:“记得。”王品说:“一直荒着,现在破败得不成样子了,我想买下来,好好收拾一下,再盖几间房……”我知道他也是心里还有静怡师父的意思,便不说破:“可以呀,天热,也好叫老娘带孩子们过去住,避避暑的。”王品想不到我竟这么赞成他,且又通情达理,大出意外。我说:“要是买园子手头不宽展,可以打我这里拿。”王品拍拍腰间:“钱还有些。”我奇怪地问他:“你的银票当初不是都压在柜上了吗?”王品捋着胡须道:“你当我就只有那么几百两银子吗?咱们哥们儿谁也别瞒谁,哪个人手头不存个千把两的,吃两辈子都有富余。”王品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留胡须,看他捋起来总觉得不大顺眼,我把他捋胡须的手打下去,说道:“我看林驿丞手头就挺紧。”王品说:“几兄弟贴补他一些,也就是了。”我说:“他那个人最要脸面,怕是不会答应的。”正说着,枪炮大作,直军又开始攻城了,这一回不同的是,不是在黑下,而是在大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