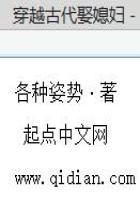误会和不误会的教案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由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例如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甫指指点点,比比画画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本是教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工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于是各种“故事”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得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和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得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王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作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地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地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愤”,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火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也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的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指气使。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往往一人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屈,好像也大有问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倨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放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下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的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被燎掉的大胡子
同治五年(1866)一开春,已经被各地民教纠纷搅得焦头烂额的总理衙门,迎头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国公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提交抗议照会,说是在直隶的宁晋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教案,法国传教士艾清照被该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设计陷害,以火药轰伤,“几至殒命”,而宁晋县政府有意袒护凶手,竟然放纵不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查明此事,严惩罪犯以及有关官员。
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拥有天主教的护教权,加上挟刚刚战胜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总是特别地蛮横,动辄派来炮舰以武力威胁。总理衙门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着什么,随即致函要求直隶总督官文务必查清此案,给洋人一个说法。由于总理衙门是由当时权势正盛的恭亲王奕领衔,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直隶总督官文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张树声立即派人查案,并亲自督办。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这场在法国公使眼里蕴涵着莫大阴谋的害命大案,原来竟是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
据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间,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农民张洛待的十七岁的二儿子张书琴不知怎么就中了邪,成天价弄神弄鬼,一会儿说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觉,一会儿又说有仙人把女鬼赶走了,但要把女儿许给他,还弄出了两张画着不知什么东西的纸片,说是仙人给的信物。张家在双井算是个富户,不仅年年余钱剩米,还有能力开个家塾,请了先生在家教二儿子念书。张洛待自家虽然没有挣上一个半个功名,但却是本村乡绅刘洛明副榜老爷的女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副榜,就是省试(即举人考试)正取之外的副额,人称半个举人,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在名声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说张家在当地说不上是有钱有势,却也处处让人高看一眼。满心指望二儿子读书用功,挣个功名,也好光大门风,所以虽然早就给儿子定了亲,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攻读,所以放出话来说是要等到儿子满二十岁再行迎娶,可是眼下儿子神神鬼鬼地闹,老师散了学不说,把个家也搞得鸡犬不宁。于是,张老先生决定提前给儿子迎娶,按民间的习俗,“冲冲喜”也许就能把邪给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