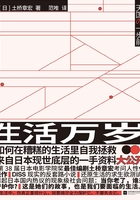阿海是多么机敏的人,他十分明白,小弟已不能与他只讲义气了。他的心头‘扑通扑通’地悸动,感到一种真正的失落。他想象着做父母的人嫁出女儿时的心境:既要祝福,又难舍难分。是别家人了哟!
四
自从依妹病故,林继祖已多时不出家门,其悲哀的程度,岂能用悼念干女儿来解释?贤惠的妻子,逐渐悟出什么,只是不说出口而已。自认做外婆的林夫人,让佣人为外孙四处去寻找健康的奶妈。她要把依妹儿子接到林府抚养,这自然会得到外公林继祖的赞成。当她把诸事都安排妥当后,便带着保姆及入选的奶妇前去“龙海之家”。美玉与她的母亲,在听明白林夫人来意后,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突然,美玉“哇”的一声哭着跪在林夫人跟前,这情势看似怕孩子被抢走。林夫人要把美玉扶抱起来,但美玉磕头道:“不可呀!这是我妹生死相托,孩子只能吃我奶长大,今生今世,我与这孩子不能分开!”
继祖夫人叶氏,是每逢初一、十五都沐浴吃素,虔诚拜佛的人。她心肠特别软,经不起这撕肝裂肺的哭泣声震撼,因而也泪流满脸。她想,这样有情有义的女子是很难得的。因此,随口安慰道:“你对依妹这样情深义重,我很感激,我很看重。今后你就是我的女儿,我们一起替依妹把这孩子抚养成人吧。”说着,她把美玉搂在怀里。此情此景,美玉母亲也很受感动,便立即应和道:“快叫,快叫声……”叫什么呢?她想到,女儿至今仍叫她做“依奶”,那么,就将义母叫做妈妈吧。于是她接着说:“快叫声好妈妈呀!”美玉照母亲的意思叫了,并紧紧地抱住义母。
继祖对于他的妻子收美玉作“接面干女儿”本不感兴趣,但对她们有意尽心养育他的外孙,自然不会反对,因此也就认可。这样一来,林夫人就安排贴心的佣人,当年由叶府陪嫁来的丫头,如今大家都尊称她作蔡妈的,每日去帮美玉带孩子,傍晚才回府陪夫人。有时夫人叫蔡妈请美玉一道带两个孩子来作过夜客。因为有孩子的缘故,美玉走林府比依妹当时勤得多,加上她较外向、开朗,嘴也甜,更得寂寞的林夫人的欢心。遇到节日,阿海总不忘带些鱼虾海鲜去林府送礼。这样,在林府众人面前,常会见到干女婿与干女儿带两个干外孙同席过节的事。席间,老二林宗祖装糊涂地举杯说些“欢迎侄女一家回娘家过节”似是而非的笑话,弄得阿海、美玉都很尴尬。继祖夫妇自然都看在眼里。
有一天,美玉在林府大客厅与干妈一起照应着都已过了周岁的两个孩子。做外婆的林夫人唱着儿歌:“月光光,照厅堂。公食饭,玛(外婆)抱孙。谁家小囝囝,我家好外孙……”
她抱着外孙在厅堂里兜圈,边走边唱,时不时地斜眼看看小饭厅。继祖不善饮酒,难得一次与阿海对酌,纯为陪阿海,那是夫人刻意安排的。夫人叶氏求自己的丈夫开口,要女婿续弦。因为自秀才老爷子离世后,林府只安定了一阵,刚过了七旬才满五十天,老二宗祖就把亡父的遗嘱置于脑后,在他妻子的挑动下,三天两头地提出要分家。当家的老三表面上是尊重大哥的,并不敢迁就二哥的意见,但也感到自己吃力不讨好,何苦要支撑这个大家庭?继祖夫人深知丈夫不愿被绑在田园里,那么,分下来的这么多田园还有当铺等家业,谁来掌管?儿子是不能依靠了,这外孙既然是林家血脉,那么,留住这干女儿美玉管内,阿海管外,即便继祖出门或不管事,这个家还是圆满的。妇道人家如此盘算家计,自是情理中的事。但这翁婿俩此刻却寂静无声地对坐良久。在难得举杯之后,阿海从怀里掏出外婆的那副眼镜并说:“外婆临终前,交出这副老花镜,示意要给依妹认亲。现在用不着了。”
继祖接过眼镜,泪水夺眶而出!又过了许久,他没头没脑地问道:“她现在哪里?”
阿海想:外婆与依妹都不在世了,问的自然是依妹的母亲福宋。
“外婆没有说,她老人家去世后,我问了郁家贵伯母。伯母说,母亲是跟高山镇的人去了日本。又说曾有龙田的日本客在长崎宗福寺烧香时遇到她。再就没有什么音信了。”阿海说完,看了岳父一眼,只见他眼神迟滞,缓缓地重述了一句“长———崎”,再也没说什么了。
在这次翁婿俩见面结束前,岳父把口袋里插着的一支派克钢笔,交给阿海,只简单地说了句:“多练练字。”
当年“南洋客”能带回国的有三件宝:英国兰铃自行车、瑞士欧美迦手表和这美国派克钢笔,那笔尖是真金的。阿海自然明白,这不仅是礼物贵重值钱,而且是一种严谨的期待。
继祖夫人得悉自己丈夫在阿海面前,根本未提要女婿续弦的事,十分失望。但她也想到,要继祖谈此事的确为难,因为他不免要为自己女儿伤心。因此,她决定找美玉母亲商量。美玉母亲十分干脆,在她心里,早已不认郁家贵是她的女婿: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拜过天地,把人抢去又抛弃了这能算什么夫妻?女婿早该是阿海。她自然不是这样对林夫人直说,斟酌了一会儿,她造出了句子:“他俩该圆房了,这对两个孩子都好。”说完又补充一句,“这也是美玉答应了依妹,该还的愿。”
美玉母亲的答复,使林夫人很满意。但这类亲事怎么操办为好,她没有主意,还是去请教曾殿臣老叔为妥。不料老叔听了,沉吟半晌,眉头皱了又皱,反问道:“我那个贤侄怎么说?”
“你说他?问过了。他不说什么就算是同意。”林夫人答得有些牵强,也有些无奈。
曾殿臣在肚子里说:妇道之见!由你林府开门办这桩喜事,岂不是向山匪叫阵?那郁家贵岂肯罢休。逼得他狗急跳墙,麻烦多了。曾叔松开紧皱的眉头,语气和蔼地说:“此事待我与贤侄商酌商酌再说。”
曾殿臣没找继祖,而是叫儿子去请阿海到曾家。找的借口还是老套:有人送来一坛“蜜沉沉”,要与阿海来分享。
跟往常一样,美玉母亲炒了四碟下酒小菜让阿海带上。她也没忘再叮嘱一遍:“蜜沉沉就是沉缸酒又名出门倒,少喝两杯!”她联想林夫人的话,猜透曾老不把好酒带上门的用意。她心里乐滋滋地望着阿海离去的背影:这女婿定了。
阿海见锡酒壶里倒出的是“番薯烧”,而不是红酒,便知道曾老有话要避开美玉她们来说。这一对老少忘年交,早已达到了有事必商量、无话不说尽的境地。可是今天,曾监生又为寻找适当的开场白所难。他感到棘手的是:阿海无意与美玉成婚的话,有失林府之期待;如果阿海看上了美玉,那麻烦就更多。他斟酌了多时才开口道:“依妹已离去周年了,你该再成个家,那样对谁都好。”
阿海听曾老说完,眼睛一眯,脖子红透。他断定指的是美玉,也不作他想,便随口问道:“她们母女俩怎么说?”
曾老一愣,不能及时回应。他明白了这小子头脑里只有美玉,此刻顺着说逆着说都不好,便含糊地答道:“要行办这样大的事,自然也要与她们商量,但总应当先听听你自己的意思。”
阿海还没有作声,曾老就趁机再抛出一个“气球”:“像你这样的人品与能耐,虽然说是续弦,但在此间找个黄花闺女,也是不难的。这样的话,事情就好办,又没有‘尾巴’,我相信人人都会如此盘算。”
阿海像是吃了一颗手榴弹,全身都受到轰击,面孔被震得发紫,拼出了一句话:“一牛对一客!”
阿海的这句话,说得像“刨番薯钱”那样干脆。自然,福清哥的这句口头禅,曾殿臣是熟悉透了:有人牵着老牛,到牙行卖掉,买头牛犊回家;也有人卖掉牛犊,买头老牛回家。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各人选各人之所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世道就是如此。那么,阿海是选定美玉了,什么样的黄花闺女,他也不感兴趣,曾殿臣这样下了结论。老头子的毛病改不了,又把心里想的话溜出口:“看来你俩早已……”早已什么,曾老开了口又清醒地收住。他难得在关键时刻记起一句“自古道”:话到嘴边留半句,理从是处让三分。他感到庆幸,差点在小辈面前说粗话。
“她早已在我心中,但我绝未碰过她的皮肉!”阿海说得有些激动也有些感慨。
曾殿臣看着阿海,感到此子比第一次见面时更显得陌生。近在咫尺、早在心中又皮肉不碰,那算是什么?老爷子感叹自己比这小子多活了五十年,却被考倒。无论如何,曾老头子是很看重与阿海的忘年交,为这小子安危着想,有话不能不说尽。他喝了一口酒,直截了当地说:“如此一来,那山里的岂肯罢休?”
“较量不止一次了吧!”
“我说的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哟!”
“怕背上吃子弹,就把心中的放水了?!”
曾殿臣看着坐在面前的阿海,心想:此子像利桥塔,是搬不动的。饱经风霜的老头子,出于对阿海的爱护,换个角度说:“有些事,可说不可做。有些事,可———做———不———可———说,你好自为之。我曾家依仗你照应的事太多了,来,干了这一杯吧!”
阿海捧起酒杯,眼里闪烁着泪花。
美玉和她的母亲把两个孩子安顿睡了之后,到楼下店堂对坐喝杯花茶,也是想等阿海回来,听听有什么说法。阿海推门进店时,偷偷看了美玉一眼,什么也没说就上楼了。母女俩猜不透今晚这“蜜沉沉”喝得是否合脾胃;不知那老头子,这次说的话是阴还是阳。做母亲的突然想到:曾殿臣有两个外孙女,都是年方二八,亭亭玉立。因此,她心里有点慌乱,但未把话说出口。美玉倒是很平静,视线跟着阿海的背影上楼。她深信自己与海哥之间,有一根红线牵着两颗心,从来没有失落过。依妹在世时,阿海从不正眼看着美玉说话,甚至依妹离世后仍然如此。但美玉却能体会出,自己无时不在海哥眼中。老外公在世时常说:稻种晒得越干,过冬时保藏得越深,播种时萌芽就越有劲。因此她认定,海哥是在暴晒、深藏种子呢。
母亲见女儿发呆,认为多想无益,便说了声:“走,上楼睡觉去!”
“龙海之家”沿楼梯上去,窗口向街道的有两个卧室,阿海住外间,近楼梯口。母女俩上楼时,见外间的房门开着,阿海斜躺在床上。做母亲的心血来潮,一巴掌将女儿推进阿海卧房,并随手把门关上,反挂了铁攀。她快步进入自己的房间,好像只听见阿海轻轻地叫声“玉!”,便都静了下来。四十来岁的母亲,却好奇地把耳朵贴紧墙板,听听动静:出奇地静了片刻,随后床板咿咿呀呀地响了两声,接着就传出女儿透大口气的喊叫声。“像在生孩子!”母亲不免掩嘴笑了。还好,这叫喊声没多久就停了下来。过了约莫一支烟的时间,母亲正想去解开铁攀,不料喊叫声又起。隔墙有耳呀!这夜阑人静时刻,邻居听了,还不知要招来多少“白字诗”呢!可是此刻如果用敲墙板或装咳嗽来提醒,都是很尴尬的事,唯一可取的,就是难为一下小外孙。外婆捏了一下外孙的屁股,并紧接着外孙的“哇”声,念念有词地说道:“啊啊,小孙孙,妈妈就来,妈妈就来了。”
外婆在外孙的哭声过后,轻手轻脚地去把铁攀解下。此时,女儿已等在门后,并立即出了阿海房间。
当母女俩回到自己房间时,母亲点点女儿的鼻子说:“太放肆了!”
“依奶!”她抱住母亲,用嘴轻轻地咬着母亲的肩膀,继续说道:“他,他是真正的男人!”
“不害臊!”
她俩都压低嗓子说话,但即便不压低嗓子,阿海也不会专心去听的。因为他沉浸在“正渔溪黄本龙眼”的回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