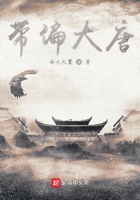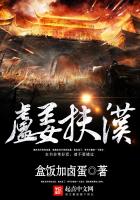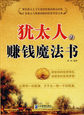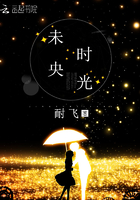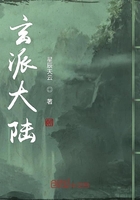第二次中西文化大交流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始于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继之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nan,1539—1607)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成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及其后继者。这些耶稣会士的科学传教,其目的在于宗教,并非作为文化使者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带到中国来,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大交流。现分别记述如下:
1天文历学
中国古来是个农耕社会,从事农业生产便少不了历法,因而中国的天文历法历史悠久,2000年前就有浑天仪和历书了。但中国历书根据月亮,不太正确,必须每年修改,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通用的是明初制定的大统历(以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为基础加以改订)。自成化元年(1465)以后,大统历与天象误差很大,朝中纷纷议论改历,但钦天监守旧,始终未能实现。及至利玛窦来华,才把西方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制定的阳历——格里高利历带到中国。
利玛窦看到中国历法的缺点,决定以天文历法为晋身之阶,所以他于1601年到北京献礼物时上疏说:“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命臣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窦翻译《乾坤体义》;还著《经天谈》,将当时西方已测知的诸恒星,造为歌诀,以便观象者记诵。他还自制浑天仪、天球仪、地球仪等器具出示,徐光启、李之藻、周子愚等与他结交,向他学习天文历法。他于1607年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由李之藻笔授,此书阐述简平仪用法,为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天文学的第一部著作。
利玛窦为准备好皇帝的召唤,写信给罗马的耶稣会总长,要求派几位精通天文历法的神父或修士来北京编译天文书籍,以便计算日、月食及行星位置之用。数年之后,庞迪我、熊三拔、罗雅谷、邓玉函等人先后来到澳门,伺机进京。不过此时利玛窦已经在北京故世了。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钦天监预测本年十一月初一有日食。职方郎范守己上疏驳斥其错误。果然届时日食不应验,万历帝责问钦天监,日食不验,该当如何处置?礼部奏道:应撤销钦天监内不称职的守旧官员,博求知历学者,令与监官昼夜推测。万历帝采纳礼部建议,大力整顿钦天监。于是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乘机推荐西洋人。上疏道:“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助典籍之缺。”当时翰林院认为,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也懂历法,可与庞、熊等同译西法,让邢云路等参订修改。但要修历,必须重视测验,建议皇上下令修治仪器,以便从事实测。翰林院的建议被皇上采纳,不久邢云路、李之藻都被召至北京,参与历事。邢云路所学的是中法,李之藻则以从利玛窦学来的西法为宗。
万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擢为南京太仆少卿,力荐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和阳玛诺等,他说:“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今迪我等年龄向衰,乞敕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但当时庶务因循,未暇开局,直至崇祯二年(1629)五月初一日食,大统历推测有误,而徐光启依西法预测应验,崇祯帝才接受礼部开设历局的建议,以徐光启督修历法。于是徐光启一面制定修历方针,一面重用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次年邓死后,又聘请汤若望、罗雅谷译书演算。徐光启本人晋升为礼部尚书,仍然督学历法。徐光启的修历,并非全部照搬西法,而是弃中法之所短,取西法之所长,互相参照考订,即所谓“宜取其法(西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也就是采用中西融合的方法。为更好地修订历法,徐光启上《历法修正十事》,即:一、议岁差,每岁东行渐长渐短之数;二、议岁实小余,昔多今少,渐次改易及日景长短岁岁不同之因;三、每日测验日行经度;四、夜测月行经纬度数;五、密测列宿经纬行度;六、密测五星经纬行度;七、推变黄道、赤道广狭度数;八、议日月去交远近及真会、视会之因;九、测日行,考知两极入地度数;十、随地测验两极出入地度数及经纬度。其后的《崇祯历书》就是按此计划累年测验之结果。同年(1629),徐光启上《见总界新图》,此为1628年所测。其上有黄赤两道经纬度,测得1356星,比大统回回历所测多5倍,并用西法绘图立表,引正旧图之误。其后又上《黄赤道总星图》,测得之星有1344颗。以上两图都成为其后《崇祯历书》的一部分。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上所撰诸书,计有《日躔历指》1卷、《测天约说》2卷、《大测》2卷、《日躔表》2卷、《割圆八线表》6卷、《黄道升度》7卷、《黄赤距度表》1卷、《通率表》1卷,共八种22卷,皆为后来《崇祯历书》的一部分。崇祯五年(1632)徐光启因病辞职,由李天经代职。是年徐光启病死,著历书百卷。
崇祯七年(1634),李天经进《历元》27卷和《历法》32卷。崇祯九年(1636)李天经与汤若望推测南京、北京恒星出没,还测得北京北极高度。至此新法历书仪器均已完成,所成之书140余卷,赐名为《崇祯新法历书》。该书分为11部,即《法原》、《法数》、《法算》、《法器》、《会通》、《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会》、《五纬星》、《五星交会》,其中有图表有论述,以西法融通中法,即如徐光启所说,“融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模型”。此书所采西法,以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日动说为主,没有采用哥白尼(Copernicus Nicolaus,1473—1543)的地动说。其主要原因,据说是他们不能用欧洲的历法简单地排除中国原有历法,因为一经变更,人民决计不会接受的。不过罗雅谷的《五纬历指》和汤若望的《历法西传》中对地动说略有介绍。该书完成后,守旧派魏文魁、郭正中等力言中历不可废,阻止颁布。及至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用西法测日食吻合,崇祯帝乃决定颁布,可惜兵事倥偬,未即实行,不久明朝灭亡。
清朝兴起,汤若望为清廷服务。首先他修复被破坏的天文仪器,还新制了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仪、望远镜等。其次他著作《新法表异》一书,以24事说明西法优越,中法拙劣。最后顺治元年(1644)预测日食成功,使清廷决定采用西法,将新历颁布天下,名为《时宪历》。后来汤若望担任钦天监正,受到康熙帝的恩宠,名声大振。但遭到以杨光先为首的守旧派妒忌,制造所谓“历狱”,不久病死。
西学保护人康熙亲政之后重用西洋人,以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7)为钦天监副(后升监正)。南怀仁于康熙八年(1669)改造观象台仪器,新制仪器六种,即黄道经纬仪、天体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地平纬仪)。又将各仪器的制法、用法、安置法绘图说明,并用其仪器所制得的诸表,合为一著作——《灵台仪象志》,书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还预测七政交食表32卷,名为《康熙永年表》。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赴盛京(今沈阳),南怀仁携带仪器随行,测得盛京北极高度,制成《盛京推算表》。当时法王路易十四世投康熙帝所好,赠地平纬仪,安置于观象台。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南怀仁死后,钦天监不再由西洋人为监正,历政顾问则有戴进贤(Ignatius Kogler,1680—1746)、林安多(Antonio da Silva,?—1707)等,监臣有纪利安(原名未详)等,他于1713年制地平经纬仪、象限仪及地平纬仪各一。康熙一代,钦定天文学书有两部,即一是《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1718),二是《历象考成》(1722),编撰者无一西洋人,全是中国人,可见中国已培养出自己的天文历法专家。除乾隆年间法国人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来华以外,已没有西洋天文学家来华服务于清廷了。蒋友仁来华进贡《增补坤舆全图》及新制浑天仪,并奉命翻译《地球图说》(何国宗、钱大昕润色)。该图说记述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原理,并引例详为考证。这是中国地动说之始。
关于清朝钦天监聘用西洋人,始于康熙八年(1669),当初只监正一人,后增加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八年(1753)又增西洋监副一人。嘉庆年间(1796—1820),监正已不规定用西洋人,监副则按乾隆旧制。至光绪年间(1875—1908)所纂的《大清会典》,已规定钦天监完全不用西洋人了。
2数学物理学
中国古代数理算术本有不少杰出的成果,但长期以来受封建体制的束缚,阻碍了它的发展,及至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才把先进的西方数理算术带到中国,给中国传统的数理算术注入新的血液,使其健全发展。
最早将西方数学介绍到中国的是利玛窦,他撰有《乾坤体义》2卷,其中下卷谈到数学,“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词简义赅,为近代数学传入中国之始”。后来利玛窦到北京,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译书,最先译出的是数学书,即《几何原本》6卷,译成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该书原为欧几里得的著作,由利玛窦在罗马时的老师丁先生即克拉维阿斯(Christoph Clavius)所编,共15卷,前6卷为欧几里得的本文、后9卷为丁先生的注释和绪论。《几何原本》的内容:第一卷论述三角形,第二卷论述线,第三卷论述圆,第四卷论述圆内外形,第五、六卷论述比例。该书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为求合本意,三易其稿,为输入西学中最完善的著作。
同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测量法义》,记述应用几何原理,以为测量之法。其中有测量术15项,每项都加以证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圜容较义》,专论圆之内接、外接形,引申《几何原本》,有定理18则,其中一则论椭圆。其后利玛窦与徐光启合撰《测量异同》、《勾股义》两书,论述三角法。万历四十一年(1613),利玛窦所著《同文算指》10卷由李之藻译出。该书论述比例、级数、开方等,为西方近代算术输入中国之始。
继利玛窦之后,艾儒略(Julius Aleni)与瞿式谷于崇祯四年(1631)合译《几何要法》。邓玉函(Joannes Terrenz)于崇祯二年(1629)译出《大测》,崇祯四年译出《割圆入线表》。罗雅谷(Jacobus Rho)著《测量全义》,系统地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及圆锥曲线、椭圆面积等。
顺治年间(1644—1661),穆尼阁(Nicolas Smogolenski)在南京著《天步真原》,由薛凤祚译出。该书以加减代乘除,折半代开方。康熙帝很喜欢数学,召西方传教士入内廷进讲。白晋记述道:“我们四个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幸被皇帝召去为他讲解欧洲科学。……皇帝委托他皇室里两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大臣来帮助我们写讲稿,并指定专人加以誊清。每天还叫我们为他口述这些文章。他整天和我们一起度过:听课、复习,并亲自绘图,还向我们提出随时发现的问题。然后我们将文章留给他自己去反复阅读。他同时练习计算和一些仪器的使用,经常复习一些最重要的欧几里得定理,以便更好地记住那些论证。这就使得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就熟练地掌握了几何学原理,只要给他一张与某定理有关的几何图,他就能立即回忆起这个学过的定理和论证。”代数当时称之谓“借根方程”或“阿尔热八达”(Algebra),与几何学同时输入,杜德美(Petrus Jartoux)著《周径密率》、《求正弦正矢捷法》,对中国代数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康熙帝命诸臣所纂的《律历渊源》中有《数理精蕴》一书,至雍正元年(1723)方始完成。该书集当时所输入的西方数学之大成。
西方近代数学输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对它进行学习和研究,终于出现了一批融合中西数学的专家和著作。例如,会通中西数学的梅文鼎,著有《筹法》3卷、《平面三角法举要》5卷、《弧三角举要》5卷、《方程论》6卷、《勾股举偶》1卷、《几何通解》1卷、《几何补编》4卷;王锡阐著有《晓庵新法》6卷;李之金著有《几何简易集》4卷;杜知耕著有《几何论约》7卷;年希尧著有《对数应运》1卷、《对数表》1卷、《三角法摘要》1卷;毛宗旦著有《勾股蠡测》1卷;陈訏著有《勾股述》2卷、《勾股引蒙》10卷;王元启著有《勾股衍》;程禄著有《西洋演算法大全》4卷;戴震著有《算经十书》、《策算》、《勾股割圆论》3卷;焦循著有《加减乘除法》8卷、《开方开解》1卷、《释弧》2卷、《释轮》2卷、《释椭》1卷,等等。以上都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启蒙书,在中国数学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物理学方面,最早将西方近代机械工程学输入中国的是熊三拔。他于万历四十年(1612)著成《泰西水法》一书,共6卷,由李之藻译出。该书记述取水蓄水等力学机械,着重应用,原理不详。徐光启对该书进行了研究,他结合中国传统的水利工程知识,撰写《农政全书》60卷,其中第12卷至30卷的水利部分皆依据《泰西水法》,因此可以说《农政全书》是中国第一部中西水利学融合的著作。其后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也受《泰西水法》影响;戴震按西洋龙尾车法作《嬴旋车记》,按西洋的引重法作《自转车记》,皆受《泰西水法》影响。
天启七年(1627),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3卷由王征译出。该书第一卷记述重心、比重之理凡61条;第二卷记述杠杆、滑轮、轮轴、斜面之理凡92条,每条都有证例;第三卷阐述应用上述原理,以起重、引重、转重、取水及用水力代替人力诸器械,各器及其用法都有详述,实为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力学专门著作。《远西奇器图说》给中国学者有一定影响,王征、方以智、黄履等便是。王征著《新制诸器图说》,方以智著《物理小识》,黄履著《奇器目略》,他们都应用机械工程学原理制造了各种器械。
万历四十八年(1620),汤若望携带新式望远镜至澳门,受到人们普遍珍视。明朝遗臣屈大均对“千里镜”记述道:“见30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划横斜,一一不爽。”天启六年(1626),汤若望撰成《远镜说》,为西方光学输入中国之先驱。该书仅16页,先述望远镜用法,再述其原理,最后述制造法;对光在水中的曲折,光经过望远镜之曲折,凹镜散光,凸镜聚光,以及凹凸镜相合以放大物像等现象解释颇详。
3地理地图学
利玛窦携带世界地图来中国以前,中国也有传统的地理地图学,大型全国地图和地方图一直在绘制着,不过与西方近代地理地图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中国地图上的标位不是通过天文观测,而是根据地区和地区间的测距而得出的,所以不精确,难怪肇庆知府王泮在利玛窦的卧室里看到悬于壁上高度精确的中国第一幅世界地图感到惊奇,并要求利玛窦把它译成中文了。于是利玛窦应王泮之请,根据西文地图重新绘制,附上中文注释,取名为《山海舆地图》,此为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也是西方近代地理地图学输入中国之始。后来利玛窦又根据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实测所得的经纬度,绘制了一幅符合中国人心理——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地图,这就是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该图将中国画在地图中央,既符合中国人的世界观,又把世界五大洲的地理知识和欧洲的经纬度制图法介绍给中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坤舆万国全图》的原版于1584年制成,后经多次修改再版(1595年南昌版、1598年苏州版、1600年南京版、1602年北京版、1604年贵州版)。原版早已失传,现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是1644年再版本。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窦著《乾坤体仪》3卷,继续介绍国际地理知识,并阐述四季和昼夜形成的原因。
关于耶稣会士绘制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的动机和目的,福斯(Theodore N.Foss)精辟地论述道:“首批来华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就把绘制中华帝国的地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他们把自己积累的制图材料用于启发中国人,并满足其同外部世界关系中的好奇心。标明中国在现代绘图学中的方位的传教用地图还可以回答中国人的问题,如:这些‘聪明的洋人’从何而来?他们深知精美的绘图品质和漂亮的地图外观的好处,这是超越语言的。耶稣会士们的制图工作还对传教有直接的好处,有利于完成在这个庞大中华帝国范围内宣讲福音的使命。从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早期活动到18世纪后期被镇压为止,绘制地图都被看成是耶稣会士、会友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中国同事们的一个合作项目。耶稣会士们为扩大传教规模及为朝廷效劳,同时也满足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情报的渴求。”因此,继利玛窦之后来华的耶稣会士不断为中国人编制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及制造地球仪。
天启三年(1623),艾儒略根据庞迪我、熊三拔的遗稿加以增补,撰成《职方外纪》5卷。它是中国第一部人文地理书,记述中国域外的风土人情和物产。该书卷首为万国全图、五大洲总图。第一卷为亚细亚总论和分论13条;第二卷为欧罗巴总论和分论12条,附欧罗巴图;第三卷为利未亚(非洲)总论和分论13条,附利未亚图;第四卷为亚墨利加(美洲)总论和分论15条以及墨瓦蜡泥加(南极),附亚墨利加图;第五卷为四海总论,有海名、海岛、海峡、海产、海舶、海道等的记述。该书除当时尚未发现的大洋洲(澳洲)以外,详细介绍了四大洲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崇祯十年(1637),艾儒略又写了《西方答问》2卷,简要地介绍了西方的风土人情。后来利类思(Louis Buglio)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将它改写成《西方要纪》,于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二十三日回答康熙帝关于西洋国土风俗的下问。
与艾儒略著《职方外纪》的同一年即1623年,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和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制成中国第一个地球仪,现藏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该地球仪制作精美,与现代制作的相差无几,它和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同为中国地理地图学史上现存的两件最重要的文物。
进入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南怀仁著《坤舆图说》,其中记述“地体之圆”说:“世谓天圆而地方,此盖言其动静之义、方圆之理耳,非方其形也。今先论东西,次论南北,以证合地圆之旨。日月诸星虽每日出入地平一遍,第天下国土非同时出入。盖东方先见,西方后见,渐东渐早,渐西渐迟。”介绍了西方的地球圆形说。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又著《坤舆全图》,这是一幅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当代欧洲世界地图,主要取材于瓦斯纳(Nicolausá Wassenaer)的1661年地图。在《坤舆全图》中,南怀仁扭转了利玛窦以来故意将中国置于世界中心附近的习惯,正确地表示了中国的地理位置。乾隆二十七年(1762)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著《增补坤舆全图》。他还翻译了《地球图说》,将哥白尼的地动说介绍到中国。
耶稣会士不仅通过世界地图将欧洲介绍给中国人,还通过中国地图将中国介绍给欧洲人。我们可以说,欧洲人有关中国地理地图学的形象几乎都是在17、18世纪从在华耶稣会士的资料中得到的,而在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地图的资料直接来源于中国人。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中国新图》就是参照了明末的许多地方志,批判地分析比较了原文并吸取了合理的结论。这里不仅有精密的各省详图,而且还对中国各个不同地区做了详尽的介绍,每省都有自然、经济和政治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卫匡国坦率地承认,“这部地理学著作并非单单出自他个人之手,耶稣会士前辈同僚们的作品给了他很大帮助。中国朋友们也为他提供最可靠的材料,甚至还从某些较长文章中摘出一部分给他”。1655年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在欧洲出版时,有位耶稣会士教友说:“卫匡国神父在其地图中把中华帝国地图情况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我们几乎再没甚么可求的了。”
与卫匡国编制《中国新图》的同时,波兰人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也在编制一本包含各省的《中华帝国全图》。卫匡国是为新建立的清朝服务,卜弥格则代表南明永历帝赴欧求援以图恢复明朝。但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当时没有出版,手稿散落各地,后来多亏法国神父、地图制作家达伯维尔(Nicolas Sansond'Abbeville,1600—1667)收集失落的手稿才得以出版。
至18世纪初,清朝版图迅速扩大,对康熙帝来说,显然需要一幅真实表现庞大帝国全貌的精确地图,而耶稣会当即表明他们对此事的兴趣和测绘及制图方面的能力和技艺。在得到皇帝批准后,耶稣会动员了足够数量、经过绘图技术训练的耶稣会士,搜集了有关地区的背景的丰富资料,让耶稣会士的绘图专家们在调查整个帝国的基础上绘制一幅完整而科学的地图。这项工程既满足了耶稣会编绘中国地图的夙愿,又满足了清廷对一幅科学帝国地图的需求。不过这项庞大的工程不是康熙帝一举就决定的,而是由几个小工程逐渐扩大的。首先是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找到了一个让康熙帝想看到一幅万里长城地图的办法,后来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又进一步鼓动康熙帝将这个项目继续进行下去。长城地图和小规模调查是促成宏伟计划的一个因素。
北河和温榆河的周期性洪水使康熙帝深深感到有必要对京郊四周进行一次详细调查,便下令让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雷孝思(Jean Baptiste Régis,1663—1738)和巴多明绘制该地区的地图。这幅地图在七天内便完成并进呈皇上了。皇上看了很满意,又召见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9—1720),要求他们绘制从永平府(北直隶管辖)到甘肃一带的长城,由地理学家雷孝思负责。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四日雷孝思一行率领耶稣会测量员离开北京。他们先到山海关,然后沿长城到山西北部,再从那里返回,到京时间是1709年1月10日。他们带回了一幅约15英尺长的地图。该图很详细,包括河流、要塞和300多个城门入口。康熙帝看了十分满意,决定绘制一幅精确的中华帝国图。耶稣会接到绘制中华帝国图的圣旨,便立即着手调查中国各省并收集西藏、鞑靼(即东北)和朝鲜等边远地区的材料。
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月八日,杜德美、雷孝思和费隐(Ehrenberg Eaver Fridelli,1673—1743)一起开始了东鞑靼地区的制图工作。该地区为满人故里,包括沈阳、热河、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河口一带,任务相当艰巨,幸而皇上下令,得到当地文武官员的大力支持,使工作进展顺利。这幅东鞑靼地图更使皇上满意,因为在北京出生的满族皇帝不离京城即可看到故土,而且从该图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接着上述三位神父又奉命绘制北直隶地图,这里是帝国政府的所在地,其位置非常重要。他们从1709年12月10日开始工作,至次年6月29日完成。
出色地完成北直隶地图之后,这三位神父被派到黑龙江中游、色楞格河和蒙古乌兰巴托以北地区从事测绘工作。他们从1710年7月22日开始工作,同年12月14日结束,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一幅新地图,皇上仍然很满意。
至1711年,耶稣会的绘图工程明显加快,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各省及其他边远地区的制图工作齐头并进。雷孝思和葡萄牙耶稣会士、数学家麦大成(Joao Cardoso,1671—1723)奔赴山东。杜德美、费隐和奥古斯丁会士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1669—1714)奔赴黑龙江、色楞格河上游和哈密地区。1711年底,又有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re,1669—1724)、德玛诺(Romain Hinderer,1669—1744)和冯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应征参加绘图工作,康熙帝当即钦定,分赴各省。
陕西、山西两省地图由汤尚贤和麦大成于1713年初完成,这两幅地图各宽10英尺。截至1715年底,其他各省地图陆续完成,送北京汇编。至1718年汇编工作完成,进呈康熙帝,费时10年(1708—1718)。这就是使用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和梯形投影法绘制而成、比例为1∶1400000的《皇舆全图》,又名《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帝对此图的绘成十分满意,对内阁大学士蒋廷锡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尔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过后面奏。”寻,九卿奏称:“……天道地道兼而有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该图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精密的地图,1718年由铜版雕刻家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在北京用铜版印制,共48幅。该铜版刻本地图被送到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 V)手中,感谢他对传教活动的支援。还有几册存英王乔治二世(GeorgeⅡ)地图学特藏库和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东方研究所。据说现沈阳故宫博物院有该地图的藏本,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又命耶稣会士傅作霖(Felix de Rocha)、高慎思(Josephd’Espinha)和蒋友仁等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又名《乾隆中国地图集》),比例为1∶1500000,共104幅,制作得比上述《康熙皇舆全览图》更精美,可见当时中国的地图绘制技术已达到国际水准。
4军事技术
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当初仅作为鞭炮之用,至宋代则用之于作战,1161年至1162年的宋金之战使用火药。后来火药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经过改良,制成火器,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最后火器被新兴市民掌握,成为消灭封建社会的有力武器,“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绝不是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这一点最早被日本人看到,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从火枪开始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明朝末年的一些开明官僚、士大夫,企图从澳门引进西洋火器来挽救亡国的命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价值,值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一笔。徐光启是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价值的第一人,他说:“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但徐光启并不是最先引进西洋火器的人,早在100多年前的嘉靖二年(1523),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在新会县茜草湾击败葡萄牙人时夺得其炮,即命名为“佛郎机”,进献朝廷仿制。《明史·佛郎机传》记载道:“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可见最早引进西洋火器的是汪鋐。此外戚继光、赵士桢等都是西洋火器仿制专家,赵士桢还著有《神器图谱》。当时有《海外火攻奇器图说》一书流传,作者不明。
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后金(即后来的清)向明朝发动战争,努尔哈赤领兵2万攻陷抚顺,次年萨尔浒(抚顺东80里)、开原、铁岭等相继失陷。警报传来,京师大震,人心惶恐。万历帝立即召徐光启从天津进京商讨对策,皇上当然知道徐光启曾“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徐光启进京之后,连上三疏,指出朝廷“兵政松弛,兵势懦弱,莫过于今日。欲得万全无害,必须有度外奇策”。这个度外奇策,便是按照西法铸造大炮,建立炮台。而建造炮台又需要深心巧思、精通理数的人。后来徐光启又接连上疏,发表了他的军事思想——富国强兵论,其中特别强调了财力、兵力和武器,三者不可缺一。关于财力,他说:“战守之具者七,而无一不需财,财不足,费不厚,欲求精兵利器,臣之愚计以为必不可得也。”关于兵力,他说:“千筹百说,总以精兵为根本;如无精兵,虽多得良将无可用,多有奇谋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结外援弗敢用也。”关于武器,他说:“欲我制敌,先议器械;欲敌不能制我,先议盔甲。”“战胜守固,必藉强兵;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与徐光启同时代的火器专家焦勖曾译出汤若望著的《火攻挈要》,他也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价值,主张武器西化:“火攻何以重西洋乎?为其能远、能准,又能速也,是以人莫能敌,最可贵者也。……得其要领肯綮,则凡铳皆可化西铳矣。”
徐光启的奏折被万历帝采纳,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监察御史,奉旨以巡抚体统行事,在京郊通州、昌平等地训练新兵,防御京城。他一上任就建议朝廷向福建、广东募集能造西洋火器的巧匠,购买西洋大小各种铳炮;还将武器库时的大小火炮提出来,发给将士操练。但是从武器库领出来的涌珠、佛郎机、三眼等大小铳炮性能极差,炸裂的很多,不敢使用,只有鸟枪一种还能使用。加上万历末年政治腐败,各部事多掣制,拱手坐视;饷银空虚,百无一备;而且保守派反对徐光启的练兵、用饷、制器等政策,困难重重。但他不气馁,既然官方途径不通,便用私资,通过朋友关系到澳门购置西洋大炮和聘请西洋技师。泰昌元年(1620)徐光启写信给闲居在杭州的好友李之藻(曾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和杨廷筠(曾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合议捐资(徐光启捐银400两)。李、杨两人一致同意,并由李之藻的门生张涛前往澳门购炮。但当时入澳关禁森严,便求助广东按察使吴中伟,转请两广总督吴应台拨船派员,护送张涛入澳,购置大炮4门。澳门当局推举精通火器的技师4人、随员及翻译6人,一同携炮到广州。此时徐光启等从澳门购炮之举受到反对派的非议,外国技师在广州被阻,后又折回澳门。大炮则由张涛自备舟船费用运至江西广信(今上饶),搁置待命。
这样一来,徐光启便灰心了,天启元年(1621)二月告病返驻天津。三月沈阳、辽阳相继沦陷。辽沈之占,明军不仅兵粮进一步匮乏,而且所拥火器大多被后金军夺去,局势更加严重。许多朝臣急呼星夜铸造火器,召回徐光启主持此事。四月中旬徐光启被召回京城督造火器,下旬颁给光禄寺少卿兼工程部郎中李之藻“监督军需”的关防,协助徐光启制造火器军械。
李之藻重返朝臣之后,极力宣传西洋火器的先进性,指出此器真可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同时他还主张到澳门招兵:“风闻在澳夷商,遥荷天恩,一向皆有感激图报之念,亦且识臣姓名,但以朝廷之命临之,俱可招徕,抚辑而用也。”
徐光启受命之后,立即提出“以台护铳(炮),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防御体系。而这种建造炮台安置大炮的防御体系,是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学来的:“若能多造大铳,如法建台,数里之内贼不敢近,何况仰攻乎?一台之强可当雄兵数万,此非臣私智所及,亦与蓟镇诸台不同,盖其法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炮台)也,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闽广商民亦能言之。”正当徐光启、李之藻大刀阔斧进行备战的时候,南京礼部侍郎沈□和宦官魏忠贤等反对派又大加攻击和弹劾,使建台、造炮、练兵的经费无着。徐光启一气之下又以病辞职,退归乡里上海。徐光启虽然离开朝廷,但此时以前留在广信的4门大炮运到了北京;由两广总督胡应台从澳门购得的26门西洋大炮及招募的外国技师7名、翻译1名和随从16名也由张涛护送来京,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兵部尚书董汉儒盛赞西洋大炮为“猛烈神器”。这30门大炮,11门调至山海关前线,19门留守京城(其中1门在演习中炸裂),在抗击后金军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启六年(1626)正月,宁前道副使袁崇焕在宁远(今辽宁兴城)保卫战中充分发挥了大炮的作用,把后金军打得落花流水,努尔哈赤也受重伤,不久身亡,史称“宁远大捷”。战后庆功时,将其中一门西洋大炮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它就是徐光启等人以私资最早从澳门购得的4门大炮中的第二位。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皇太极(清太宗)亲率10万清兵入关,围攻北京,全仗西洋大炮解了围。正当清兵围攻北京时,由两广总督王尊德招募的陆若汉(Jo?o Rodriguez,?—1634)和公沙的西劳(原名不详),携带大炮10门,率领技师、工匠等从澳门抵达京城南郊的涿州,协助明军守城15昼夜。后来大炮运入北京,分置于冲要之地,保卫了京城。陆若汉和公沙的西劳被明廷留用,并派人向他们学习大炮操作法,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陆若汉上疏感谢道:“奉旨留用,方图报答。天末远臣,愿效愚忠。”
不久明廷命中书姜云龙偕陆若汉赴澳门购炮及招募技师、士兵,结果招了300人,编成一旅返京。不料礼部给事中卢兆龙等反对派上疏中伤,说什么“此300人,助顺则不足,酿乱则有余”。“澳夷专习天主教,最易惑世诬民。”结果陆若汉所率的队伍被阻于南昌,皇上只准陆若汉等少数人运解大炮进京复命,其余一律返回澳门。
崇祯四年(1631)春,陆若汉回京复命,徐光启将他介绍给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协助造炮练兵。此时精通西洋火器的登莱监军道王征、登莱副总兵张涛及葡人公沙的西劳都在登莱,使这里成为一个研制和演习西洋火器的中心。崇祯五年(1632)五月,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十月病故。徐光启死后人们继续引进西洋火器,但终究未能挽救明朝的灭亡。但是,“徐光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政治和军事的结果,而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成就。他引进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军事科学技术,由此引起了我国传统军事技术及战略战术的深刻变化,并对数学、机械学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把人们的眼光引向外界,引导人们汲取和融会异域文化精华,补充和丰富自己的文化宝库,最后达到超越他人的目的。这些才是具有永久性价值的东西,为后世借鉴外来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的经验”。
继徐光启之后引进西洋火器的是汤若望。崇祯十五年(1642)兵部尚书陈新甲上疏说,西洋炮乃中国长技,有无间大将军之称,宜加紧铸造。崇祯帝便命汤若望铸造,由工部办料;还命汤若望将用法传授给兵杖局内监。汤奉命,共铸无间大小炮20余尊,大者重1200斤,中者重300斤,小者重100余斤。炮铸成后,崇祯帝派大臣随同验放。皇上嘉其坚利,下诏再铸500尊,并命汤若望教授放炮法,编纂炮术书。炮术书于次年撰成,详述大炮铸造法、使用法、安装法及弹药、火箭、地雷的制造。该书由焦勖译出,取名为《火攻挈要》。
清朝建立以后,因吴三桂叛乱,南怀仁奉命铸炮,自康熙十三至十五年(1674—1676)铸成大小炮120尊,发给各省。至二十年(1681)又铸“神武炮”320尊,在卢沟桥试放成功,康熙帝莅临现场检阅,嘉其命中。南怀仁之后,因国家太平,西洋火器引进不急切,史书未见记载。
5医药生理学
明隆庆元年(1567),葡萄牙传教士加内罗(Melchior Carneiro,1519—1583)到澳门传教,次年被晋升为澳门第一任主教,负责传教工作。隆庆三年(1569)加内罗在澳门东侧开设第一所医院,不分教内外,病者一律收容,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关于这所医院,《澳门纪略》这样记道:“别为‘医人庙’,于澳之东,医者数人。凡夷人鳏寡茕独,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其费给自‘支粮庙’(在澳门南面,如内地之育婴堂)。”
该医院又叫白马行医院,分内外两科。看内科者除诊脉外,还以玻璃瓶盛溺水验其色,以识其病根,所有药品全是露汁,此为西药蒸馏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之滥觞。看外科者有医生安多尼,擅长外科,所用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计;冰片油以瓢计。
乾隆二十年(1755)方济各会士从马尼拉来澳门开设医院。嘉庆二十五年(1820),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医生立温斯顿(John Livingstone)在澳门开办一所医院,该公司另一名医生郭雷枢(T 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也到澳门开办一所眼科医院。当时预防天花的种牛痘的医术也传入澳门及中国内地乃至北京。首次在澳门试种牛痘是嘉庆八年(1803),但未成功。两年之后,英国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再次在澳门种牛痘,获得成功。他的有关种牛痘的著作,由广州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编译成《牛痘奇书》出版。嘉庆十年(1805)皮尔逊到广州行医,在洋行会馆开设牛痘局专种牛痘,30年间种牛痘的人达100万人。番禺人潘仕成在广州学得种牛痘技术之后到北京。道光八年(1828)广东人余心谷在北京南海会馆开办牛痘局,由潘仕成主持种牛痘,北京的医生纷纷来学种牛痘技术,从此以后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技术普及全国各地。
与西医技术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医药生理学理论也由传教士带来。万历二十二年(1594)利玛窦撰《西国记法》1卷,其中《原本篇》记述人的记忆在脑袋里,打破了中国人历来认为记忆在心的谬误。万历四十五年(1617)熊三拔著《药露说》,此为西药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之始。
最早将生理学传入中国的是邓玉函。泰昌元年(1620)邓玉函初到中国在澳门行医时,已作临床病理解剖。次年他根据瑞士解剖学家鲍欣(Gaspard Bauhin,1560—1624)的《人体解剖》(1605)写了《人身说概》(清抄本题为《泰西人身说概》)2卷,此为西方解剖学传入中国之始。该书上卷记述人体的骨、肉、筋、皮、筋络、脉搏、血液、神经等15个部位,下卷记述总觉司口、耳、目、鼻、舌,四体觉司行动、言语等8个部位,所论生理器官形态极为详细,部位非常正确。其后罗雅谷著《人身图说》1卷、《五脏躯壳图形》1卷。清抄本将此两卷书与邓玉函的《人身说概》作为姊妹篇合订一册,现存北京图书馆。此外,南怀仁还著有《目司图说》1卷。
清康熙年间(1662—1722),西医在中国进入实用阶段。康熙帝招聘不少懂西医术的耶稣会士入宫充当御医,并在宫内建立一个制药实验室。白晋记述道:“在那里排着各种不同式样的炉灶,摆着化学制药用的工具和器皿。这位皇帝竟不惜开支,指令所用的工具和器皿都要银制的。三个月里,在我们主持下,叫人制造了许多种丸、散、膏、丹。在试制过程中,皇帝驾临观看过几次。当我们药物的试验获得成功时,他极其高兴,并指令所制的药物归他支配使用。”康熙帝还命西方传教士编写了18至20篇关于各种不同疾病的医学著作。“非常幸运,皇帝对这批著作十分欣赏,以口头和书面大加赞扬,甚至把我们召到御前,当面称赞。”与此同时,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西药治愈了大量病人,其中有不少是宫廷大臣,还有一个是皇帝的驸马,甚至康熙本人。据白晋说:“不久皇帝也患了场重病,他服用御医们的药却毫无效果,就求救于我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洪若翰和刘应两位神父来到了,并带来了金鸡纳霜,治愈了皇帝的病。”
在西医西药的影响下,中国产生了自己的西医医生和西药学家。如中国最早的西医王宏翰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著《医学原始》,这是中国第一部西医学书。又如王清任根据邓玉函的《人身说概》和罗雅谷的《人身图说》写成《医林改错》2卷,论述如何利用尸体解剖来验证病人生理和实施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