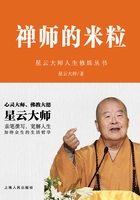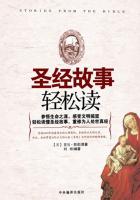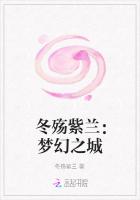禅学既然生根于中国的园地里,是纯粹的中国佛学,那么它的思想必然与儒道两家源流共沐。因此,从慧能开展出来的禅学系统便兼有儒、道两家思想。不过这并非说禅宗学者都是精通儒、道两家典籍,然后加以融会的,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僧侣,都是在中国思想所灌溉的园地里成长的,纵使他们没有读过儒、道的书,但在这块园地的泥土里,也很自然地吸取了儒、道两家的思想。
由此可见,禅学之所以融合儒、道两家思想,并非偶然的,也非人为的。事实上,在唐宋间的中国思想界根本是一个大熔炉。这一时期,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学说,都兼有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这时的儒家是新儒家,这时的道教是新道教,这时的佛学是新佛学。它们之所以为新,乃是在原有的系统外再吸收其他两家思想。譬如新儒家的理学、新道教的全真道,便是在它们本身的学统外,再兼采道佛或儒佛两家思想。同样,新佛学的禅宗也是在传统佛学外兼融了儒、道两家思想。
不过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理学虽然兼采道佛两家思想,但那些新儒家们为了发扬孔孟、维护道统,不得不排道辟佛。全真道虽然吸取儒、佛两家思想,企图革新以符箓为主的传统道教,但它们身为神仙家,也摆脱不了宗教的色彩。至于禅宗却不同,他们消化了儒、道两家思想后,便完全摆脱了印度佛教的旧传统,而开创了崭新的中国佛学。禅宗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固然主要由于慧能及以后许多禅师的智慧和气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便是早在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之时,首先去开门迎接的是道家思想。此后经过了三百余年无数半佛半道的中国高僧和名士的努力,才使佛与道逐渐融合,才使佛学完全的道家化,而有禅学的产生。所以自魏晋以来,佛学的中国化实际上乃是道家化。至于儒家思想的融入,则是在佛学彻底道家化以后的事了。基于此,今天我们研究禅学,必须从源头上了解禅学的道家背景。
一 禅法与方术的接触
当一个外来的宗教要突破另一国文化,去传布它们的教义时,最先往往不是以高深的理论去说服对方的知识分子,而是用最浅近、最神秘的信仰和法术到素朴的民间去发酵。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走的便是这条路线。
一般公认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是在汉明帝永平年间。这时,在表面上虽然仍保留着儒学独尊的空架,但骨子里却充满了阴阳谶纬、神仙方术。其实,自武帝以来的汉代君主,不仅外儒内道,而且他们所崇尚的道多半是方士的道术,并非老庄的玄旨。如武帝好神仙,成帝学炼丹,王莽尊图谶,光武奉占候,楚王英信方术,而明帝夜梦神仙才遣使去西域求佛法。所以,在这样一个儒学空虚、道家蜕变的时代中,印度佛教要图生存和发展,便只有与神仙方术结合。汤用彤先生曾说:
按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其特殊学说为鬼神报应。王充所谓“不著篇籍,世间淫祀,非鬼之祭”,佛教或其一也。祭祀既为方术,则佛徒与方士最初当常并行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
事实上,汉代的佛教并不限于斋戒祭祀和鬼神报应,因为当它最初在民间起信时,常常需要一些神通去收服人心,尤其在神仙方术弥漫的东汉,印度佛教要想站住脚跟,便必须拿出一套高明的法术来和方士竞争。据《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在汉明帝时,曾有道士褚善信等上书排斥佛教而奉诏在白马寺和摩腾斗法,结果道士失败,被迫出家奉佛。这段故事虽经后人断定是捏造的,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佛教在当时被包围于神仙方术中,不仅和方士并行,而且发生了冲突。由于冲突,一面以神奇为号召,希望压倒对方;一面附和于方术,以推行它的教化;一面则向它的大本营讨救兵,尽量输入有关法术的经典。所以,这时西来的名僧都擅长术数,如译经大师安世高便对“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高僧传》卷一)至于他所译的经有三十余部,著名的如《安般守意》《阴持入》《大小十二门》《道地》《禅行法想》《阿毗昙五法》等经,都是有关禅法的,都属于小乘的禅观修行,正好和当时的神仙方术连成了一气。
以《安般守意经》来说,它是当时最流行的一本禅经。所谓安般守意,依该书的解释是:
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念息不离是名为安般。守意者,欲得止意。在行者新学者,有四种安般守意行,除两恶十六胜,即时自知乃安般守意行令得止意。何等为四种:一为数(注:数呼吸也),二为相随(注:顺着呼吸也),三为止(注:心念专一也),四为观(注:返观内视也)。(《大安般守意经》卷上)
从这段解释可知:安般守意乃是由呼吸的方法打消意念而入禅定,这与中国方士的吐纳之术及后代道士的行气之法有点相似。吐纳之术的起源很早,在《庄子·刻意篇》中便有“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的记载,但详细情形不得而知。至于行气之法,在《抱朴子》一书中却写得很明白:
初学行炁,鼻中引炁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炁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着鼻口之上,吐炁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抱朴子·内篇·释滞》)
安般守意和吐纳行气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原理却相似,都是由数息而止念,由止念而入定。入定以后,都有神通,都能返老还童,“制天命,住寿命”。所以,这两者在当时便一拍即合。
大致东汉以来流行的禅法,不外于安般守意。安世高教人所习的禅,便是行安般。世高传给陈慧,陈慧再传给康僧会,便构成了安般禅法的系统。这一系统主张行安般可以成神,与神仙家养气成仙之说完全一致,所以,在当时极为风靡。
禅法和方术的结合,是印度佛学与中国道术最早的接触,但这次接触并没有触及思想的核心。因为禅法在印度佛学中不是最高境界,它一方面为婆罗门及其他外道所共法,一方面又属于小乘的禅观修行,所以在大乘佛学中都不谈禅法。至于方术在道家思想里更是一种旁门,《庄子·刻意篇》中便批评吐纳导引,只重养形延寿,而非道家本色,后来方术附于道教,其成分也就更混更杂了。所以禅法和方术都不是佛道两家思想的主流,它们的结合,只是这一融和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一种不成熟的尝试而已。
二 般若与玄学的合流
这一尝试,到了魏晋之际便有了新的转变。因为自魏正始以来,由于何晏、王弼等人的提倡,清谈之风渐盛。清谈的起因固然很复杂,但从思想的脉络来看,不外乎反对汉代的训诂,痛感儒学的衰弱,而逼出道家思想来安慰人心;再由于神仙方术的攀附,使得道家思想混浊下沉,而逼着大家向上去追求老庄的玄旨。所以这些清谈家们不仅厌弃训诂之学,而且对方士长生久视之术,如却俭的辟谷、甘陵的行炁、左慈的补导,也都表示不信。如曹丕在《典论》中批评说: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然而惑者望乘风云,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饥餐琼蕊,渴饮飞泉。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返,潜者莫形,足以觉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八)
虽然嵇康有养生之论,曹植、阮籍、张华、何劭、张协、郭璞等人都有游仙之诗,但他们向往的是逍遥的境界,是玄学的神仙,而非讲求符箓咒语,作威作福的方术的神仙。所以,这时一般有识之士已逐渐摆脱两汉以来的鬼神祭祀和灾异谶纬。即使炼丹鼻祖、好谈神通的葛洪也批评说:
夫福非足恭所请也,祸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祷延,疾可以丰祀除,则富姓可以必长生,而贵人可以无疾病也。(《抱朴子·内篇·道意》)
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甲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抱朴子·内篇·道意》)
佛教在这样一个风气转变的时候,一方面为了适应环境,一方面由于在民间的传教已有基础,所以便逐渐脱离了方术,而到士大夫社会中去另谋发展。但这时士大夫社会陶醉在玄学清谈中,很少有人推崇那种安般守意的禅法。因此佛教要想与玄学同流,便必须拿出一套清谈的功夫来。幸而佛教中的“般若”思想和老庄的玄旨相近,适于清谈,在这方面的储藏比禅法还丰富,所以只要风气一转,便立刻由和方术相混的汉代佛教变为高谈清净无为的魏晋佛学。
早在汉末,和安世高同时来中国的支谶(注:本名支娄迦谶)曾翻译《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经,这些经和安世高所译的小乘禅不同,都是宣扬大乘的禅观。不过在当时为方术及小乘禅法所盖,并不流行。直到魏晋之际,由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谦的弘扬,这些大乘的经典才流行于中土。汤用彤曾说:
安世高、康僧会之学说,主养生成神。支谶、支谦之学说,主神与道合。前者与道教相近,上承汉代之佛教。而后者与玄学同流,两晋以还所流行之佛学,则上接二支。明乎此,则佛教在中国之玄学化,始于此时,实无疑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六章)
所谓佛教在中国的玄学化,就是般若思想与老庄玄旨的结合。自此以后,一方面是般若经典的大量翻译和流传,一方面是玄学清谈的愈谈愈盛,而且这两方面又正好是相辅相成,相得而益彰,所以使得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名僧和名士的天下。
这时的名士,如王导、周顗、庾亮、谢鲲、孙绰、桓彝、桓玄、谢安、谢玄、许椽、郗超、王羲之、王坦之、习凿齿、陶渊明、谢灵运等人,有些是政治上的领袖,有些是文学界的泰斗,都与佛学有密切的关系。而当时的名僧,如于法兰、于道邃、支孝龙、康僧渊、康法畅、支愍度、竺法深、支道林、道安、慧远、僧肇、道生等人,虽然都是清净的佛门中人,但却常和名士来往,甚至参加清谈,以老庄的玄旨压倒名士,如《世说新语》中便有许多记载: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不仅像支道林等名僧深通老庄,要挤入清流;即使在当时持戒最严的慧远,他三十七年不离庐山一步;他为了不拜王侯,三度上书给桓玄;他临死时为了戒律,而不肯饮豉酒。照理说,应该和清谈绝缘,但其实他仍然和殷浩、陶渊明等人往来,仍然以老庄解佛,如: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慧远)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高僧传》卷六)
这些名士和名僧之所以气味相投,乐于清谈,就是因为老庄的玄旨与般若的思想可以互相发明。当代名士所谈的玄都是以无为本,据《晋书·王衍传》所载: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
至于般若思想以性空为体,据刘宋时的昙济分析,当代的般若学有本无(道安为主)、本无异(竺法深为主)、即色(支道林为主)、识含(于法开为主)、幻化(道壹为主)、心无(竺法温为主)、缘会(于道邃为主)七宗。而这七宗的学说都是以“无”为立论的中心,正好和玄学的崇尚虚无互相呼应,互相印证。所以,这些名士和名僧不是以老庄解佛,便是以佛解老庄。今天我们翻一翻当时所译的经、所作的注、所写的论,都带有些玄学的色彩,都套用道家的术语。如支谦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即《道行经》,也称为《大明度无极》,便改掉胡音,而用道家术语,至于内容更是反映老庄的玄旨。再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便以“无为”释佛,他说: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弘明集》卷三)
由于这些名士和名僧的趣味相投,使得魏晋间的佛学完全是玄学和般若的合流,这时的般若已非印度的般若,而是玄学的般若,最能代表这一特色的,便是僧肇的四论。
三 僧肇的四论
如果说由禅法与方术的接触到般若与玄学的合流,这是禅学的道家背景的话,那么,僧肇的四论便是这个背景中最特殊的表现。因为,般若与玄学的合流固然是针对禅法与方术的一种扬弃,但它们所合之处在于这个“无”字,而这个“无”字本不易把握,再加上清谈之风的影响,因此易流于虚无。暂且不论魏晋名士的由旷达、放诞而至于颓废,就是当代许多名僧也往往或走入玄学的迷宫,失去了佛学的正旨;或眷恋于清谈的虚名,而离开了清净的佛门。《世说新语》中记载: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惔问:“道人何以游朱门?”深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名公法喜态》卷一)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康僧渊遇殷渊源而知名,竺法深好游朱门,于法开与支道林争名,这些都是清谈名士的作风。由于当代的和尚都为这一风气所染,虽然他们神采秀逸,名高一时,但对于佛学,除了译经、注经之外,并没有重要的贡献。就拿当时最为名士推重的支道林来说,他虽然出家为僧,但养马放鹤,优游山水,以文翰冠世,与名士周旋,孙兴公把他比之于向秀,说:“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人异时,风好玄同矣!”(孙兴公《道贤论》)王该称他:“支子特秀,领握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肃。”(《弘明集》卷十三)大家似乎都把他当作名士看待。至于他自己的得意杰作,也只是有关庄子的《逍遥论》,所以他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清谈家。
虽然他们的清谈有时好像禅学的公案,也颇有禅味,如: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但这毕竟限于清谈,只是在语言思辩上用功夫,以楔去楔,仍然落于边见,并没有入道。
在这些玄论清谈的名僧中,真正能熔老庄、般若于一炉,既有玄学的风雅,又不失佛学的正旨,且有不朽的著作流传于世的,恐怕要推僧肇为第一人了。
僧肇是鸠摩罗什的大弟子,他在未遇罗什前已通老庄,后来又随罗什精研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维摩》《般若》各经,由于他天资敏悟,别有会心,再加以才情横溢,所以能用极优美的文字写极艰深的佛理。
他的主要著述是《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在这四篇论文中,僧肇不仅到处运用老庄的名词,如“无有”“无为”“无知”“无名”“无言”“虚心”“常静”“谷神”“化母”“自然”“抱一”“希夷”“绝智”(以上皆采自《涅槃无名论》),而且到处引用老庄的思想,如:
夫浑元剖判,万有参分,有既有矣,不得不无,无自不无,必因于有,所以高下相倾,有无相生,此乃自然之数,数极于是。(《涅槃无名论》)
然则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即有无齐观,齐观即彼己莫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涅槃无名论》)
事实上,僧肇整个思想的间架即是以老子的有无相生配合庄子的物我同体,来说明般若的动静合一、体用一如。
在当时,般若的思想为玄学所迷,而落于虚无。僧肇在《不真空论》中便批评心无、即色、本无等三家说: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不真空论》)
心无宗是支愍度、竺法温、道恒等人的思想,主张万物实有,只求心不执着。即色宗是支道林的思想,主张色无自性,因缘而有。本无宗是道安、竺法汰等人的思想,主张诸法本来无,万物由无生。这三派学说都是把本体和现象分成两截:以本体为真无(本无宗),以现象为实有(心无宗)或幻有(即色宗),而硬要去求通,所以仍然落于有无的边见。至于僧肇的看法却不同:他把现象和本体打成一片,现象透处即本体,本体显处即现象。就现象看是不离有无,但就本体看又不落有无,所以他说:
处有不有,居无不无。居无不无,故不无于无。处有不有,故不有于有。故能不出有无,而不在有无者也。(《涅槃无名论》)
然而,僧肇究竟以何等的手法把现象和本体打成一片呢?他所写的四论,便是四种法门:
(一)物不迁
在《物不迁论》中,僧肇举这个视之有形、敲之有声、摸之有体的物为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物是因缘假合、瞬息生灭的,即使当前为实有,但也只是尚未消灭而已,所以仍然是无常的。至于僧肇的看法却不同,他说:
伤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对真而莫觉,既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复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物不迁论》)
在僧肇眼中,这个大千世界正像一部电影,它的底片都是一张张固定的形体,而其所以有动作变化,乃是经过时间的流动,在人们心中所造成的连锁作用。同理,宇宙中的任何一物虽然都有成住异灭的过程,但这只是人们戴着“无常”的眼镜去看万象,其实就物体本身来说,它在某一刹那的存在却是永恒不变的。僧肇看透了这一点,因此他说:
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物不迁论》)
唯其如此,所以——
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注:语出《庄子》,指生物之气息也)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物不迁论》)
在这里可以看出僧肇手法的高明,他非但没有舍弃变化去谈本体,相反的,是就变化处去证入本体。同一条河流,一面是水势滔滔,没有一刻静止;一面又是千古如斯,未曾有一刻变动。僧肇便在这变与不变之间就地一转,把这个无常的物转入了永恒的常流。
(二)心不滞
然而照僧肇所说,物如果真是不迁的话,那么这个物岂非又成了当途之障?对于这一问题,他在《不真空论》中曾三次强调说:“即万物之自虚。”他认为一般人看到物便好像遇见仇敌似的,感觉周身不安。有些人(心无宗)背转身说“不理它”,有些人(即色宗)闭着眼说“不是它”,有些人(本无宗)大声喊说“除掉它”。这就同把自己的影子误为鬼魂,逃得愈快,跟得也愈紧。其实,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地看一看,便将发现物性自虚,作祟的还是自己。所以他说:
是以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无滞而不通,故能混杂致淳;所遇而顺适,故则触物而一。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不真空论》)
在这里,僧肇已把这个一般人认为铜墙铁壁似的物分解得丝毫不存。他的方法显然和心无、即色、本无三宗的逃避问题不同,而是真刀真枪的,用真心去即物。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真心,使它不“触途为滞”,不着于有无,那么无论这个物不去不来,都将还归自虚,不再是我们的障碍了。这正同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只要技进乎道,神与理会,以无厚入于有间,便所见而非全牛。同样,以不滞之真心,入于不迁之物如,自然是“无滞而不通”“所遇而顺适”了。
(三)智无知
不过僧肇所谓的真心,不是指那个能思虑、能辨析的生灭心。因为思虑和辨析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都是随着外境而转,落于有无的边见,因此都是假而不真的。至于真心却不然,它之所以能不滞,之所以能即物自虚,并非用知用虑去解析万物,相反的,是舍知舍虑去体合万物。僧肇在《般若无知论》中说:
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然则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智无知,故能玄照于事外。智虽事外,未始无事,神虽世表(注:即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明神之超然物外),终日域中(注:即庄子“与世俗处”)。所以俯仰顺化,应接无应,无幽不察,而无照功,斯则无知之所知,圣神之所会也。
僧肇这段话和庄子“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的说法相同。他把真心的作用比作一面明镜。这面镜子本身一无所知,一无所有,既不追逐于外物,也不留影于内心,但却没有一刻空过,因为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它随时随地都含摄着万物,返照着万物。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僧肇把现象和本体打成一片后所造成的便是这面智慧之镜。这面镜子自其无知无虑来说,它是扬弃了现象界的分别心,而自其知无不照、神无不会来说,它已证入了穷神知化的玄妙境界。
(四)道无为
这一玄妙的境界就是印度佛学上所谓的涅槃。依照当时中文的意译,一作无为,一作灭度。无为是“取乎虚无寂寞,妙绝于有为”,这是当时所流行的见解。灭度是“言其大患永灭,超度四流(注:见、欲、有、无明四流)”(《涅槃无名论》),这是印度小乘佛学的思想。至于僧肇所说的涅槃虽然兼容这两者,但却是以老庄思想为本,在他眼中的涅槃几乎等于老庄的道。以作用来论,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他说:
无为,故虽动而常寂;无所不为,故虽寂而常动。虽寂而常动,故物莫能一;虽动而常寂,故物莫能二。物莫能二,故愈动愈寂;物莫能一,故愈寂愈动。(《涅槃无名论》)
以道体来论是物我冥一的,他说:
然则法无有无之相,圣无有无之知。圣无有无之知,则无心于内;法无有无之相,则无数于外。于外无数,于内无心,彼此寂灭,物我冥一,怕尔无朕,乃曰涅槃。(《涅槃无名论》)
这个涅槃到了僧肇手中,已不再如小乘佛学所说,是死寂的、断灭的,相反的,是一种动静合一、体用一如的妙道。能够进入这种妙道的便是至人、圣人。在这里我们将发现僧肇虽然是一位佛家,不得不运用佛学的名词,如涅槃,但他这篇《涅槃无名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老庄的思想,他所追求的最高理境,事实上,仍然离不了老庄的常道。
我们从僧肇的四论中可以看出,他的确已用老庄的钥匙打开了般若的大门,看到了禅道的宝藏。如物不迁已触及现象的永恒性,心不滞已为“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思想开路,至于智无知、道无为,更发挥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精神。
最后,我们综合前面所说的,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1.印度最早传入中国的是禅法,它的深度只能和中国的方术同一层次,后来由于道家的觉醒,才使玄学摆脱了方术,般若代替了禅法,所以早在这个时期的道家思想已有舍弃印度禅的趋势。
2.由于僧肇的努力,使老庄思想和大乘佛学水乳交融,结成一体。此后,老庄思想便是透过这方面去影响禅学的。譬如石头希迁就是因读肇论而悟道,写下了不朽的《参同契》。
从这两点看来,中国禅学的源头应该从这里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