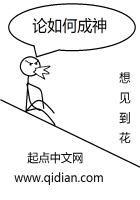1943年夏天,我被德国人逮捕了。当时我正和弟弟安热尔在染坊工作,我雇他来帮忙。前来逮捕的人让我们跟他们走,随后上了一辆伪装过的军用卡车。我的家人都已经在车里了,还有老奥吉埃和他的女儿多拉,就是那个之前经常和我一起上学的女孩儿。这是一次小型围捕:维尔的犹太人只剩下我们了。当我看到父亲时,我很希望他能说些什么,任何让我们安心的话都可以,但他一直保持着沉默。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丝毫没有反抗,也没说一句话。整个行程持续了两个小时,没人问我们这是去哪儿。
卡车终于停了,我们被塞进卡昂最臭名昭著的监狱——拉马拉德莱里监狱。七个人全部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除了年纪又大病又重的奥吉埃之外。整整两天时间,没有一个守卫过来看我们一眼,也没有食物和水。我们被完全遗忘了。
没过多久,躺在稻草垫子上的奥吉埃开始呻吟。他的嘴巴半张着,双眼死死盯着天花板,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不停地往下流,多拉俯下身靠近他,可是这位老人就要死了,他的呻吟声越来越大,并不时打断他的呼吸。我试着用同样的节奏呼吸,以分担他的痛苦。父亲用拳头捶门,想让守卫知道这里有人快要死了。他弄出了很大的动静,这才有个守卫过来。
“他参加过‘一战’,和你并肩为德国打过仗。他为此还失去了一条腿,你们不能让他就这样死在监狱里。”
守卫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奥吉埃求我父亲给他提前唱珈底什[25]。我看见父亲起身,开始为他朗诵献给死人的祷文。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祷告,我之前甚至都不知道父亲会这个。父亲念诵的祷文打破了几日来监狱里的沉寂,他的声音也由此带上了特殊而重大的意义。我知道被关在这里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集中营,或者死亡。起身唱祷文之前,父亲望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那一天,我们都确定,自己听到的就是所罗门的祈祷。
奥吉埃解脱了,但他的女儿还没有。父亲发誓会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她,我们也把多拉当成了家庭里的一员,这样她就不至于变成孤儿了。第二天,我们和这个地区其他所有犹太囚犯一起,被赶上了一列火车。装得满满的公交车把人像卸货一样放出来,然后再由士兵把我们塞进火车车厢。数百个人就这么堆在车厢里,什么年龄和阶层的都有。在一片嘈杂声中,德朗西这个地方被反复提及。保罗在车厢里奔走,到处问:“谁有纸?有吗?钢笔有吗?”
有的人是在家里被抓的,他们带了行李。保罗从这些人那儿借来了他需要的东西,回到了我们身边。
“你要做什么?”
“我要写信给阿根廷领事。”
“为什么?”
“你看,他们都戴着星标,而我们没戴。能在这时候帮我们的只有领事,他能保护我们。”
他写了好多封信,内容都一样,上面写了我们的名字、日期和要被送去的地方,这样阿根廷方面就能要求释放我们了。火车开走了。保罗把这些信给了所有他能找到的人,还有铁路工人,甚至还从窗户扔出去了几封。
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哪位好心人能帮我们贴上邮票然后寄出去。
让我来描述一下德朗西。那是一片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住房区。六层高的楼群一字排开,很长,这些尚未完工的楼房绕着巨大的院子形成了一个“U”字。没有门,没有窗户,也没有隔墙。由加固混凝土做成的住宅区就像一个骷髅一样被丢弃在那里。一座无墙的监狱,没有东西能帮你挡掉审视的目光,或者阻挡寒风。对于守卫来说地面上的一切都一览无余,同时在我们头顶上方,还有五座巨塔投下的恐怖阴影。德国占领军就住在里面。
这是一座“风殿”:一是字面上的意义,冷风一直在不停地吹;二是被逮捕的人们来到这里又被火车运走,也像是风吹过一样。
这里有几千人,全是抓来等待被火车送走的。四十人一个房间,到了晚上男人和女人会分开。这里像是一座蚁冢。没有人会在德朗西留下来,这里只是他们被送到欧洲各个集中营前的一站,他们在这里被分拣。有的人刚到就会被送走。德国人把那些地方称为“劳动营”,你见过能工作的老人和不到两岁的婴儿吗?这已经不是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了,所有人都听说过“冬季赛车场大搜捕”[26]。至于这里的人要被送到哪儿去,我们听到的目的地只有一个:佩奇波伊[27]。
在人们离开的前一晚,你能听见整幢楼里都回响着哭声,他们当中有的人被剃光了头,有的因为没有床只能坐在楼梯上。听起来这里就像一座精神病院。每当听到这些人的声音,我都会想起住在女性区的妹妹玻琳和多拉。整个晚上,我只希望她们能睡着,这样她们就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父亲已经答应过奥吉埃把多拉当成自家人,但不幸的是,此次领养只对我们自己有效。我们刚到这里,多拉就被安排到了楼下——那里都是“被驱逐的人”。父亲想尽办法让他们相信多拉是他的女儿,甚至还设法跟集中营的指挥官阿洛伊斯·布伦纳见了一面。但布伦纳坚持认为多拉是法国人,他的话让父亲只能接受现实:“如果就像你说的你不能抛弃她,我可以给你们全家在下一趟列车里找好位置。”
这次令人沮丧的会面结束几天后,多拉的名字就出现在了被遣送的名单上。对于她的离开,我们无能为力,时间也没法抹去我心里深深的愧疚感。
很多人都被送走了,而我们还留在这里。这里的规矩是每次遣送一千人,布伦纳对数字很执着,如果一个人在出发前失踪了,就会另外找一个人来代替。这个集中营可以前一天还和罐头一样挤,到了第二天就空空如也,然后又必将再次被新抓来的囚犯填满。全是犹太人:高的、矮的,金发的、棕发的……到了德朗西后,我才发现自己此前对犹太人一无所知。维尔的犹太人很少:雇用我父亲的莱维一家,奥吉埃一家,我们一家,还有其他几个人。纳粹宣传部门把犹太人说得很邪恶,夸张离奇的描述让我丝毫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在说自己,但是大众似乎很认可。战争期间我听到了不少反犹言论,并没怎么在意。人们会跟我说:
“都是犹太人的错,那些肮脏的犹太人。”
“但我们也是犹太人。”
“啊,是,你们不一样。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但其他犹太人……”
他们真的知道其他犹太人是什么样吗?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德朗西,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犹太人。我爱他们,通过爱他们,我也学会了爱自己——我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这个身份会伴随我一生。
在德朗西,我从一位老人那里学会了代数和算术,之前犹太人还能教课时,他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28]当老师。他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在我身上,而我则完全沉迷在数学和化学之间的关系里。我对什么都好奇,为了让课程能够顺利往下进行,我白天做笔记,晚上再背下来。
多亏了这位老人,让我即使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也能继续学习理论。他被我对知识的如饥似渴所打动,我想这些课程体现了我俩的一种基本且非理性的渴求,因为那是唯一能让我们忘记当下的囚徒处境的时刻。我是他最后一名学生。有一天,到了上课时间他却没来。他特意没提前告诉我,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名单上,或许就是为了帮我们省去一次艰难的告别。
我对政治的了解也越来越全面。我在这里延续了之前和让—拜耳在工厂,以及随后和布兰库尔特一起在维尔铁路线上值班时的那些永无休止的对话,现在则是和欧内斯特·阿彭策勒,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他简直可以作为雅利安人种“优越性”的代表而登上海报了。当时我十七岁,他十八岁。他说他是因为受过割礼而被误抓的。“受过割礼但不是犹太人。”他补充道。
他当时要求专门研究种族问题的德国科学委员会对他进行一次测试,他确信测试结果只会向他们证明自己是雅利安人。他自信的语调和敏捷的思维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让—拜耳。他常跟我说:“如果我是犹太人,那我一定是个复国主义[29]者。”
像父亲一样,我认为犹太人能拥有自己的土地纯属幻想。我觉得一个人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应该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有一种家的归属感;归根结底,宗教和国籍没有必要一致。我和欧内斯特无所不谈。我们彼此交换观点,任何事都能形成一套理论:政治、哲学,还有我们的理想。我们甚至还聊过神学,不过主要是他在聊,我其实不太懂。我被欧内斯特所掌握的犹太教知识所折服——而他甚至都不是犹太人。我俩一起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更好的世界。
三个月来,我遇到了数不清的人,这些相遇很不寻常,让我永久受益。我交了很多朋友,却只能眼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被驱逐,离开,而我对此无能为力。作为一个阿根廷人,我获得了在集中营里工作的“特权”。我先是当粉刷匠。在那些被我刷白了的墙壁上,原先写了很多的名字、日期,还有一些我不想涂掉的信息——因为这可能是写下信息的人生命最后的印记。有一次,我在刚刷完的墙上用铁片把那些字又刻了一遍,不幸的是,我被抓到了。于是我被送去了洗衣房工作,以免我再干下“这样的蠢事”。不知道为什么,阿洛伊斯·布伦纳每天巡查集中营时都会在我面前停下来,挺直身体,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在他面前我们本该低下头,但我选择了直面他的目光——那是为了多拉和其他所有人。既然所有人都陆续被运走去送死,只有我留在这里,我才不管会有什么后果。我已经不再害怕。直到现在,我依然能记得布伦纳用他那双尖利的黑色小眼睛看我时的眼神。他每天都会上下打量我一番,无视我的傲慢,一言不发地接着走他的路。对此我很是费解,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也许是阿根廷领事馆不断要求释放我们,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又或者只是单纯地因为我叫阿道夫。
“你们是怎么活着离开德朗西的?”
保罗给阿根廷领事的信起了作用。我们在集中营待了三个月,这是最长期限。救下我们的是一个政府的懦夫外交:它一方面不愿与强大的北美政府为敌,另一方面又想保住和纳粹德国的经济协议。于是阿根廷宣布保持中立,但中立并不存在。即便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做,也足以让这个国家成为帮凶。
当父亲说我们将被释放时,我差点就要把“拒绝”说出口:要在其他人迈向死亡之际离开,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呢?所罗门试图说服我:我留在这里毫无意义,在外面或许还有点用……这让我立刻想起了布兰库尔特和我在维尔做过的火药。我应该在那儿,和他一起。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那里。
就这样,我们身无分文地来到巴黎,身上只有藏在夹克衬里的由德朗西那些被关押的人写的几十封信。巴黎的反犹法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严苛,我们虽然没佩戴黄色的星标,但证件上的红色印章已足够明显。我们住不了旅馆,也回不了诺曼底,甚至都不能给自己买食物。虽然自由,但却举步维艰。自从1938年搬到维尔后,我就再也没来过巴黎。这座城市变了不少。所有路标都用了德文和法文两种文字,店铺橱窗里挂着“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墙上贴满了海报,上面画着鹰钩鼻、大耳朵、指甲像鸟爪一样尖的犹太人。德国军官坐着闪亮的新车开过街头,与贫穷破败的巴黎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人建议我们去找法国犹太人总工会。像孤魂野鬼一样在街头游荡了一整天,眼看就要到宵禁时间了,一无所获的我们只得照办。我们坐上最后一班地铁,在犹太人专属的三等车厢里。保罗不想去,他自己走了,他怀疑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旅馆是一个陷阱。这确实是事实。他们就是一群和纳粹串通一气的犹太人。
我们被安置到了瓦勒德马恩省的一处位于舒瓦西勒鲁瓦的房子里。那里曾经是一家养老院。我们在那儿得到了食物和照料。在德朗西的那段时间我变得很瘦,站都站不起来,膝盖不停打战。等恢复了一点力气后,我径直到塞纳河岸边的一家二手书商那里买了不少化学书。我想在重新任凭布兰库尔特差遣之前,学会如何造出有威力的炸药。我们被放出来的当天我就给他写了封信,我在信中实事求是地向他讲述了一切——显然,这也没什么好难堪的——就是告诉他我还活着。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信中满是善意和鼓励,还提醒我说他随时都会尽全力来帮助我。我把这封信当作护身符藏在枕头底下,这样就算是在晚上也不会弄丢。
我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直到有一天凌晨四点的时候,我听见了车的声音,引擎在我的窗户底下熄灭,然后是警察的脚步声。就在他们上楼的这段时间里,我吞下了布兰库尔特的信。我把它放进嘴里,可是信太长我没能全吃掉,但好在我已经把最关键的部分吞了下去,剩下的就丢进马桶冲走了。警察闯进了房间,告诉我有十分钟整理行李的时间,十分钟后必须离开。我带上了所有化学书,全是很重的大部头;再加上我依然很虚弱,其中一个警察还礼貌地帮我一起打包。我心想,这个人大概不会想到,他帮我搬的是我打算用来和他们作战的工具。
我们再次回到了德朗西,因为经历过这一切,所以我们都克服了那种恐怖的感觉。这一次,父亲一到这儿就开始了抗议。可局面似乎有些混乱。有人说:“是的,上面下令逮捕他们。”另外一些人说没有。最终,在经过了二十四小时后,我们被释放了。刚走出来,我们就在门口遇到了被警察围着、要送进德朗西的一群人。父亲听到他们在用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30]混着交流——这是阿根廷犹太人的典型特征。
“你们从哪儿来?”父亲问他们。
“我们是阿根廷人。”
“但……不是有外交协定吗?”
“已经没有了,他们现在在抓所有的阿根廷人。”
我们这才明白,原来德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协议已经终止,我们的庇护也消失了。此次重获自由,靠的是法国警方、纳粹党卫军和德朗西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不畅。如果再晚几个小时,我们就死定了。
第二天,父亲消失了,等到再回来时,他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
“我联系上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个俄罗斯人,是崩得组织的前成员。从现在起我们需要分头行动,大家各走各的。”
“就连我也是吗?”只有十三岁的玻琳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光是想想要和我们分开,就把她吓得够呛。
“你们每个人都会被安排到一个农场里,我还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或用什么方式,但首先我们需要弄到一些假证件。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护照照片,他们希望由一个年轻人把照片带过去。阿道夫,就靠你了。他们很快会给你安排一次会面,对方叫‘企鹅’。”
假证件……从小到大我受到的教育都告诉我要遵纪守法,假证件这回事我真的是从来没想过……
几个小时后我到达了见面地点,按照指示带着一本书在法兰西公学院门前的莫里哀雕像旁等待。我站在那里,人群在我身边来来往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学生,但是没人来找我。我不时地向四周看看,想要找出符合我心目中抵抗组织成员形象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应该是个像让—拜耳一样高大、自信、随和的人。
“阿道夫。”
我转过身,发现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矮个子,微胖,有着一头黑色鬈发的年轻人。他很随意地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像我们认识了很久一样。没人会怀疑这次见面。
“企鹅?”
他确认四周没人跟着我们后,带我走进了法兰西公学院。“你带照片了吗?”
我一边在走廊上走着,一边迅速把照片递给他,他立刻将它们塞进了口袋。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我们会试着在证件上保留你们真实姓名的首字母。你是哪年出生的?”
“1925年。”
“我们会写成1926年,好让你的年龄变小一点,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免除强制劳役了。职业的话,就写学生。”
“不,不行!我还得工作挣钱呢。”
“你有活儿干?”
“对,我是染匠。”
就在这时,一个学生从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走了过去。企鹅马上改变了声调:“你还记得她吗,吕西安娜?想不到吧,我刚碰到她了,你说巧不巧?她在学法律,但还和她父母住在一起……”
等那个学生走开后,企鹅继续说道:“你说你是染匠?”
“对,没错。”
“那你肯定知道如何去除墨渍了?”
“是的,这是我的强项。我还会做一些化学实验。”
“那去不掉的墨迹呢?”
“没有这种东西。所有墨迹都能去掉。”
这时又有一群学生朝我们走了过来。企鹅看了看四周,开始谈别的,关于一个我认识的人因为感冒今晚不能来一起吃饭云云。我开始掌握了些技巧,接着他的话聊了几句,然后又回到了刚才被打断的话题上。
“我们在处理华特曼笔[31]的蓝色墨迹方面遇到了难题,它根本没办法去除——这种笔迹到哪儿都弄不掉。你有办法吗?”
“目前没有,我得先分析一下里面的成分。”
“这个我知道,亚甲蓝。”
“那就很简单了。只需要用到一种还原剂——乳酸。”
“你确定?”
我确定?我怎么可能不确定!于是我跟他讲了我是如何在维尔的乳制品商店里学到了化学知识,包括那些让我读得如痴如醉的化学书,以及如何去除衣服上的污渍,还有如何制造条皂、蜡烛,甚至炸药。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最后问出了那个我期待已久的问题:“你愿意为我们工作吗?”
两天后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一次是为了取回我们全家人的假证件。从现在起,我就是朱利安·阿道夫·凯勒了;安热尔和玻琳同我一样,也姓凯勒;父亲变成了乔治·韦尔内。我们全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抵抗组织让我们所有人都“入了法国籍”。
因为周围人很多,企鹅一直在跟我聊他的堂姐——本来打算结婚的她,却不料被未婚夫毁约,等等。我很怕他会对之前的提议绝口不提,毕竟我已经激动得两天晚上没睡好觉了。临分别前,他让我去青年人旅馆租一个房间,并告诉我那是一个由救世军运营的新教徒机构。然后他补充道:“我们会联系你的。”
整整三天,他们一直在试探我的口风紧不紧。一个同样住在青年人旅馆的医学生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找我。他十分友善,或者说过分友善了……他问了我很多个人问题,比如回忆、家庭。我很自然地用一套官方答案来回答。我叫朱利安·凯勒,是一名染匠,父母都是里昂的农民。其他啥也不说。到了第四天晚上,他和企鹅一起来了,他俩把我带到莫贝广场边上的一家旅馆里,那里已经有两个人——“长颈鹿”和“苍鹭”在标间里等着了,两人都在二十五岁左右,自我介绍用的都是犹太童子军时的名字。他们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与之相反,他们聊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明白,他们已经调查过我了,了解了我的一切——甚至连我母亲去世这件事都知道。
长颈鹿让我坐在桌前,在我面前放了一张空白的身份证,还有一张纸,上面写了所有需要填到证件上的信息。我要做的就是小心地模仿出每一个细节,跟市长办公室里的小职员的笔迹一样就好——他们顶多也就上过小学。这项入门级别的操作谁都能完成——但不知为何我却极度紧张。这是我第一次伪造证件。我永远忘不了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桌上因为燃着一盏小灯而散发出木头的气味,笔和墨水都已经摆好,企鹅、苍鹭和长颈鹿就站在我的身后,越过我的肩膀安静地看着。我用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名字签好字,然后递给他们看。我越过了第一道坎儿,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迈出了漫长的伪造者生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