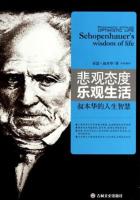如今,唯有独自出发,才能够更好地享受一次远足。如果人们结伴同行,哪怕只有两人,都会使真正意义上的远足变味,成为一种类似野餐的行为。远足应该完全独立完成,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任意停止或继续,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行走的道路;总的来说,你可以依照自己的步伐前行。[18]
是否真的应该独自行走?独行的例子其实不在少数:尼采、梭罗、卢梭……
事实上,陪伴时常意味着碰撞、阻挠,乃至步伐的扭曲。因为,每个人在行走时都有自己基本的节奏,并总想努力保持它。一旦找到各自适合的节奏,人在行走时就不再感到疲倦,甚至可以持续行走十余小时。但是,这种节奏却十分精确。所以,当我们需要跟随他人脚步来加速或减慢时,身体的灵巧度就会降低。
然而,彻底的孤独并非行走的必需。因为,就算三四人结伴同行,仍可在行走时保持缄默。每个人依着自己的步伐,渐渐拉开些距离,此时,走在前头的人常会转身稍作停歇,然后不由自主,神态轻松,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地问一句:“都还好吗?”走在后面的人则用手势作答。有时,前面的人也会双手叉腰,等待落在最后的同伴,等大家聚齐后便重新上路,途中,先后顺序也会悄然发生改变。人们根据自己的节奏,来来往往,交错向前。步行前进并不意味着要迈出完全一致、整齐划一的步伐。因为人体毕竟不是一台机器,它时常允许我们拥有短暂的消遣和放松的欢愉。当结伴同行的人数达到三至四人时,行走就会成为一段分享孤单的时光。因为孤单也可以被拿来分享,就像面包和时光一样。
然而,当人数超过四人时,这群行走者就会组成一个社团,一支向前的队伍。人们大声喧哗,吹着口哨,推推搡搡,互相等待。很快,大家就会拉帮结派,组建小团体。每个人都开始吹嘘自己的装备。甚至在吃饭时,人们都在竞相攀比,总想让别人尝尝自己带的神秘美味。此时的状况犹如炼狱,所有简单质朴的元素都消失殆尽。此刻,社会被移植到了山上。人们开始进行攀比。所以,行走的时候最好还是孤单一人。当同行的旅伴超过五个,孤单则再也无法被众人分享。
可是,当我们真正独自行走,形单影只时,却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首先,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真正的独处。就像梭罗所描绘的一样:“我整个上午都被簇拥着,直到有人来拜访我。”[19]本来,陪伴梭罗的是树木、阳光、碎石。事实上,与他人的相遇,常使我们变得更加孤独。因为,交谈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谈论自己与他人的区别。随着交谈的深入,对话人常会把我们引入他自己的经历和生存空间中。其结果会导致交谈双方相互的不理解,甚至互相欺骗。
当人们置身于自然中,就会感受到一种持续的召唤。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致意,同我们交谈,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树木,花丛,斑斓的小路,微风的低吟,昆虫的鸣叫,潺潺的小溪,掷地有声的脚步。所有的这些悸动都与你的出现遥相呼应。当然还有雨水。有时,一阵微风细雨,是我们最好的陪伴。因为它在喃喃低语的同时也会用心聆听。不难发现,雨声其实也有自己的“声调”、响度、间隔。比如打在石头上的雨水会发出清晰的汩汩声,倾盆大雨有时会形成一块帘布,以匀速倾泻而下。所以,要想在行走时做到完全孤单,几乎是件不可完成的事。透过目光,人们拥有了太多事物,它们就这样展现在行走者的面前,通过凝望而为我们所拥有。每一个行走者都应该感受一次海岬所带来的眩晕,当人们经过努力终于站立或安坐在岩石上时,才能眺望海洋,把全景尽收眼底。所有的田野、房屋、森林、小径全都属于我们,甚至为我们而存在。行走者通过攀登成为万物的主宰,并时时享受着这份拥有。试问,当人们在拥有这个世界的时候,还会感到孤单吗?事实上,观察、俯视、遥望就是拥有。然而,行走者却无须面对一个“主人”所需要承受的困扰,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以一个“偷窃者”的身份在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当然,行走者们肯定不是真正的偷盗者,因为,一路攀登也需要付出努力。所有我看到的一切,展现在我眼前的事物都为我所有。所以,视野的宽度也决定了拥有的物体。总的说来,我不再孤单,因为世界为我所有,为我存在,与我同在。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富有智慧的朝圣者的故事。一日,天色漆黑,眼看着马上要下暴雨,这位朝圣者沿着一条路走了很久,走到山谷尽头,看到了一片种着成熟小麦的田野。这片麦田生长于杂草丛中,被打理得很工整,在低沉阳光的映照下,麦田在微风中摇曳,泛起一圈迷人的光晕。这一景色美得让人动容,朝圣者缓慢前行,同时欣赏着这番盛景。正走着,他遇到了这片农田的耕作者,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正要返回。朝圣者叫住了他,拉着他的手臂,动容地低语道:“谢谢。”农民沉下脸,说道:“我没有什么可以施舍给您这个不幸的人。”可是,朝圣者却平静地回答道:“我感谢您,并不是因为您将会施舍给我什么,因为事实上,您已经把一切都给了我。您为这方麦田烦恼,在您的努力下,这片农田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丽。此后,您关心的是一颗麦粒的市价。而我,作为一个行走者,在整个旅途中都能够欣赏这片金黄麦田的美。”说完,长者仍旧保持着微笑。农民则转身,继续赶路,一路连连摇头,认为自己今天遇上了一个疯子。
所以我们在行走时绝不会感到孤单,因为途中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物体都能引发我们的共通感,不论是草木还是花朵。甚至,人们有时行走只是为了外出“拜访”:拜访那一片片绿地、树丛、紫色的山谷。在相隔数日、数周、数年之后,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道:“我确实很久都没有去那里走动过了,这些风景正在等我,是步行去拜访它们的时候了。”于是,我们缓慢上路,脚步坚定,重新遇见高耸的山丘和茂密的森林,就像与老友重逢一样。
在行走过程中不会感到孤单的最后一个理由是:行走的个体一旦上路,就成为两人同行。尤其是在长时间跋涉后。我的意思是,就算我们独自一人,身体和灵魂的对话仍在照常进行。当人们行走规律顺畅之时,内心就会充满斗志,感到愉悦,并会满足地拍拍双腿说道:“我的腿还真不赖。”这一动作,其实和骑马时拍拍马脖子,赞叹马匹别无二致。相反,当有时经过长途跋涉,身体感到透支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为身体打气:“加油,你一定能行。”所以,当个体一旦开始行走,其实立刻就组成了一支两人同行的队伍:人的内心和躯体。不难发现,心灵在这里充当着身体的见证者,它积极却又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内心不但要跟随身体的节奏,还见证着它的努力:当人们向上艰难攀登,并把双手支在腿上时,可以在膝盖处感受到身体的重量。在继续前行时,内心就会不断给予“你很棒”的鼓励。此时,心灵成为身体的骄傲。因为,我一旦上路,就能依靠内心形成一种自我陪伴。而且这场身体和心灵的永久对话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而不让人感到厌倦。事实上,正是通过这场对话、这一分享,才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在行走,在前进。换句话说,行走引发我们自我审视,完成自我鼓励。
有时,当我们置身于一片岩石之中,身边又鲜有草木时,会感到这条布满碎石的道路过于陡峭,充满艰险,甚至有些绝望:觉得自己被孤立,内心深处有种被世界排除在外的想法。如果那天碰巧天气阴沉,那么这种想法马上会变得难以忍受,并且难以克服。这时,行走者的喉咙就像打了结一样,焦躁地在崎岖的路上加速前进。当人们被巨石包围,身处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时,独自行走就显得难以想象:此时的脚步声会发出惊人的回响,身体由于移动,也发出阵阵喘息声。在这一刻,我们的躯体为生命蒙羞,被这个冰冷、高傲、绝对、永恒的世界所抛弃。或是在雨天或雾天的时候,当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也会出现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的幻觉。此刻的行走者会认为自己只是一具被冻僵却仍在向前的躯体,仅此而已。